當代視野的劇場性與文學性辨異兼論“戲劇”與“劇場”的界定與重審
時間:2021年01月28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 要】戲劇與劇場的界定曾在二十世紀被提出,其后由于步入后現代戲劇時代,創作中強調去文學化,導致了舞臺與文學的分裂,因而更加凸顯出劇場性與文學性的區別。如何辨析當代戲劇劇場中的劇場性與文學性特征?這個問題緊密聯系著當下對“戲劇”與“劇場”概念的重審,經過再定義,不僅能夠更貼合當代視野內的劇藝創作,更為國內戲劇理論批評提供了一定的指引。
【關鍵詞】劇場性;文學性;戲劇;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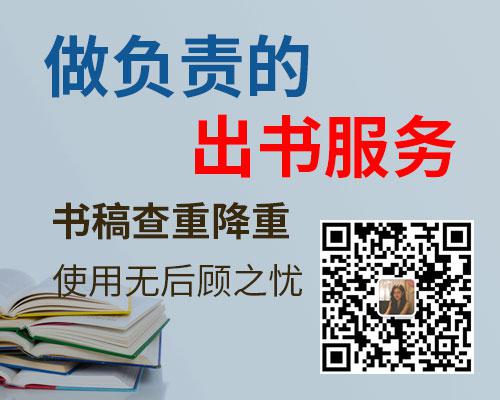
一、劇場性與文學性的分野與整合
在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等為代表的現代學者還未在文化界掀起關于時代文化轉向之理論前,作為一個整體概念的戲劇(DRAMA),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至二十世紀初,自始至終實際上一直是一種分分合合,但易被忽視的變化體。二十世紀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西方對于劇場與戲劇的概念界定有所區分,但始終沒有被擺在亟待解決的重要地位上。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解釋了悲劇、喜劇為何,而非籠統定義了戲劇的概念。但亞氏將悲劇放置在詩歌的類別下,一定程度上默認了悲劇作為戲劇詩有一種歸屬文學領域的特質。而在關于悲劇的定義中,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具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
戲劇論文范例:戲劇藝術傳播的移動媒體應用方式探析
而其中的行動,其實也就等同于情節性。行動的起承轉合、首尾發展,其實都是變相地承認了文本文學的功用。自此之后,身體表演方面的功用退居其次,戲劇文學成為歐洲戲劇發展史上的關鍵重心。古典主義戲劇時期,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提出了古典主義戲劇創作法則——“三一律”,他認為戲劇“應該早點題,只表現一個故事,在固定地點和一天時間內完成。”這一規則在文藝復興時期被發展,同樣鞏固了文學性。
即便是莎劇對“三一律”有所背反,也是在文本中心制基礎上的再創。萊辛雖然部分提到了對劇場演出的要求,認為表演應該具有思想內容且有控制感情的本領,但他論述的中心依舊是“性格”,而性格卻依舊歸屬于戲劇文學的創作領域。自此之后,自然主義、現實主義,乃至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法與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它們雖然提出反文學、去文學的理念,但依舊是以文學來反對文學。以貝克特《等待戈多》為例,劇本意旨中的無意義是借助對話(文學媒介)傳達,實際上,它本身的反常完全依附在文本基礎上,是基于劇本要素的斟酌、思考。如果剝奪臺詞,剝奪環形敘事結構,戈多何時到來也只是一句毫不重要的發問而已,原劇能量難以傳遞釋放。
尤其是當西方19世紀劇作法理論逐漸自成脈絡后,布倫退爾在《戲劇的規律》中提出的意志沖突說、勞遜將人的意志沖突擴大到社會性沖突、阿契爾在《劇作法》里強調的激變論,以及弗雷塔克《論戲劇技巧》中所論述的金字塔公式(介紹、上升、高潮、回復、結局),都是將戲劇這門藝術與戲劇文學劃上等號,劇場性的一面被無形忽略。然而另一面,當戲劇成為戲劇文學的等同詞之時,西方劇場導演通過自身的排演實踐,同樣在潛移默化地挖掘著關于戲劇劇場性的特質。法國自然主義劇場藝術的奠基人,也是提出并確立導演職位的安托萬,在創立自由劇場的同時,宣告了現代歐洲第一個實驗性劇場的成立。邁入20世紀,雅克·科波建立他的老鴿巢劇院,以實現在表演基礎上的綜合藝術性戲劇之理想。
德國導演萊因哈特沿襲瓦格納總體戲劇的思想,鮮明地體現了演出自身的完整統一性,以及統一的導演藝術構思,將戲劇歸還到現場性的劇場藝術領域中。而放眼東方戲劇范疇,源自酬神、娛人的宗教祭儀的戲劇傳統,發展到明清巔峰時期,“湯沈之爭”所討論的案頭之曲、場上之曲,后來也逐漸被視為不同創作風格的曲學流派。即便有不同流派的紛爭,但東方戲劇從來沒有明顯地在內部劃出清晰的藝術界限。無論是曾經啟發阿爾托的巴厘戲劇,還是間接影響布萊希特的中國戲曲等等,它們都以綜合性藝術的面貌出現。
梨園觀眾在乎的不僅是唱本的文雅精妙與否,更看重的還有場上的藝術,觀眾的重心也會傾向戲曲演員的臺功。所以當后戲劇劇場時代來臨之后,面對被請下神壇的文學性,戲劇界陷入了更多對于劇場性、文學性的爭議中,也因此衍生了關于劇場(THEATER)與戲劇(DRAMA)的更多界定爭議。雖然兩者在20世紀之前一直處于分合交織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但當戲劇轉向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時,關于戲劇與劇場的爭議難免更為激烈、明顯。當文學性不再主導戲劇時,戲劇為何?
二、當代視野下對“戲劇”概念的再定義
關于當代視野下“戲劇”為何的問題,筆者選取“劇藝”這個詞以貼切論述。劇藝中的“劇”既指的是戲劇,也指劇場,它適合放到今天國際視野下的戲劇界中加以闡述。戲劇首先是指戲劇文學,然后由特定的演出空間(即劇場)將其呈現出來。因此,文學性和劇場性是戲劇創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兩重要素。但是從戲劇史的變遷來看,文學性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然而劇場性作為戲劇文學過渡到劇場演出(即戲劇)的重要參考,也尤為重要,它是作品從戲劇文學文本發展到整體戲劇作品的引導性特質。
二十世紀以來,戲劇的文學性和劇場性開始被重視起來,學界逐漸將其界定與區分,但是始終沒有得出定論。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后現代主義戲劇開始出現,從阿爾托的《殘酷戲劇》到雷曼的《后戲劇劇場》,戲劇的劇場性開始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去意義深度與去文化深度的后現代思潮逐步瓦解了戲劇邊界,導致了舞臺與文學的嚴重割裂,從而引發關于戲劇定義的學術討論。但在當代視野下,戲劇的文學性是不是就此被消融呢?顯然不是,以羅伯特·威爾遜為例,其《睡魔》、《沙灘上的愛因斯坦》等作品雖然強調觀演體驗的劇場性,通過“視象”來展現,但是其核心仍然具有文學性內核,威爾遜并不排斥文學,也不反感經典文本。雖然《沙灘上的愛因斯坦》并沒有直接敘述愛因斯坦的故事,但是其敘事元素仍然隱含于視覺呈現之中。
威爾遜作為雷曼指定的后戲劇劇場導演,他的作品雖然注重劇場性地位的提高,但并未完全拋棄文學性,只是做到了劇場內各元素的平等運用,將曾經被視為權威中心的文本請下神壇,雖然沒有從前突出,但文學性始終從未消失在劇場中。隨著雷曼的《后戲劇劇場》的出現,戲劇和劇場的對立差異更明顯。尤其在劇場性與文學性的界限長期模糊的中國,引起軒然大波。關于戲劇的劇場性與文學性的爭論中國自古便有,“湯沈之爭”便是重要的案例,但是結果顯然是文學性取得了勝利。
近年來,國內關于劇場性和文學性的問題因為《后戲劇劇場》的引入而再次回歸學術討論的中心位置。國內后現代主義戲劇并未像國外那么多,在早期也有部分人認為后現代主義戲劇是對劇場性主體地位的確立,以及對文學性的徹底剝離,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戲劇不完全是戲劇文學可以概括的,它不是文字學理論,歸根結底是屬于藝術的,且是融合多種藝術門類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因此不能過多等同于文學性。
同時來說,劇場不是展演藝術,不是跨界、跨領域的表演行為,不是在一個特定的看場看一出體操表演,但它還是需要一定的范圍限制,盡管戲劇需要在劇場內演出,但是仍然需要一定的文學性鞏固。戲劇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文學性體現為其情感化形式與藝術化形式,體現其文學性的戲劇文本的內核是以人類生存狀況與命運為基點,以人類的苦難和情感為關注點,以建構人類精神和價值為主旨點的。文學性為戲劇提供內在力量的支撐,拓展其藝術深度和廣度。戲劇的劇場性能否有力突出,舞臺效果能否最佳地展現出來,能否潛移默化地去影響受眾,是衡量戲劇文學成就高低的標桿,劇場性作為視聽表現手段,直接將戲劇這種藝術展現出來。
以劇場排演作為傳播方式,是戲劇與其文學樣式的分水嶺。劇場性作為戲劇外在力量的展現,同樣是不可缺少的。作為斯叢狄的繼承者,雷曼的《后戲劇劇場》是對斯叢狄《現代戲劇理論》的續寫和完善。雷曼描述的后戲劇劇場理論中,并沒有排斥文學性。雷曼認為后戲劇劇場的文本和情節應該“向劇場敞開自己,詞語被視為劇場中聲響的一部分。”他提出文學性在劇場中只是作為符號化的展現,因此雷曼只是將文學性從戲劇的中心地位去除,將其視為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許多試圖割裂或忽視文學性的后現代主義戲劇,卻在一定程度上有極端化強調劇場性的嫌疑,曾經居于主體地位的戲劇文學性與戲劇劇場性互換,以至于很多后現代主義戲劇流于俗套或者不明所以,從而無法感染觀眾。戲劇既是戲劇藝術也是劇場藝術,只有文學性的內在支持與劇場性的外在呈現結合,二者相輔相成、地位平等,才能使戲劇區別于其他文學樣式,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從而更好地發展。所以當代劇藝,需要的是一種綜合、辯證的融合,比如謝克納的環境戲劇、奧古斯都·波瓦的被壓迫者戲劇就是權衡了兩方、處于中間的類型。當代的戲劇研究不能再如過去,極端地對文學性或劇場性做出明確辨異。從現代一路至后現代、后戲劇時代,在藝術的全球化、跨界趨勢下,劇場性已然與文學性趨于融合,難分難舍。所以筆者認為,今天我們用“劇藝”這個概念來描述當下戲劇劇場藝術更為合適。
參考文獻:
[1]奚牧涼.“劇場性”和“文學性”如何共處?[N].北京日報,2017-06-15(015).
[2]麻文琦.文學性與劇場性之爭到底在爭什么[N].文藝報,2019-11-22(003).
[3]劉家思.劇場性:戲劇文學的本質特征[J].四川戲劇,2011,(01):43-48.
[4]高子文.戲劇的“文學性”:拋棄與重建[J].戲劇藝術,2019,(04):1-11.
[5]周珉佳.戲劇“文學性”、“思想性”、“劇場性”之辨析[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09):203-211.
[6]漢斯·蒂斯·雷曼.后戲劇劇場[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作者:黃福彬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