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廣瀨淡窗與王維漢詩比較研究
時間:2022年01月12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日本漢詩發展深受中國漢詩的影響,于江戶時代達到頂峰。本文從題材、意象入手比較研究日本江戶時期漢詩人廣瀨淡窗與唐朝詩人王維的漢詩,發現兩人詩中地理空間的形成很大程度受原生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其影響機制為主要自然地理環境主導漢詩人的環境感知,漢詩創作廣度與文學家所處地理環境廣度呈正相關,漢詩在地域擴散過程中中國作為文學源地始終占據主導地位。
【關鍵詞】漢詩;文學地理學;廣瀨淡窗;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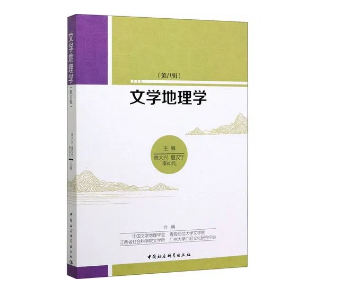
較歷史地理學、文學史等學科分支而言,文學地理學作為從空間維度解釋文學內在聯系的一門學科,同樣具有極大的學術前瞻性和發展意義。加快對其研究有利于促進文學地理學作為文學下設二級學科的早日建成,更好為研究我國和世界文學發展規律做出貢獻,也有助于在世界一體化深入推進的當今國際環境下,為促進文化理解和交流提供中國智慧。廣瀨淡窗和王維兩位詩人文學造詣深厚,在生活地理環境和藝術風格上具有諸多相似點,具有較高的比較研究價值。本文選取兩位詩人的漢詩作為研究對象,主要采取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如文獻研究法、地理意象研究法、空間分析法①等進行詩人、作品分析。
一、廣瀨淡窗與王維漢詩地理空間及其要素
廣瀨淡窗(以下簡稱廣瀨),名建,日本豐后日田人,終生不仕,江戶時代末期著名教育家,有“西海詩圣”之稱。主要著作有《遠思樓詩鈔》《淡窗詩話》等。其漢詩多為旅途風景所感及感懷詠史之作。詩風清淡幽遠,情勝于理,詩中有畫。
其主要詩學主張為講求性情和氣象,描寫實景,精思錘煉,提倡性情性靈、格調風雅、敦厚之旨。王維,唐代著名畫家、詩人。字摩詰,河東蒲州人,世稱“王右丞”。又與孟浩然同為盛唐山水田園派代表詩人,并稱“王孟”。王維是全能型詩人,在詩、書、畫、樂及佛學領域造詣頗深,有“詩佛”之稱。其前期詩歌雄渾開闊,較多表現建功立業和社會現實,后期則轉為山水田園詩,描寫恬靜優美的農家生活。其詩音律和諧,兼具禪理、畫意與詩情。
本文選取了《王維詩鑒賞辭典》中的60首漢詩和《廣瀨淡窗漢詩集》中《遠思樓詩鈔》初編中的328首漢詩,從其題材、意象等入手進行比較分析。從題材類別看,王維漢詩所涉題材包括山水田園詩、邊塞軍旅詩、贈別唱酬詩、懷古詩、感懷詩、應制詩,廣瀨包括行役詩、感懷詩、題贈詩、懷古詩、詠景詠物詩,王維要更廣。從各題材占比看,感懷詩、山水田園詩分別在廣瀨和王維漢詩中占比最高。感懷詩主要側重于作者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具有很強的主觀色彩,而山水詩則側重于刻畫自然風物,具有很強的自然屬性。
同時“田園”“隱居”等也使這類詩打上一定人的烙印,更傾向于追求自然和人的調和之美。在意象類別上王維比廣瀨多出政治軍事類,與王維漢詩中含有邊塞軍旅詩這類題材而廣瀨不含有相吻合。從選取最多的意象類別看,兩位詩人均為自然景物,但在占比上廣瀨58%高出王維約12%。再對其中水、山及動植物和氣象類意象進行細化比較,廣瀨占比均高出王維,平均超出3.83%。除自然意象外,專有人名地名意象兩位詩人也存在一定差異,廣瀨11.0%,王維8.3%,占比差異2.7%,與自然意象平均超出占比具有一定的差異相似性。再對意象做具體分析,廣瀨所選取的意象相比王維具有三大顯著特征。
一是意象中具有大量的中國元素。廣瀨漢詩中出現的意象本應以日本的意象元素為主,但其中卻夾雜大量的中國元素。這一特征在專有人名地名類意象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范蠡、嫦娥、孟軻、嵇紹、張良、王維、李白等人名,淮海、隈川、泰山、滁州、建康等地名。更有不少懷古詩直接選取中國歷史作題材入詩,如《題晉武帝乘羊車圖》《題伍子胥圖》《讀淮陰侯傳》等。
二是存在大量化用中國詩句或典故的現象。如《病起宴門人作》中“半宵三起何辭苦,一飲千鐘未報勞”化用歐陽修《朝中措•平山堂》的“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鐘”,《春日奉懷東都羽倉明府》中“堤柳風輕春試馬,檐花細雨夜論文”化用杜甫《醉時歌》中“燈前細雨檐花落”一句。典故類化用則有《九月七日訪有臺》中的“子猷乘興好相過”化用王子猷雪夜訪戴;《送兒謙游讃歧,因到備后,謁見茶山翁》中“我亦桑弧蓬矢志”②直接引用“桑弧蓬矢”這一典故。其詩下所載評論也往往以“漁洋(王士禎號漁洋山人)風致,以神韻勝(筱崎弼評)”,“似聞摩詰笑于泉下(龜井昭陽評)”等來贊揚其漢詩。由此可見廣瀨漢詩與中國漢詩乃至歷史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
三是在意象的語言色彩上,廣瀨所選詞語如蓂、娵隅、秔稌、縞綦、蜩蟷等相比王維要更為佶屈聱牙,在詩中并非十分自然。《孟春十六日草堂集得忙字》一詩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一葉蓂飛春載陽,喜君相訪度濠梁。草堂幸值經營華,隱士況無慶賀忙。冰面娵隅浮淺渚,梅邊觳觫放橫塘。今年雅會從茲始,詩興應追長日長。③一日詩人與朋友會于草堂吟詩,欣賞孟春之際冰雪消融的初春景致,表達了詩人對友人造訪,萬物復蘇的喜悅。全詩基調歡快,瑞草飛舞,春光和煦,魚兒從冰面探出頭來,水塘邊上,牧牛在悠閑地吃草。這時應選擇曉暢明快的意象來負載更多的情感信息。蘇軾稱贊王維“詩中有畫”,其實質便是稱贊王維成功運用意象疊加,用繪畫的“空間性”來表現詩的“時間性”。
但就這首詩而言,明顯可以發現娵隅、觳觫兩個意象的選取不夠恰當。從語體色彩看,兩詞相對都較生僻且不易理解,使得本應明快的氛圍凝重化。從詞義角度看,娵隅是我國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對魚的稱呼,具有較強的民族色彩,廣瀨在此使用屬詞義理解不當。從修辭角度看,用雙音節來表達單音節即可表達之意,不夠凝練更降低了美感。再將此詩與王維的漢詩加以比較會有更深的體會。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積雨輞川莊作》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④第一句寫積雨天氣下的輞川山野。漠漠廣布的藍色水田,白色翩翩起舞的鷺鳥,樹林陰翳,黃鸝鳥婉轉歌唱。從色彩上看,涵蓋了藍、白、綠、黃四種顏色,空靈秀美,一幅引人入勝的夏日輞川山水圖景。從動靜上看,水田是靜態的面,白鷺和黃鸝是動態的點,二者一取其態,一取其聲,樹林又是靜態的線。
點、線、面相得益彰,聲色、動靜相互映襯,詩中有畫。第二句寫邊塞風光,用意象列錦進行構圖。大漠是一望無際的面,孤煙、長河是縱橫的線,而落日是大大的點。意象雄渾開闊而在空間上相照應,很好地體現了王維深厚的構圖功力。大漠的黃、孤煙的黑、長河的渾濁與落日的紅給人以視覺強烈的沖擊,表現出一種勁拔堅毅中又富有親切溫和的塞外奇景,令人叫絕。對比這兩句中王維所選取的意象,水田、白鷺、夏目、黃鸝、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均極為曉暢但具有“構圖特質”,能夠在色彩、聲音和外形等上極大豐富詩作的畫面構造。再對比娵隅、觳觫則十分單一,不僅不夠曉暢易懂,使畫面失去美感,更不利于意境營造。
二、廣瀨淡窗與王維漢詩中的地理空間構建
就某一具體作家而言,構成其創作空間背景的地理環境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該作家原生地的自然地理系統,二是該作家個人地理空間上移動之處的自然環境。分別以兩人的兩首代表作為例進行比較,整體把握其漢詩自然意象的不同藝術特色,試分析其背后的自然地理空間。數家籬落水西東,蘆荻花飄雨后風。日暮釣魚人已去,長桿插在石磯中。——《江村》休道他鄉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親。柴扉曉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桂林莊雜詠示諸生》⑤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渭川田家》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⑥這四首詩從自然意象占比看,廣瀨顯然遠遠高出王維。且不難發現王維在這部分自然意象中含有如牛羊、雉、麥苗、蠶等大量極具農業生活色彩的自然意象,相比廣瀨詩中蘆荻花、風、雨、川流等純自然意象,這類意象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業生產而存在,獨立性較低。
從意象作用看,《江村》吟詠水鄉風光。蘆荻花飄,夕陽西下,風雨中獨自的垂釣者已然離去,只剩下一根魚竿插在石磯之中;《桂林莊雜詠示諸生》將自然風光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描寫了作者年輕時和同學親密無間的生活情景。兩首詩中的自然意象均非脫離作者生活的獨立描寫對象,而存在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日常之中。這說明自然地理環境與作者生活具有很強的交融性,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對其描寫看似是吟詠自然風景,其實質是刻畫作者趣意橫生的鄉村生活。
再來看王維漢詩的兩首詩。《渭川田家》中的自然意象以農業意象為主,主要描繪閑適自樂的農家田園生活;《鳥鳴澗》以動襯靜,極具禪理,重在刻畫月夜春山的“靜”字,不難發現王維詩中之景與作者存在較強的距離感。作者以“物外之眼”對自然加以禪理或美學的審視,把視點放在自然之美本身。即使是描寫實踐性的農業活動,廣瀨作為實踐者,和同伴們一同砍柴、挑水,但王維卻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對田園生活加以刻畫。由此可見兩人山水田園生活詩的一大區別即實踐者和旁觀者視角的區別。對上述意象差異成因加以探究,自然環境因素無疑居于首位。
(一)原生地自然地理系統
廣瀨活動范圍為今九州大分縣西北部日田市。大分縣沿岸地區為瀨戶內型氣候,日田市年平均降水量在1800mm左右。相比處于暖溫帶氣候區,最高降水量均不超過1000mm的山西、陜西⑦,其降雨量遠超王維所在地降水。從氣溫上看,日田市處于海拔偏低的盆地,夏熱冬寒,早晚溫差大,冬季多積雪,春秋兩季常產生底霧。地形地貌方面,大分縣山地面積較多,地質構造復雜,東端為沉降式海岸;中部是鶴見、由布等新火山;西部地區則有日田、玖珠等盆地。其中日田市地處西部盆地,多山多溪流,被稱為“水鄉”。豐富的降水、冬雪、密布的河流、廣闊的山地以及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物多樣性塑造了廣瀨的審美和內心世界,使其生活與周圍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為其漢詩創作提供了靈感來源。如《耶馬溪》中“危峰拔地尖于筍,瘦樹巉巖短似苔。”
寫山巖的險絕高聳;《七月十五夜南村新居作》中“峽云多變態,山月無常明。”寫山中氣候的變化多樣;《鶴》中“朝游云水暮蒹葭,島嶼洲汀總我家。”寫居住環境的水網密布等,無不緊扣自然地形地貌、氣候水文抒發作者的感慨。王維的主要活動范圍在今山西、陜西一帶,即關中、三晉地區。屬于三晉文學區⑧的王維,其文風必然帶有該文學區作家的一類共同特質。山西具有的文學家生命氣質的自然地理環境影響因素主要有兩點⑨:
一是山西地理單元的極強封閉性。二是盆地、河流眾多。另一方面高大的地理屏障又使山西免受戰亂破壞,大量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其政治區位優勢更是在唐代達到了一個高峰。因此山西文學家所具有的一大顯著特征即是重農崇實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識。不同于廣瀨,作為封建士人的王維無須親身從事生產勞動,客觀上也使他不可能將自然融入為日常生活,而只能作為一種廟堂之外短暫的治愈之所。對比如張籍《江村行》中“水淹手足盡有瘡,山虻繞身飛飏飏”寫江南多水,農夫整日在水中勞作痛苦的情狀,白居易《觀刈麥》中“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寫炎炎烈日下農夫勞作的“田園之苦”,王維更多著眼于“田園之樂”,即田園的閑情逸趣等美學價值,而非反映勞作生活的實際感受。王維另一主要活動地區在今關中平原一帶。作為我國最早被譽為“天府之國⑩”的戰略寶地,該地屢受封建王 朝的政治青睞,從而使此地的文學家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感。王維雖非中原文學區⑪文學家,但長達二十余年的生活使其作品同樣表現出該地區文學的基本特性。如應制詩《酬郭給事》的出現;《老將行》《出塞作》對于軍旅生活、報國殺敵的謳歌;《渭川田家》《積雨輞川莊作》對農業生活的刻畫等諸多題材意象差別大都是基于山陜兩地的自然地理環境這一內在深層邏輯。
至于廣瀨詩中頻繁出現的中國漢詩意象和部分佶屈聱牙的詞匯則不難解釋。漢詩作為中國本土的文學形式,本就建立在中國大量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學景觀和歷史典故之上。如廣瀨的漢詩中就曾多次出現“江南”這一意象,對其運用也早已不單單是指地理上的“江南”,更多是借其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來寄托情感。劍門關、長安、輞川等也是如此,脫離單純的地理指向而更多負載其文化意義。日本漢詩人作為學習者,由文化差異形成的理解壁壘及地理空間的天然隔閡使他們難以親身領會漢江、岳陽樓、輞川、長安等文學景觀的豐富意蘊,不能自如運用中國元素為漢詩創作服務。
(二)作家移動地理空間具體自然環境
前文提到王維漢詩無論是所涉題材還是意象,其多樣性都勝于廣瀨,對其成因加以探究,自然環境因素無疑居于首位⑫。王維足跡遍布今山西、陜西、甘肅、河北、河南、江蘇、湖北、湖南、廣西等中國多地,其空間地理行跡無疑要遠遠大于廣瀨。自然環境影響文學家氣質,又繼而影響到他們對題材的選擇乃至于文風⑬。
從這個角度而言,王維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相較于廣瀨無疑是多樣的。這些豐富而鮮活的自然地理環境陶冶了他的人格特性,使其在漢詩創作中帶有不同地域自然地理環境的鮮明色彩。相較之下廣瀨的漢詩中雖然存在數量可觀的如《送田有年之長崎》《訪咬菜石翁》《八月十五日謁大園神祠》等行役詩,但其行旅活動范圍極小,是在一定具有高度相似性的自然環境中進行內部移動,其所到之處風物并無大的差異,這決定了他無法具有王維那樣廣闊的地理視野和詩歌創作題材。
再者,基于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和科學技術水平,江戶時期德川幕府嚴格實行海禁⑭,且廣瀨身體欠佳,其活動范圍很難超出日本。客觀上就中日兩國的自然地理環境多樣性而言,日本自然也遠小于中國。縱觀整個日本漢詩的基本脈絡,很少有漢詩人能達到中國詩人在題材選擇上的多樣性。因此中日兩國的客觀自然地理環境差異和廣瀨主觀的地理空間移動的狹窄性是造成兩人漢詩題材和作品地理空間多樣性差異的主要原因。
三、結語
由以上研究我們發現地理空間對于漢詩創作的一些可能存在的影響機制。一是所處主要自然地理環境主導漢詩人的環境感知、審美心理和創作空間,其創作不能脫離其所處的一定地理環境。二者相較,王維身處三晉和中原文學區表現出強烈的重農和政治傾向,廣瀨則更多表現出對于自然山水、氣象、動植物的關注。二是漢詩創作廣度與文學家所處地理環境廣度呈正相關。廣瀨身處島國相對自然環境單一且自身遷徙范圍較小,相比于經常游歷,領略不同自然風貌的王維創作廣度要有所遜色。三是漢詩在地域擴散和接受過程中,中國作為文學源地始終起不可替代的主導地位。廣瀨在漢詩中大量使用中國元素的同時又存在對于意象運用不夠自如的情況。
作者:于海鵬程濟雯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