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在魯迅翻譯思想中的體現
時間:2021年10月11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內容摘要:每一位譯者在翻譯中都追求使譯作對等于原作,而絕對對等在就原作的內容或是讀者的反應而言均不可能存在。 因此,對等適度就成了譯者在翻譯時所遵守的主要理念。 而原作、譯者、讀者這三方都會對適度產生重大影響,造成了古往今來眾多派別的針鋒相對,如異化與歸化、直譯與意譯的沖突等。 本文主要分析了魯迅在其翻譯過程中,在歐化和歸化策略以及直譯與意譯方法上不斷調整及尋求適度的理念,并借此提倡適度理念在翻譯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魯迅 適度 “歐化” “直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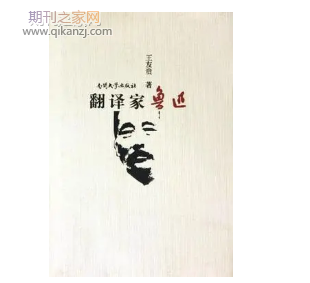
任何一位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都極為講究對原作的忠誠度,他們希望能夠原原本本地傳達原作的意思。 換言之,也就是希望自己的譯本能夠和原作對等。 然而,大量分析表明,這種對等絕不可能是常量,而是變量。 在受到原作本身文化內涵和背景的限制之外,譯者母語的文化背景和讀者的理解能力都會導致這種適度的平衡有所偏頗。 這種適度可以體現在對原作的忠誠度上,對譯文的可譯性上、和對讀者的可接受性上等等。 不同譯者對于適度的理解不同,亦或是對于翻譯有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排序,勢必會導致矛盾。 因此,如何正確界定這種適度,也變得眾說紛紜、難分伯仲。
文學論文范例: 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葛浩文的譯者主體性探析
作為在中國翻譯史上最具有“爭議”的翻譯家之一,每當提起魯迅,接踵而至的似乎就是人們對他“硬譯”的詬病,認為魯迅過分追求“異化”翻譯。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魯迅采取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并不是一味的“異化”和“硬譯”,相反,他是在“異化”與“歸化”、“直譯”和“意譯”中的黃金分割點上展開的翻譯。
一.“歐化”與“異化”策略的異同
魯迅在翻譯中所提倡的“歐化”,并非現代譯學中韋努蒂主張的“異化”。 “在忠實原作、保留源語文化異質性方面,歐化和異化沒有差別,它們都是與歸化相對而言的。 ”然而,兩者在目的性上有根本不同,韋努蒂強調在世界文化權力不對等的當下,翻譯勢必會傾向于強勢國家,造成翻譯的單一化和強權化,因此他提出“異化”主張,反對強勢國家文化的霸權以及保留弱勢國家文化的獨特性。 魯迅則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為了改造中國語言和文化,進而喚醒大眾,他借用外國原汁原味的源語文化來豐富中國自身文化的缺憾。 也就是說,韋努蒂站在弱勢國家的立場上,強調翻譯文化的多樣性,而魯迅,則強調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學習,借以改變自我命運。 綜上,兩者在出發點上有較大的差異,我們不能把這兩者的概念加以混淆。
二.“歐化”策略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方法——“硬譯”
“硬譯”一直被認為是魯迅提倡的翻譯方法,他認為“硬譯”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譯。 ”魯迅認為翻譯要忠實于原文,不僅要逐句,甚至逐字對應,句法結構、句子順序也要一一對應。 他的翻譯觀和“直譯”在忠實原作上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在一定程度上,“硬譯”可以看作是“直譯”的極端表現。 另外,“硬譯”的產生來自于那個時代魯迅心中對立人、立國、立民的深切渴望,他渴望通過借用異域語言來改造中國語言,通過外來文化的輸入,創造新文化。 可是翻譯帶來的效果是漫長持久且成效甚微的,因此他寄希望于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讀者幫助推動語言“歐化”的大眾化趨勢,希望他們能夠帶著“硬著頭皮看下去”的精神好好地接受和吸收這些異域語言文化。 然而,這種“硬譯”帶來了譯文晦澀難懂的問題,非但沒有達到該有的效果,反而為魯迅帶來了數不清的輿論批判。 譯者梁實秋就曾猛烈抨擊過魯迅的翻譯方法,并將之與“死譯”、“曲譯”相提并論。
三.適度的體現
魯迅在其翻譯實踐中并非通篇采用“歐化”策略和“硬譯”,這種翻譯方法指導下的譯文只在極少數,更多地則是在以忠實原作為基礎上,“歐化”和“歸化”相結合、尋求“適度”的策略翻譯的,尤其是在兒童文學作品上的翻譯,魯迅更是追求“去歐化”。
1.一味“歐化”
1907~1909,《域外小說集》出版,標志著魯迅“歐化”翻譯策略的正式實施。 此后,魯迅大部分作品仍采用“直譯”翻譯,而只有少數作品,如《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作為“硬譯”的代表,卻激起了梁實秋等人對于“歐化”和“硬譯”的抨擊,引起了著名的翻譯論戰。 而事實上,魯迅本人在對“硬譯”做出的少量實踐中,就已經明白了它的局限性:
第一,魯迅對于“硬譯”作品的受眾有明確的限制和過高的期望。 “外來語匯的引進應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譯者只能為這個過程提供素材,適時引導,而不應把讀者一時還不能接受的東西一股腦兒地強加給他們。 ”這也就是說,魯迅在翻譯中僅僅只考慮到了讀者接受的動態性,即它對語言、文化方面積極的推動作用,包括文化的“融異化同”的功能,而沒有考慮到讀者接受的保守性。 正是這種保守性阻礙了異域文化的傳播,也給魯迅帶來了鋪天蓋地的指責。
第二,魯迅“硬譯”方法中過分強調句法一致,忽略了文化可譯性及文化可接受性。 中西文化有很大的差異:
首先,英語注重結構的嚴謹性且多用被動句和復合句,而漢語注重意思的表達則更傾向于用主動句和簡單句,如果兩者在翻譯時一味苛求一致,則會導致漢語句子冗長并且成分贅余,使句意晦澀難懂。
其次,中西文化背景截然不同。 在西方國家人們都很喜歡養狗,因此他們常用狗來自稱或互稱。 而在中國,自古以來,狗便是“令人嫌惡”的,和狗相關的也多是貶義的詞語,如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等。 所以,在英語中,“You are a lucky dog.”若是“直譯”過來便是,“你是一只幸運的狗”,讓人很不舒服。
綜上,魯迅在實踐過程中便已發現了“硬譯”的缺陷,他開始尋找“歐化”和“歸化”的適度平衡點。
2.“歐化”和“歸化”結合
在經歷了“硬譯”翻譯的失敗后,魯迅認識到:“翻譯一直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其間異域文化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體易于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印記”。 因此,他在詩歌和戲劇的翻譯上放棄了“歐化”策略,認為通俗易懂的譯文才是最合適的。 他的第一部戲劇譯本《一個青年的夢》中這樣寫到:青年問:“這里有什么事,”不識者答:“有平和大會呢。 ”全篇都采用極其簡單的話語,人物對白明了。 而在文藝理論翻譯中,魯迅也認為意譯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專業術語,否則讀者不能掌握其意思。 由此可見,魯迅在詩歌、戲劇、文藝理論翻譯上的轉變表明他已經尋找到這種適度——即讓讀者能夠讀懂作為底線,“保持異質文化”的“歐化”翻譯才是他以及當時所有主張“歐化”翻譯的譯者的目標。 因此,魯迅采用了“歸化”翻譯。 而正如鄭振鐸所說的,“忠實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縱”是每一個譯者都應追求的最高目標。
3.“去歐化”
魯迅在兒童文學上主張“去歐化”,他認為孩子是未受傳統文化迫害的,最有希望的一代。 因此,他充分考慮到了孩子的接受能力,選擇能夠滿足孩子新奇心理的內容,采用輕松淺顯的方式翻譯。 “云彩還在發光。 東方的天做深藍色。 柳樹沿著岸站立成行。 ”這樣的表達已絲毫看不出“歐化”的痕跡,只是魯迅自己曾說過:“可惜中國文是急促的文,話也是急促的話,最不宜于譯童話; 我又沒有才力,至少也減了原作的從容與美的一半了。 ”由此可見,正是因為魯迅精益求精的鉆研精神和對“歸化”翻譯的采用,創造了他在兒童文學翻譯上的巨大成就。
總體來看,魯迅在翻譯史上經歷了一段比較長的黑暗摸索期,為實踐“歐化”策略付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他在實踐的摸索中,不斷調整自己的翻譯方法及策略,最終發現了適度這一理念,將“歐化”和“歸化”相結合,為未來中國的翻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豐富的理論及實踐指導。 因此,任何譯者都應當同魯迅一樣,在實踐中發現最適度的一套翻譯標準,并努力找到“信”和“達”之間的動態平衡點。
參考文獻
[1]馮玉文著,《魯迅翻譯思想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15.144.
[2]魯迅著,《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00.
[3]魯迅著,《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者附記》,《魯迅著譯編年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9.24.
[4]楊曉榮著,《小說翻譯中的異域文化特色問題》[M].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3.69.
[5]傅斯年著,《藝術感言》,《新潮》[N].1919(03).
[6][日]武者小路實篤,《一個青年的夢》,《魯迅譯文全集》[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09.337.
[7]鄭振鐸著,《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小說月報》[N].第12卷第3號.
[8][荷]望·藹覃著,《小約翰》,《魯迅譯文全集》[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8.
[9]魯迅著,《譯文序跋集·池邊·譯者附記》,《魯迅全集》[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02.
作者:黃榮榮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