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電影:作為影視教育實踐的一個渠道
時間:2020年02月28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一、學院“正統”與網絡電影創作關系的變化
網絡電影在21世紀初期出現時,在以膠片美學為正統甚至還來不及過渡到數字時代的影視專業院校或者綜合性大學的影視和藝術院系中,其接納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總體來看,以精英文化自居的學院“正統”接受網絡電影大致與網絡電影自身發展的過程緊密相關。具體來看,有三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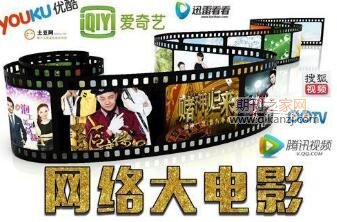
(一)質疑階段:網絡電影是不是電影
網絡電影是伴隨著網絡的普及,影像創作門檻降低等因素形成的一種視聽傳播新形式。但是從它作為一個現象被關注后一路發展,到2014年之前,都是一種雜草叢生的狀態。當時關于網絡電影的研究文章表述:“其操作模式具體為:由品牌商出資,邀請新晉青年導演和豪華幕后班底拍攝,同時使用品牌代言人擔任主演,網站則整合娛樂資源,提供媒體支持和播放平臺。”[1]這種表述看出,當時的網絡電影中很重要的一種形態是廣告視頻。另外一種形式就是草根的創作,這種創作的質量更不具備可控性。從網絡電影面目模糊的出現開始,學術界的討論就沒有停止。
無論從當時的《電影產業促進法》的表述來看,還是學院派對電影本體的傳統認識來看,網絡電影都沒有完全被接納到“電影”這一藝術形態中來。“網絡電影不是傳統電影的網絡化。網絡電影是以網絡為最主要發行和播放渠道,以數字文件形式存在的,有一定故事情節,具備草根性、游戲性、整合性等特征,供網絡用戶觀賞和參與的一種新型電影藝術樣式。”[2]從這些定義來看,網絡電影在那個時期被認為是一種與高雅藝術關聯并不大的視聽形式,屬于膚淺、娛樂、快銷性的網絡現象。
而21世紀的前10年,我國高校教師的隊伍中,80后們還沒有登場,75后的教師也尚未占據話語核心,主要的高校老師是20世紀80年代高校畢業已經成長為重要學者的一批人,和80后的網生代不同,他們的成長和教育背景奠定了這批學者極強的精英意識,而這種精英意識也帶入到對“第七藝術”電影的理解和日常教授中。所以草根趣味占據了主要話語場域的網絡電影,并不被“學院派”們看好。但不容被忽視的一個萌芽是,在影視專業學生實踐中,一直進行的學生短片創作,因為網絡的普及和在線視頻的出現,在線平臺成為影視專業的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的一個重要渠道,從傳統學生作業轉型成網絡微電影為之后“學院派”接受網絡電影做了一些準備。
(二)緩和階段:面對觀眾才更重要
2014年到2017年,是網絡電影飛速發展的幾年,網民數量的增加、視頻網絡平臺的增加、網絡付費觀影習慣的養成等因素,使得網絡電影的數量激增,從2014年450部的上線量,到2016年2193部的數量[3],是一個飛躍。另一方面,網絡視頻的質量也在提升,2017年6月,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在常務理事會上審議通過的《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加強了監管、提升了網絡電影在平臺的準入門檻,2018年網絡電影的上線量下降,但總體質量有了提升,在2014年時作為網大的重要平臺的愛奇藝,提出了網絡大電影是在網絡上發行,時長超過60分鐘,符合電影敘事規律和國家相關政策法規,并以付費點播模式分賬的電影。[4]運營平臺通過實踐設置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也規范了網絡電影,網絡電影開始明顯分層,其中的一些精品,其投資規模,制作水準與院線電影持平,甚至有獲得龍標的院線電影找不到合適的院線上映機會,以網絡大電影的形式在線發行放映。
而另一方面,院線電影的特質也正發生著改變,在路陽、韓寒、徐崢、楊超、陳思誠等一批背景各異、創作風格各異的“新力量”的導演的影響下,院線電影呈現出這批導演“網生代”的特質,他們觀念上的開放性、意識形態上的包容性、思維上的多元性,置身商業大潮的現實性和世俗感性[5]等特點,讓院線電影更顯現出強大的商業特質,從微電影和網絡視頻開始入行的烏爾善、李蔚然、肖央、盧正雨等本身在電影創作中就有駕輕就熟的“網感”,網絡電影和院線電影的差異不斷縮小。事實上,除了這些聲名鵲起的新力量導演之外,還有大量和這些導演成長軌跡相似的、21世紀之后影視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從學生時代在網絡上展示自己的微電影開始,已經非常熟悉這一渠道和方式,畢業后成為網絡視聽內容的專業生產者,這些具備網絡時代特質的學子們轉變了過去的精英觀,認可電影作為商品的傳播價值,只有見到觀眾才是有意義的作品。
(三)合作階段:不可避免的融合
2017年3月1日,《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實施,在這部文化產業第一法中,也涉及了互聯網上放映的電影作品,之后一系列配套政策,一步步明確了網絡大電影的審核標準,以及先審后播的規定,并且網絡大電影與院線電影審查標準將統一成為一個趨勢。[6]規范的逐步實施,使得網絡電影的創作流程、創作工藝和藝術水準與傳統院線電影無差異。這一發展勢頭,讓“學院派”對網絡電影的偏見得以消除,從而有了“一視同仁”的可能。同時,經過了10余年的發展,已經有了10余屆學生從學校畢業,這些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們是伴隨著網生內容的發展成長起來的,不少學生畢業后的從業單位,就是網生內容產業鏈上的各個平臺,“學院派”們與網絡電影的制片、發行、放映等各個環節已經“水乳交融”無法割裂了。
同時,“數字化,網絡化,多媒體融合,分眾性和交互性,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最突出的改變是點對點傳播路徑的產生,每個傳播者既是傳播主體,也是傳播客體”。[7]這些85后和90后們,有著更強的個體意識,具備自由表達的意愿,網絡傳播的特質與他們的精神更為契合,在網絡上以影像作為分享內容已然成為年輕人的社交方式,網絡平臺的影像傳播與他們的氣質與習慣不謀而合。而越來越多觀眾養成了在線觀看的習慣后,平臺對網生內容的需求量進步一加大,加之監管的嚴格,對優質資源的需求更是迫切。這也使得網絡平臺將視線轉向了學校。騰訊、愛奇藝等知名平臺頻頻展開各種學校合作的活動,以期尋求更好地模式得到雙贏。
二、學院與網絡電影“聯姻”實踐的路徑
(一)劇本創作——最早涉入的環節
網絡電影最缺乏的是創意與內容,所以在2016年前后,“屯IP”“炒IP”成為潮流,在這樣情況下,許多的劇本創作的征集活動在校園里展開。騰訊的NEXTIDEA創新大賽從2012年發起,與影視相關的“NEXTIDEA青年影視人才計劃”已持續多年,其中最持續的“青年編劇大賽”至2018年舉辦了四屆,雖然整個大賽是面向16-35周歲的全球青年作者,但在推進大賽的過程中,更著力于與北京電影學院等6所藝術院校、清華大學等15所綜合院校建立專區合作。而愛奇藝、優酷、芭樂、華影盛視等網絡平臺都從2012年前后面向青年創作者,開展過各種形式的劇本征集和劇本獎勵。
因為相對電影創作的各個環節而言,面向學生的劇本征集可操作性最強,是能夠直接看到成果的一種形態。除了公開的劇本征集外,學生進入網絡電影創作的還有一些從事網絡電影行業的老師、學長們私下召集在校學生進行的劇本創作,一般已經有了劇本創意概念或者創作大綱。當然這種模式本身在院線電影創作中已經存在,而在網絡電影產量增長的時代,創作內容成了網絡電影而已。
(二)以劇組招募的形式
當下信息傳播和媒介渠道的多樣化,尤其微信群和朋友圈的出現,成為學生們獲取資訊的“主渠道”。多數大學生使用微信群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交流信息”,至于“滿足情感”等需要則是次要原因。[8]在以熟人為主要群體的微信群中,學生更易獲得“靠譜”的影視創作實踐機會,而相對于院線電影,網絡電影的門檻稍低,需求量又大,學生更易獲得跟組的機會。所以老師介紹、師兄師姐帶、朋友幫忙等等方式,許多在校學生以劇組招募的形式,獲得了網絡電影實踐的機會。
1.機構和學校之間有規劃地深度合作
相比于上面兩種更為偶發的實踐形式,在網絡電影創作機構以及放映平臺越來越品牌化的當下,這些機構與學校之間,有計劃地展開深度合作有了可能。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機構與學校間的合作形式,主要是通過機構點對點的設立基金,鼓勵學生創作;機構給出資金與項目,學校組織創作團隊;機構提供便利與傾斜,協助學生展開眾籌等形式獲得網絡電影創作資金和教學層面深入交流四種形式。第一種形式諸如愛奇藝與北京電影學院達成的合作計劃中包括設立基金,鼓勵學生原創內容;主打移動新媒體增值服務和內容提供商的量子云科技公司通過面向大學生的影視比賽,設立專項獎勵基金,鼓勵大學生們創作。第二種形式目前表現來看呈現得豐富多樣。比如在學校建立學生為主的創作工作室,承接機構的網絡電影項目,或者通過像杭州青年數字電影大賽這樣比賽,給獲獎學生提供創作資金,讓學生自行組織創作團隊。
第三種形式往往依托于一些知名的網絡電影眾籌平臺,如淘夢網、優酷眾籌等,這些平臺常常會舉行一些校園主題的創意征集活動,實際上是面向青年創作者尤其是大學生群體進行的眾籌活動。第四種形式,往往在影視專業院校更為廣泛,如愛奇藝對北京電影學院編劇大講堂的支持,使熟悉網絡特性,有豐富網絡電影創作經驗的人員走進校園,帶給學生一線的資訊,當然,其他的綜合性院校也有講座等各種形式的校園活動。
三、“學院派”進入網絡電影產業的現狀
(一)網絡電影已經和院線電影一樣成為“學院派”的一個“正統”選擇
近年越來越多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入行就是網絡電影,或者從影視廣告等行業轉向網絡電影,網絡電影已經和院線電影一樣,成為一個創業和創作相當繁榮的渠道。比較知名的就是拍攝《老男孩》的肖央,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在廣告業一段時間后,通過網絡視頻《男藝妓回憶錄》被觀眾所知曉,之后超高點擊量的《老男孩》也是網絡電影。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的王子,在經歷一段演員生涯之后,也是通過網絡電影轉型做的導演,其導演的首部網絡電影《末日情人》,當時在樂視網獨播獲得了極高的點擊率。
可以看出,除了少數在影視行業其他崗位有豐富經驗轉行做網大導演的外,目前進行網絡電影創作的導演大多是從專業藝術院校或綜合性大學藝術院系畢業,直接進入網絡大電影或者微電影行業的“學院派”。“學院派”們愿意作出這樣的選擇,除了網絡電影和院線電影的天然區格在逐漸打破外,網絡電影的投資規模和數量需求,使得尚未畢業或者剛畢業的“新人”同樣有機會挑大梁,相比過去通過廣告拍攝的磨礪或者在劇組各種“助理”的形式,現在畢業生甚至在校生,都有可能成為網大的主創。
(二)地方院校對通過網絡電影進行實踐的依賴度更大
地方院校,尤其是非藝術類的專業院校,無論是在校生還是剛畢業,獲得實踐的機會相比大城市和專業院校,更依賴網絡電影。通過對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的廣播電視學系、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數字媒體藝術系、浙江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藝術與傳媒分院下設影視藝術系的廣播電視編導專業這三所位于杭州市的學校的三個相關專業大三學生的問卷來看,在總數97份有效問卷的回答中,僅有65人是參加過影視相關的實踐的,這65人實踐的總次數達到了176人次,但大多數學生參加實踐的次數并不多,有3位學生參加了10次以上的實踐活動,在問卷回到中,85%以上的學生表達了“很難找到相關的實踐機會”。學生獲得實踐的機會主要來自于網絡視聽內容的網大、網劇以及微電影,在實踐的環節中以制片環節中的后期制作最多,而學生自行組隊的創作占了較大比重。
(三)“學院派”進入到網大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在網生內容的重要性被不斷提升的當下,進入到網生內容產業的各個環節已經是相關專業畢業生的一個重要擇業方向,除了制作內容之外,騰訊、愛奇藝、優酷等自制內容的創意、管理、發行、營銷等團隊,都有大量相關專業畢業的“學院派”。打造出《道士出山》系列、“二龍湖浩哥”系列等話題級的網絡電影作品,并獲得高效商業回報的愛奇藝資深制片人于泳洋,就是從中國傳媒大學數字媒體藝術專業畢業的“學院派”,他在網絡思維和學院經典之間成功突圍,成為網絡大電影的重要拓荒人。目前優酷土豆、騰訊視頻等各個環節,不僅僅有我國自產的學院派,更有許多從海外學習影視回來的“海歸學院派”。
(四)網絡電影的實踐對學生形成了負面影響
但不容忽視的是,網絡電影還是在洗牌和調整的階段,作品良莠不齊,而資訊發達的當下,學生們“跟組”的誘惑增多,“野路子”網大的創作邏輯和模式容易帶偏學生,無論是文化積淀還是技術層面,學生沒有足夠累積的情況下,這些實踐機會壓縮了學生在校時間,迎合市場,短、快、糙的制作容易將學生帶到一條浮躁又膚淺的道路上。
四、影視教育實踐在網絡電影中規范化的可能性
“學院派”的精英情結閃光而可貴,但互聯網思維的當下,如何將兩者保持平衡,并能使學生的實踐在規范化的道路上保持不脫軌,在實踐過程中雖然有些困難和障礙,但依舊有一些可控可行的路徑。
(一)大師監制把控的青年影人扶持
2010年優酷網推出了11度青春電影計劃,扶持了11部短片,引發了巨大反響。2016年,隨著微電影各方面理念和技術的成熟,全新的“微電影+”理念浮出水面,衍生出了網絡大電影的全新概念。實際上,伴隨著微電影熱的興起,由著名導演、影視公司、互聯網平臺等發起的電影計劃非常之多,有導演、編劇、表演、主題等不同的側重方向。除了11度青春電影計劃,還有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發起的CFDG中國青年電影導演扶持計劃,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發起的B20青年電影計劃,賈樟柯發起的添翼計劃、語路計劃,崔永元發起的新銳導演計劃,以及各路平臺發起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H計劃等。
這些電影計劃要么有政府背景,要么有大師搭檔“導師”,要么有商業巨頭支持,給入圍的青年影人提供資金、設備、技術、思路等全方位的支持。這些被扶持的青年影人,大多數是影視專業的畢業生,甚至在校生。非常難能可貴的是,這些電影扶持計劃并不要求青年影人迅速產出來獲得市場回報,而是希望他們洋溢出自己內心的渴望,做出有溫度、有情懷、有思想的作品,而不是快餐。
這與青年影人在高校中所形成對于電影價值的判斷非常接近,在這樣的扶持下,所創作的網絡電影自然成為一股清流。即便是這些網絡電影能獲得的關注有限,也沒能創造多少市場價值,但是,這卻為網絡電影“高品位化”提供了可能。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總得有優秀的影人為之付出艱辛的勞動,并且承受票房失敗的現實。網絡電影同樣會經歷類似的過程,并且互聯網的碎片化特色使得網絡電影比院線電影更加艱難,不過有一群經歷學院派打磨的優秀電影人,以及相對不計回報的電影扶持計劃發起者,未來可期。
影視方向論文范文:電影解說作品的著作侵權問題探究
網絡世界的逐漸豐富讓更多的娛樂方式展現在了大眾面前,很多網紅也就是通過對電影進行剪輯再加上幽默的方式進行解說,才可以在網絡上爆紅。但是也有相關報道稱,有幾家制片方控告網紅未經授權就采用盜版影碟改編電影,然而這些網紅始終堅稱自己的行為是合法的。到底這一系列的電影解說作品是否屬于侵權行為,是否可以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的方式來促進文化更好的傳播,下面文章就對此展開研究。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