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村振興的空間之維基于福建土樓修繕的案例
時間:2021年06月24日 分類:農(nóng)業(yè)論文 次數(shù):
摘要鄉(xiāng)村振興繞不開空間維度.通過福建土樓修繕的個案分析,展現(xiàn)了物理空間的修復(fù)過程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社會參與和鄉(xiāng)村再組織化,在解決地方問題的同時,賦予了空間新的文化活力.土樓修繕引起的連鎖反應(yīng)改變了鄉(xiāng)村面貌,呈現(xiàn)了在空間形塑、主體實踐、文化勢能機制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相互建構(gòu)的動態(tài)過程,凸顯了地方性、社會參與和文化活化的關(guān)鍵作用.
關(guān)鍵詞鄉(xiāng)村振興;空間;土樓修繕;鄉(xiāng)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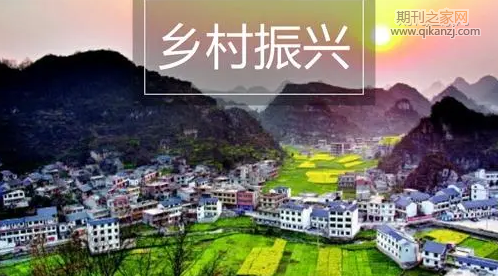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2018-2022年)»指出,鄉(xiāng)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jīng)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chǎn)、生活、生態(tài)、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zhèn)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gòu)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規(guī)劃中所強調(diào)的鄉(xiāng)村與城鎮(zhèn)“互促互進,共生共存”,部分原因恰恰是城市對鄉(xiāng)村的不斷侵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xiāng)村一直處在“非農(nóng)化”演化進程中[1].在城市化影響下,農(nóng)村傳統(tǒng)的社會空間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居住空間、教育空間、生產(chǎn)空間、養(yǎng)老空間等與民眾息息相關(guān)的各類空間不斷衰退和破敗,使村居環(huán)境喪失了生態(tài)活力[2].
鄉(xiāng)土社會結(jié)構(gòu)不斷瓦解,村落共同體日漸衰落,甚至有學(xué)者提出了“村莊的終結(jié)”[3].在“城市導(dǎo)向”的影響下,人們傾向于以城市為尺度丈量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成為落后的象征,成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導(dǎo)致了鄉(xiāng)村社會的病理化[4].在這種觀點下,鄉(xiāng)村要向城市看齊,致力于成為城市的翻版.然而,鄉(xiāng)村社會承載著鄉(xiāng)土建筑、聚落文化、宗法秩序等社會文化資本,鄉(xiāng)村生活方式中也蘊含著平衡城市生活的精神內(nèi)核和文化魅力,是承載著鄉(xiāng)情和鄉(xiāng)愁的精神故園[5],具有一種人居保育、文化維系、生命教育的家園價值[6].
因此,鄉(xiāng)村的歸宿并不必然是城市化、工業(yè)化,鄉(xiāng)村振興也不應(yīng)該是對城市的模仿,復(fù)制城市的生活[7],而是找回鄉(xiāng)村社會,探索與城市不同的鄉(xiāng)村發(fā)展路徑.隨著社會科學(xué)的空間轉(zhuǎn)向,空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鄉(xiāng)村振興不能忽視空間維度,正如列斐伏爾所說,如果不同時改變空間,那么“改變生活方式”和“改變社會”都是空話[8].
可見,空間與社會密切相關(guān).在傳統(tǒng)觀點中,學(xué)者們對空間與社會關(guān)系的論述存在兩種不同取向.一種取向認為,空間是社會的一般反映,是人的主觀性在空間上的投射.在這種認識下,空間是被動的、被決定的,是社會的附屬物和派生物.例如,涂爾干曾指出,空間具有社會性,是社會的構(gòu)造物[9].芒福德也曾將城市空間看作是社會活動的劇場[10].另一種取向恰恰相反,認為不是社會決定空間,而是空間決定社會.在蘇賈看來,空間具有構(gòu)建和轉(zhuǎn)換的規(guī)則,獨立于更廣泛的社會結(jié)構(gòu)[11],他過分夸大了空間對社會的建構(gòu)作用,因此被稱為空間決定論者.無論是社會決定空間,還是空間決定社會,都只是強調(diào)了空間與社會關(guān)系的一個方面,忽視了二者之間的雙向建構(gòu)和雙向生成[12G13].
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的動態(tài)所塑造的,社會參與了空間生產(chǎn),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xiàn)了各種社會關(guān)系.然而,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也不僅是社會關(guān)系演變的容器,而是社會能動的表現(xiàn),空間演化與社會重構(gòu)是相互影響的動態(tài)過程,質(zhì)言之,空間與社會具有一致性[14],空間結(jié)構(gòu)與社會關(guān)系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雖然社會與空間相互建構(gòu)的觀點已經(jīng)得到了學(xué)者們的普遍認可,但社會與空間依然呈現(xiàn)出主客分立,這就使如何連接兩者以破除二者之間的對立成為亟需破解的難題.哈維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chǔ),認為空間與社會的互動只有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才能得以實現(xiàn),他從社會實踐的角度出發(fā)闡明空間建構(gòu)的復(fù)雜過程并尋求改善當代社會的可能性[15].卡斯特也提出必須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理解空間[16].
空間不是僵滯的、刻板的、直接的固定空間,而是具有生成性的、社會秩序?qū)嵺`性的建構(gòu)過程[17].空間的實踐性體現(xiàn)了更多的人文關(guān)懷和積極的社會建構(gòu).通過社會實踐,人們得以參與到空間建構(gòu)中,改造人們生活和感知的空間.上述空間與社會雙向建構(gòu)的觀點為從空間改造入手重構(gòu)鄉(xiāng)村提供了理論依據(jù).由此視角出發(fā),鄉(xiāng)村振興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鄉(xiāng)村文明空間重構(gòu)的過程[18],鄉(xiāng)村公共空間應(yīng)該作為鄉(xiāng)土共同體生活重構(gòu)與振興的出發(fā)點[19].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學(xué)者們已經(jīng)意識到空間改造對于鄉(xiāng)村重構(gòu)的重要意義,但對于如何通過空間改造以實現(xiàn)鄉(xiāng)村社會的改變與振興仍然缺乏充分的探討,這是本研究得以開展的邏輯起點.
作為空間理論的重要奠基者,列斐伏爾在物質(zhì)空間、精神空間二分法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社會空間的概念[20],形成了物質(zhì)空間、精神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三元分析框架.Halfacree則將空間理論運用到鄉(xiāng)村研究,并提出了鄉(xiāng)村地方性、鄉(xiāng)村表征與鄉(xiāng)村生活所構(gòu)成的鄉(xiāng)村空間的分析框架[21].此外,李紅波等提出從“物質(zhì)空間G社會空間G文化空間”認識鄉(xiāng)村空間系統(tǒng)[22].龍花樓、屠爽爽則提出從空間、經(jīng)濟、社會三重維度進行空間重構(gòu)[23].既有文獻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但也存在不足之處.
其一,空間理論批判性有余,建設(shè)性不足.例如,列斐伏爾對資本主義抽象空間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對空間的改造以及因此造成的日常生活的異化[24].福柯以全景式監(jiān)獄的隱喻揭示了現(xiàn)代資本主義通過“凝視”對個體的規(guī)訓(xùn)[25],深刻分析了空間對社會的影響.列斐伏爾和福柯共同開啟了社會理論的空間轉(zhuǎn)向,對后續(xù)的研究者產(chǎn)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但二人的空間分析以批判為主,缺少與當下社會的連接,對空間改造的指導(dǎo)性不足.如何通過空間改造影響社會,為當下的鄉(xiāng)村振興提供路徑參考,是亟待研究的議題.其二,關(guān)于空間的分析框架,大多是結(jié)構(gòu)性的、靜態(tài)的,而非過程性的、動態(tài)的;即多是分析空間的不同維度或構(gòu)成部分,缺乏對于空間改造過程以及空間和社會互動過程的關(guān)注.
其三,既有研究中對行動者的主體性關(guān)注不足.由于行為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人類行為對空間同樣有著塑造與再塑造的作用.作為在空間內(nèi)生活的人,其主體性對于空間的形塑作用是巨大的.以往研究關(guān)注更多的是國家權(quán)力、資本權(quán)力對空間的影響,對于民間力量的關(guān)注則相對不足.可見,如何從空間入手改變鄉(xiāng)村這一問題還未得到滿意的回答,尚待進一步探究.土樓是福建鄉(xiāng)村地區(qū)的特色建筑,但隨著時代變遷呈現(xiàn)頹敗之勢.2015年起,福建云霄縣內(nèi)龍村的“好厝邊”項目通過土樓修繕致力于促進鄉(xiāng)村改變,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本文通過對此案例長時間的跟蹤考察,展現(xiàn)空間改造促進鄉(xiāng)土社會改變的動態(tài)過程,凸顯其中民間力量的主體性,并嘗試探索從空間入手助力鄉(xiāng)村振興的路徑.
一、案例:福建土樓的命運與衰敗的內(nèi)龍村
2008年,“福建土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受到了空前的重視.由于其獨特的建筑形式,土樓被稱為“民居中的活化石”“中國最特別的民居”[26].據(jù)歷史考證,漢唐以來,大量北方的人口遷入福建,使福建形成了移民社會的特征.在遷移過程中,北方移民經(jīng)常遭到閩越土著的頑強反抗,北方移民之間也經(jīng)常為爭奪生存空間發(fā)生沖突[27].
想要在競爭殘酷的環(huán)境中獲得優(yōu)勢,以宗族勢力作為后盾是必要的.為了團結(jié)族人、防御外敵,土樓逐漸形成了“對外封閉,向內(nèi)聚合”的空間特征.“對外封閉”是指土樓一般為封閉的環(huán)形結(jié)構(gòu)(或方形結(jié)構(gòu)),外部用生土夯筑厚且高的外墻,具有防御功能,外敵很難攻入.“向內(nèi)聚合”是指環(huán)內(nèi)住房都朝向圓心的祖廟和水井,具有明顯的向心性.物理空間對社會文化具有形塑作用,誠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空間將人們限定在不同的地方,從而有助于建構(gòu)社會秩序,型構(gòu)階層、性別和分工[28].
福建土樓的空間結(jié)構(gòu)歷經(jīng)千百年,改變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構(gòu)建了一種獨特的土樓文化.可以說,土樓既是客家文化的一種外在景觀,又是其文化內(nèi)涵的外在條件[29].土樓文化豐富多彩,其精髓是以耕讀傳家為核心的家族宗法秩序和理念[30],是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
然而,隨著時代發(fā)展,土樓的防御功能早已消失,其居住功能也逐漸弱化.部分土樓成為旅游景區(qū),獲得了更好的保護.沒有成為旅游景點的土樓則由于風雨侵蝕,年久失修,開始逐漸走向破敗.本文所關(guān)注的陶淑樓是一座有百年歷史的土樓,位于福建省云霄縣下河鄉(xiāng)內(nèi)龍村.陶淑樓位于村莊的中央,呈圓環(huán)形,高三層,錯落有致,總建筑面積約為9420平方米.陶淑樓極具古韻民風,據(jù)傳南宋末代皇帝宋昺帝趙昺曾客居于此并題名“陶淑樓”.在鼎盛時期,陶淑樓居住了三百余人,容納了村莊近半數(shù)的人口.土樓特有的環(huán)形結(jié)構(gòu),使得土樓環(huán)內(nèi)空間天然成為村民們的聚集地.
在茶余飯后,村民們聚集在土樓內(nèi)的空地上,小孩們游戲玩鬧,大人們洗衣服、喝茶、打牌、閑話家常.逢年過節(jié),土樓更是熱鬧.陶淑樓承載了村莊的集體記憶和鄉(xiāng)土文化,在村民心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陶淑樓逐漸走向破敗.據(jù)文獻記載,陶淑樓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僅有住戶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風吹雨淋使屋頂和墻體受損嚴重,木質(zhì)梁柱因蛀蟲而坍塌,土質(zhì)結(jié)構(gòu)也開始連片倒塌.雖然土樓已經(jīng)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但在福建地區(qū)土樓數(shù)量眾多,陶淑樓未被列入保護單位,未能得到有效保護.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條件的人家陸續(xù)搬離陶淑樓,住上了新蓋的樓房.此外,隨著城市化的發(fā)展,村民也不斷外流.2016年,內(nèi)龍村戶籍人口有2000人左右,但實際上常住在村子里的只有兩三百人.在土樓修繕前只剩三十余戶村民聚居于內(nèi),且以老年人為主.無人居住的土樓很快衰落,很多房間已經(jīng)破敗不堪,導(dǎo)致陶淑樓的狀況每況愈下,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危房.居住在土樓內(nèi)的老年村民常常擔心土樓倒塌,但苦于沒有其他住處,只能繼續(xù)住在里面.
二、土樓修繕與“好厝邊”項目
1.新鄉(xiāng)賢帶動下的“好厝邊”項目
2015年,從外地回鄉(xiāng)的林先生看到家鄉(xiāng)的現(xiàn)狀非常心痛,下決心要改變家鄉(xiāng)的面貌.林先生本是內(nèi)龍村人,北京大學(xué)光華管理學(xué)院社會公益管理碩士畢業(yè),先后創(chuàng)辦了三家公益機構(gòu),致力于社區(qū)營造與社會創(chuàng)新,曾入選南都公益基金會銀杏伙伴計劃,獲得共青團中央“全國向上向善好青年”、英國大使館社會企業(yè)獎等獎項.林先生有知識和資源,是新鄉(xiāng)賢的典型代表.面對家鄉(xiāng)的現(xiàn)狀,林先生結(jié)合自己的專業(yè)特長,開始籌措“好厝邊”計劃.“厝”在閩臺地區(qū)指的是屋子,“好厝邊”在當?shù)胤窖灾写笾孪喈斢诤绵従拥囊馑?體現(xiàn)了項目改造社區(qū)、造福鄰里的愿景.“好厝邊”計劃的首要切入點就是陶淑樓的修繕.林先生說:“我的童年是在陶淑樓度過的,對于我們這樣旅居外地多年的人來說,陶淑樓就是我們對故土的精神寄托.土樓名氣大,有吸引力,適合作為一個起點.”
三、一個動態(tài)框架:通過空間改造重構(gòu)鄉(xiāng)村的路徑模式
鄉(xiāng)村振興必然需要改造鄉(xiāng)村空間,政府和市場都在其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政府通過行政管理和政策引導(dǎo)對鄉(xiāng)村的物理空間進行規(guī)范,但相關(guān)研究指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由于缺乏村民的參與,最終導(dǎo)致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懸浮”于鄉(xiāng)土社會[35].市場力量對鄉(xiāng)村空間的形塑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典型的做法是將鄉(xiāng)村打造成為旅游景區(qū),但可能導(dǎo)致鄉(xiāng)村的商業(yè)功能擠壓其生活功能,鄉(xiāng)村性剝離,鄉(xiāng)村空間異化[36].
概而言之,政府和市場更強調(diào)鄉(xiāng)村的物理空間,對空間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雖然也有所關(guān)注,卻容易由于缺乏村民參與而導(dǎo)致懸浮和異化.可見,物理空間的改造并不必然能實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土樓修繕案例提醒我們,在物理空間之外還需要實現(xiàn)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改變,而后兩者對于鄉(xiāng)村發(fā)展也許更為重要.
關(guān)于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的劃分,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土樓修繕案例,嘗試做出如下界定:首先,物理空間即傳統(tǒng)觀點對空間的理解,是一切人類活動得以展開的介質(zhì)和場所,如地理環(huán)境和建筑物.物理空間是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基礎(chǔ)和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物理空間如果損毀,附著于其上的社會記憶和社會秩序也將岌岌可危.物理空間在本研究中具體表現(xiàn)為土樓等物質(zhì)的空間.
其次,社會空間是人們?nèi)粘I钣谄渲械目臻g,是行動者基于其所處的物理空間進行的集體建構(gòu)[28].社會空間強調(diào)了空間的社會屬性,即空間由社會所生產(chǎn)[37],同時空間也在生產(chǎn)著社會關(guān)系[38].社會空間也是一個實踐空間,實踐主體一方面具有被動性,受到物理空間和社會文化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具有主動性,行動者通過實踐參與空間建構(gòu),實現(xiàn)空間生產(chǎn).空間中的被支配方、被主宰方,惟有通過社會運動和自主改革的實踐,才能參與親歷(lived)空間的型構(gòu)[17].
在本研究中,社會空間既表現(xiàn)為圍繞土樓形成的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秩序的空間,也蘊含著空間建構(gòu)的實踐力量.再次,文化空間建立在人類話語體系、表象活動、秩序觀念之上,是符號化和概念化的空間,凝聚著人類的記憶與文化,表征了歷史層積的人與地的關(guān)系、人與人的關(guān)系[39].
空間形塑、主體實踐與文化勢能三者相互作用,重構(gòu)了鄉(xiāng)村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由于多重空間存在相互建構(gòu)關(guān)系,某一維度空間的改變能夠觸發(fā)動態(tài)的連鎖反應(yīng),實現(xiàn)多重空間的連續(xù)互動.不過,多重空間的互動引發(fā)的后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鄉(xiāng)村傳統(tǒng)空間的破敗伴隨著鄉(xiāng)村社會的凋敝和鄉(xiāng)村文化的衰落,體現(xiàn)的就是負向的互動關(guān)系.
鄉(xiāng)村振興論文范例: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下的文化治理進路理論向度與實踐路徑
土樓修繕的案例關(guān)注地方性,重視村民參與,強調(diào)文化活化,通過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的正向互動實現(xiàn)鄉(xiāng)村面貌的改變、鄉(xiāng)村社會的再組織化和鄉(xiāng)村文化的傳承創(chuàng)新,為我們從空間入手助力鄉(xiāng)村振興提供了路徑參考.在鄉(xiāng)村振興中,以蘊含地方特色的物理空間為抓手,能夠快速調(diào)動多方資源,改變鄉(xiāng)村面貌,凝聚居民關(guān)切.在物理空間之外,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重要性應(yīng)得到更充分的重視.村民參與是社會空間活力的來源,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更新是文化空間活化的必然路徑.參考文獻
[1]朱霞,周陽月,單卓然.中國鄉(xiāng)村轉(zhuǎn)型與復(fù)興的策略及路徑———基于鄉(xiāng)村主體性視角[J].城市發(fā)展研究,2015(8):38G45.
[2]蒙慧玲.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農(nóng)村社會空間變遷研究[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0(4):63G70.
[3]田毅鵬,韓丹.城市化與“村落終結(jié)”[J].吉林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1(2):11G17.
[4]MARSDENT.Questionsofrurality[M]//MARSDENT,LOWEP,WHATMORES.Ruralrestructuring:globalprocessesandtheirresponses.London:Fulton,1990.
[5]王佳星,龍文軍.文化治理視角下的鄉(xiāng)風文明建設(shè)[J].江南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9,18(6):73G80.
[6]申明銳,沈建法,張京祥,趙晨.比較視野下中國鄉(xiāng)村認知的再辨析:當代價值與鄉(xiāng)村復(fù)興[J].人文地理,2015(6):53G59.
[7]王曉毅.鄉(xiāng)村振興與鄉(xiāng)村生活重建[J].學(xué)海,2019(1):51G56.
作者:王杰1,洪佩2*,朱志偉3
- 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河源市電商助推經(jīng)濟發(fā)展的策略研究
- 空間生產(chǎn)理論視域下的鄉(xiāng)村聚落景觀優(yōu)化研究以開平市東和村為例
- 以農(nóng)文旅康深度融合推動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振興作用機理與推進策略羅先菊內(nèi)容
- 鄉(xiāng)村振興視閾下民族地區(qū)構(gòu)建現(xiàn)代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體系的機制與路徑探析
- 中國城市生態(tài)空間的范圍、規(guī)模、成分與布局
- 鄉(xiāng)村振興人才培養(yǎng)的留農(nóng)效果研究以“一村一名大學(xué)生”人才培養(yǎng)工程為例
-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下農(nóng)村職業(yè)教育鄉(xiāng)土課程開發(fā)現(xiàn)狀研究
- 虛擬公共空間與基層鄉(xiāng)村治理變革基于一個中部地區(qū)村落的考察
- 鄉(xiāng)村文化與旅游產(chǎn)業(yè)融合研究回顧與展望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hù)SS
- 2025-01-22語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xué)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guān)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xué)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nèi)容?
- 2025-01-24醫(yī)學(xué)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