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麥隆英語區社會危機成因探析
時間:2021年01月04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
【摘要】位于非洲中西部、緊鄰大西洋的喀麥隆共和國,因其豐富多彩的地質、多元獨特的文化、總體穩定的政局和蓬勃發展的經濟,被視為中部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強國。 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獨立后喀麥隆英語區與法語區之間矛盾頻發,從最初的英法語言沖突逐步上升為日益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已然成為制約喀國社會發展的重大隱患。 本文在厘清喀麥隆英語區危機歷史沿革的基礎上,揭開英法語言之爭的表象,從歷史、政治、經濟、語言、外交等方面剖析沖突產生的原因,展望危機演進的趨勢,并對喀國政府重新建立全國對話賦予英語區特殊地位等舉措抱有期待。
【關鍵詞】喀麥隆 英語區危機 政治沖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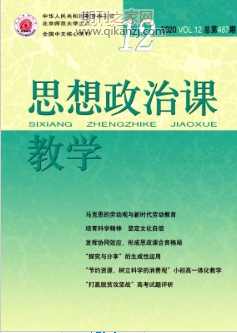
喀麥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西臨尼日利亞,東靠乍得、中非,南與剛果(布)、加蓬、赤道幾內亞毗鄰,是中非地區的政治經濟強國。 1472年葡萄牙海員在喀麥隆海岸登陸,揭開了喀麥隆與歐洲乃至世界聯系的帷幕。 1911年德國殖民者占領喀麥隆全境。 一戰后,英法兩國以國聯委的名義將喀領土瓜分殆盡。 二戰后,隨著民族獨立斗爭的蓬勃發展,法屬托管區(即如今的法語區)于1960年1月獲得獨立,建立喀麥隆共和國; 1961年10月,英國托管區南部(即如今的英語區)并入喀麥隆共和國,組成喀麥隆聯邦共和國。
獨立后的喀麥隆一直面臨著分裂和政治統一的脆弱性問題。 這一致命短板并不主要歸因于部族眾多和文化的多樣性,而是來自英語區與法語區的分裂傾向。 頻繁發生的武裝叛亂給喀麥隆的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已然成為制約喀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國內學界對喀麥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教育、文學及衛生領域,關于英語區社會危機話題的討論僅見于新聞報道,亦或散見于少量研究喀麥隆官方雙語政策實施困境的文獻中,鮮有針對英語區社會危機誘因的具體論述。 筆者認為,喀麥隆英語區危機雖表象于“英法語言之爭”,實則是由語言沖突引發的社會政治危機。 鑒于此,本文擬從歷時角度分析考察喀麥隆英語區危機演變的歷程,從殖民歷史、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語言規劃和外交關系五個方面探究危機產生的內外因,以期對喀麥隆社會問題研究有所裨益。
一、喀麥隆英語區概況
喀麥隆英語區,又稱西喀麥隆,即喀麥隆的西北省和西南省(圖1淺紅色部分為英語區),是1961年喀麥隆統一時并入到喀麥隆共和國的原英屬托管區的南部地區。 喀麥隆英語區與尼日利亞接壤,擁有16490平方英里的領土,人口約554萬,占全國總人口的22%。 該地區的種植園、漁業、木材業、石油開采和商貿經濟活躍,在喀麥隆的國民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危機的沿革
1961年10月原英屬托管區南部地區并入喀麥隆組成喀麥隆聯邦共和國,英語區與法語區度過了短暫的“蜜月期”。 70年代,阿喬希(Ahdjo)政府取消聯邦制,將國名改為喀麥隆聯合共和國,這一舉措開始讓講英語為主的西北區和西南區民眾產生被拋棄感。英語區人民尋求改革和擴大自治的訴求從未停歇,雖抗議活動不斷但多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分離分子在這其中遠不是主流。
2016年成為英語區危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從2016年10月開始,西北區和西南區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地區危機。 表2羅列的主要沖突事件發展至今讓英語區的大多數學校商店停課歇業,導致超過60萬學生輟學,造成至少3000人喪生、53萬人流離失所、4萬人逃往鄰國尼日利亞,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法郎。 隨著暴力事件的持續發展,數據仍在不斷更新。
通過上述事件,我們可以窺探出英語區社會危機演進的特點:第一,沖突焦點從語言地位的失衡逐步轉變為政治經濟等利益的不對等。 第二,從停課罷工、和平訴訟再到武裝叛亂、流血沖突,斗爭手段趨于暴力,程度也更加劇烈。 第三,惡性影響愈發嚴重,從簡單的尋求政治民主權利上升為國家安全事件,甚至面臨領土分裂的危機,嚴重危害了喀國的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
三、危機的根源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 Simmel)根據沖突的現實性將社會沖突分為現實的沖突和非現實的沖突,根據沖突發生的領域又分為經濟沖突、政治沖突和語言文化沖突。 筆者認為,喀麥隆英語區危機最初是一種追求語言利益的現實沖突,發展至今早已政治化,已然成為殖民遺留、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語言規劃和外交行為等各種矛盾交織而成的社會沖突。
1. 殖民主義歷史遺留
一戰后,喀麥隆被英法兩國瓜分殆盡,其中20%的國土由英國占領,80%的面積由法國統治。 英屬南喀麥隆以及法屬喀麥隆在英法兩國分治下發展為相對單一的政治單元,兩個地區之間的異質性不斷增強。 如下文表3所示,在近代歐洲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政治哲學思想的影響下,英國和法國建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殖民體制,形成了兩套政治語言文化體系,在行政管理、文化推廣和經濟開發等方面各有特點。
1.1行政管理體制
在行政管理上,為了確保委任區統治的穩定,同時考慮殖民區內部民族的復雜性,英國政府對喀實行“以夷制夷”的間接統治策略:一方面,要求委任區的土著官員承認英國對其宗主權; 另一方面,英國殖民當局確認當地土著政權的合法性,要求土著政權對當地人民實行治理,包括對稅收和按照本地法對土著居民進行司法管理。
同時,英國殖民當局還建立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管理體制,建立了由總督、行政委員會、立法委員會組成的中央政府。 在“間接統治”的政策之下,英屬委任區具有高度的自治權利,其教育體系、司法制度、貨幣、經濟體系以及社會規范同時也受到英國模式的深刻影響,故而在獨立之前英語區就已實現了新聞自由、政治多元和民主自治。
相反,法國實行“直接統治”方式,實施對喀委任統治區的同化政策,將法國本土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移植到了委任區,力圖使委任區的社會按照法國的模式發展,最終和法國融為一體。 法國殖民當局的政治高壓之下,委任區的自由民主程度不高。
1.2 語言文化政策
(1)語言生態環境
受“去殖民化”主張和漢普頓-塔斯克基教育模式的影響,英國在其委任區早期采取以“適應性”理念為核心的規避英語教育政策,注重發展本土教育,確立土著語為基礎教育的教學語言,遏制英語在社會中廣泛傳播。 二戰后當局政策發生轉向:打壓土著語言、大力擴張英語、推廣英國文化。 英屬委任區的殖民語言由此完成了從“先生”的語言到“平民”的語言之完美蛻變。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間接統治”政策在文化領域中的實踐為當地土著語創造了良好的生態環境。 當地民族語與英語相混合形成了一種在英屬喀麥隆地區廣泛流行的新語言——喀麥隆洋涇浜英語(Cameroonian Pidgin English)。 洋涇浜英語的使用程度遠超標準英語,較大程度擠壓了標準英語在喀國的生存空間。
反觀法國,在“直接統治”政策的影響下,法國采取語言同化政策。 秉承“法國必須向全世界擴張自己的影響,將她的語言、習俗、旗幟、武裝力量、工程學帶到各地”的理念,歷任殖民總督將消滅本土語言、推廣法語和法蘭西文化視為首要任務之一。 系列方針政策的頒布實施促使法屬委任區的土著語和法語的語言生態發生了巨大改變:諸如富拉語(Fulfulde)、豪薩語(Hausa)、卡努里語(Kanuri)等民族語言的生存受到極大威脅; 法語則在行政、媒體、教育等領域最終占據了主流語言地位。
由此可見,因語言政策推行的差異性,同為殖民語的英語和法語在喀麥隆的發展路徑截然不同。 無論語言自身的純潔性還是語言使用的群體基礎,法語都遠超英語。 英法兩種語言地位的懸殊為喀麥隆英語區社會危機埋下隱患。
(2)文化價值理念
英國和法國不同的殖民政策同樣造成了殖民文化輸出的不同后果。 從殖民擴張的動機來看,英國的殖民活動以服務海外貿易活動為主要目的,英國與殖民地的聯系相對松散。 隨著英語的有效傳播,英屬喀麥隆民眾逐漸形成以“英語語言文化”為符號的共同身份認同,但英國殖民者采取的“間接統治”更多地折射出了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利用”與“被利用”的經濟利益關系。
與英國不同,法國的殖民活動更多出于政治考量。 法國寄希望于通過語言和文化的輸入獲取殖民地人民對法國公民身份的認同和對法國的歸屬感。 這些攀升的過程便包括接受學校教育、移接法國風尚、為殖民利益服務等途徑。 法國的“同化政策”是一種自然漸進的過程。
1.3 經濟開發政策
英屬喀麥隆位于喀麥隆西部地區,是西方殖民者在喀麥隆最先到達和開發的地方。 在德國殖民者統治期間,該地區作為重要的種植園區得到了德國人的開發,有著較好的經濟基礎。 如前文表3所示,英國殖民政府接替管理后,繼續采取“間接統治”方式重點發展種植園經濟,對種植園生產的橡膠和棕櫚等產品進行簡單加工。 二戰后,當局雖逐漸控制了林業、農產品加工業、交通運輸業、銀行業以及進出口貿易等經濟部門,但對其依附性具有局限性。
相對于英國的“放手不管”,法國殖民當局對其統治區的“經濟改造”更為積極徹底。 在統治初期,法國殖民者提出了“殖民地開發政策”,堅持功利原則,片面要求發展出口經濟作物的生產; 壟斷林業、石油、天然氣開采和金融等重要命脈行業; 建立了包括法屬喀麥隆在內的法朗區,實行貨幣匯兌; 加強對法屬統治區的經濟援助。 種種舉措促使法屬喀麥隆在殖民時期形成了一種過渡依賴宗主國的依附性經濟結構。
通過上述研究,筆者認為,英、法對喀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造成東西兩邦在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語言文化上的巨大差異,成為英語區社會危機產生的歷史因素。
2.中央集權政治困境
2.1獨立與統一:分歧的開始
1960年1月1日法國托管區宣告獨立,建立了喀麥隆共和國。 英國托管區人民要求脫離英國托管,建立統一的喀麥隆的歷史任務提上了日程。 在英國托管區的南喀麥隆,約翰·恩古·豐沙(John Ngu Foncha)領導的南喀麥隆民族民主黨(Kameru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KNDP)上臺后積極推動英、法托管區的統一。 1960年7月17日至21日,豐沙政府和獨立的喀麥隆共和國總統阿馬杜·阿希喬(Amadou Ahidjo)在西部城市豐班(Foumban)舉行了多次立憲會議,商討統一方案。 然而,在爭論中產生的臨時憲法賦予了聯邦政府許多重要的權力,如國防、外交、教育、科研等方面; 英語區地方邦政府僅擁有少數涉及公眾健康、初等教育、技術教育、監獄管理等問題的臨時管理權并且須在統一后的兩年之內將權力交還給聯邦政府。 為了促進統一,處于弱勢地位的英屬喀麥隆政治家們最終做出了讓步。
1961年2月11日,英國托管區的南北喀麥隆在聯合國主持下同時進行全民公決,南喀麥隆通過公投決定并入喀麥隆共和國。 1961年8月,喀麥隆共和國國民議會通過了聯邦憲法,同年9月1日阿希喬頒布臨時憲法。 1961年10月1日,南喀麥隆脫離英國托管與喀麥隆共和國統一,成立喀麥隆聯邦共和國。 根據憲法規定,原英屬喀麥隆改名為西喀麥隆,原喀麥隆共和國改名為東喀麥隆。 合并之后東西兩邦權力的分配不均讓英語區民眾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2.2 中央集權化加強
喀麥隆聯邦共和國成立后,以聯邦總統阿希喬為首的政治家一方面利用臨時憲法規定的權力加緊東西兩邦的聯合,另一方面不斷擴大和加強政黨對聯邦的領導作用,旨在創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
統一后不久,阿希喬頒布第61/DF/15號法令,宣布將聯邦劃分為六個區,其中東喀麥隆被分為五個區,而西喀麥隆作為單一的行政區。 同時規定,每一個區將由總統任命的聯邦政府監察員來管理。 此舉進一步削弱了西喀麥隆的地方權力,加強了總統對英語區的直接控制。
此外,阿希喬還通過政黨改革進一步加強聯邦中央權力。 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阿希喬所在的喀麥隆聯盟執政黨地位的確立,該黨在法語區的地位達到空前高度。 聯邦共和國成立后,一方面喀麥隆聯盟不斷壯大在東喀麥隆的實力,另一方面阿希喬積極實施政黨合并事宜并對反對其建立統一政黨的政敵進行清洗。
同一時期,西喀麥隆的政黨聯合傾向也在加強,然而西喀麥隆政黨內部矛盾不斷,在組建聯合政黨的問題上分歧嚴重。 以阿希喬為首的東喀麥隆政黨領導人積極利用西喀麥隆政黨的分化組合,削弱西喀麥隆有獨立意識的黨派。 1966年,全國性政黨--喀麥隆民族聯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du Peuple Camerounais, RDPC)成立,西喀麥隆的民族民主黨等黨派分別解散。 喀麥隆中央權力的加強使英語區在政壇中的力量日益式微。
2.3 政治民主化削弱
1982年11月,保羅·比亞(Paul Biya)接任總統。 他一方面繼承了阿希喬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國家的民主改革。
在推進中央集權的進程中,比亞政府繼續漠視西喀麥隆的政治地位,無視民眾爭取民主權利的訴求。 早在1972年阿希喬政府就將聯邦共和國體制變更為總統制的單一共和體制,1984年1月,比亞步其后塵修改憲法,再次變更國名。 國體變更是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的體現。 聯邦地位的喪失使得英語區失去了獨特性和自治權的憲法支撐,東西兩邦的平等地位名存實亡,此次修憲舉動直接導致英語區分離主義抬頭。
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下,比亞政府著手政治民主化改革。 盡管此時的英語區成立了諸如社會民主陣線(Social Demoractic Frot)等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反對黨派,但對比亞政府及其所在的人民民主聯盟(Union Nationale)的執政地位未有絲毫撼動。 在中央政府層面,重要部門的關鍵崗位依然保留給法語區的政治精英; 地方層面,英語區幾乎完全喪失自治權,民眾無權擔任政府部門里的相關要職。
通過上文對喀麥隆政治建設的論述,筆者認為,政府中央集權化和同化政策的不當推行導致東、西邦矛盾激化,成為英語區社會危機爆發的關鍵因素。
3. 經濟政策公平缺失
經濟“邊緣化”同樣是引發英語區民眾對中央政府不滿的另一誘因。 正如前文所述,殖民時期英國“放任不管”和法國“積極改造”的經濟政策使得東、西喀麥隆的社會發展極不平衡。 盡管獨立后的歷屆政府采取諸多舉措以協調兩邦發展,但英語區仍然面臨著資源分配不均、改革邊緣化和經濟活力下行等質疑。
3.1 貨幣改革引發矛盾
聯邦政府剛成立時,中央政府面臨著統一度量衡的重要任務。 為了充分掌握西喀麥隆的社會經濟發展指標,聯邦政府在西喀麥隆設立統計機構,于1964年開始統一采用公制度量衡。 在貨幣政策方面,政府決定停止英鎊在西喀麥隆地區的流通,采用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即非洲法郎)作為全國共同貨幣。 西喀麥隆繼東喀麥隆之后加入法朗區。
貨幣政策的變革直接導致英語區民眾所持英鎊貶值,購買力至少下降10%。 購買力下降的真正秘密在于“匯率偏差”。 在阿希喬政府的操縱下,英語區民眾以1英鎊兌692非洲法郎的價格進行貨幣交易,匯率遠遠低于“1英鎊兌800非洲法郎”的市值。 英語區民眾的財富因此出現縮水,他們不但不能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反而成為犧牲者。
3.2資源分配備受質疑
喀麥隆國家統計局普查數據,我們發現,2014年喀麥隆全國貧困發生率37.5%。 其中西南省18%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西北省則高達55.3%,貧困人口數全國排名第三,僅次于極北省(74.3%)和北部省(67.9%)。 盡管英語區兩省的貧困人口平均數并不比北部省和東部省的數量多,但與其并列齊名的雅溫得(5.4%)和杜阿拉(4.2%)相比則高出許多。 在此背景下,英語區人民將責任歸咎于中央政府,指責政府部門掠奪英語區資源。
英語區西北、西南兩省的地方經濟主要涉及種植業(可可、橡膠、棕櫚油等)、木材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4.5%)、石油業(占國內生產總值9%)。 兩省各自擁有地區產業優勢。 西北地區資源相對匱乏,主要依靠農業、畜牧業和進出口貿易。 在國家公共企業上農流域開發機構(La société de développement de la Haute Vallée du Noun, UNVDA)的經營管理下,西北省的水稻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一。
與西北省鮮明對比的是西南省擁有木材、漁業和石油等豐富的經濟資源,西南省是英語區的主要財富支柱。 一方面,西南省在喀麥隆發展公司(Cameroo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DC)的管理下,擁有3.5萬多公頃的種植園,主要種植和經營棕櫚油、橡膠、茶葉等重要的出口經濟作物。 另一方面,自從位于西南省的里奧-德爾雷伊盆地被勘探出儲藏有相當數量的石油后,該地區匯集了喀麥隆國家石油公司(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hydrocarbures, SNH)、喀麥隆國家煉油公司(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raffinage, SONARA)等多家石油開采和生產產業。 全國唯一的煉油廠也建于西南省港口城市林貝(Limbé),由喀麥隆國家燃料公司經營管理,日產石油4.5萬桶。
英語區坐擁豐富的礦藏自然資源,是否就可享有與其相匹配的財富? 顯然,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的英語區民眾,在經濟上也倍感委屈。 究其原因,一方面,1963年加入聯邦初期,西喀麥隆斬斷了與英聯邦的關系,故而失去與英聯邦國家相關的海關出口特惠待遇。
另一方面,隨著中央政府政治集權化的加強,經濟集權也在英語區推進,原本屬于地方政府的公司企業收歸國有,諸如林貝港、巴門達機場和提科機場等在建工程的所有權全部上交,地方政府同時也喪失了征收進出口貨物稅等財政自主權。 盡管英語區經濟發展充滿活力,但民眾的貧困局面并沒有得到改觀。 英語區的活動家因此向政府提出抗議:“如果喀麥隆英語區是獨立自主的,那么西南區的石油就屬于他們; 即便在聯邦制下,英語區民也可通過租金分配享受到更多紅利”。
3.3 “英法”高管占比失衡
“青年非洲”周刊雜志(Jeune Afrique l’Intelligent)評選的2014年非洲企業500強中,喀麥隆共9家企業上榜。 其中喀麥隆國家煉油公司(SONARA)排名第82位,喀麥隆國家石油公司(SNH)排名第88位,其他如喀麥隆石油儲備公司(SCDP)等能源行業企業都有較好排名。 通過查閱上述企業的組織架構圖,我們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高層社會階級被說法語的喀麥隆人統治,說英語的喀麥隆人鮮有機會得到優秀的工作崗位。
如表4喀麥隆國家石油公司(SNH)董事會成員名單所示,9名董事會成員中最核心的2名領導人——董事會主席和執行總經理均來自法語區。 排除已故的巴卡西地區總負責人Chief Daniel Anki Ambo,法語區成員占據5席,英語區僅3人。 大型企業高層職位的占比失衡體現了法語區與英語區就業機會的不公平性,是英語區和法語區矛盾的又一集合點。
綜上,筆者認為,東、西兩邦經濟集權進程中推行的貨幣政策、資源分配和就業問題的不完善導致英語區民眾的被拋棄感增強,從而挑戰政治認同,成為英語區社會危機產生的重要因素。
4.語言功能行使失衡
喀麥隆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奉行官方雙語制的國家。 英法官方雙語政策是國家一體化進程的助推器,亦或是引發英語區矛盾沖突的導火索? 我們將借助博納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教授的語言政策傳統研究模型(圖3)探究雙語政策在英語區社會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4.1 語言信仰的確定
如前文所述,英國和法國對喀麥隆40多年的殖民統治,使得英語文化和法語文化在喀麥隆深深地扎下了根,為喀麥隆留下了兩種語言、法律、政治和教育體系。 獨立后的喀麥隆與其它非洲國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一樣,面臨著兩個由歷史與現實、理念與實踐交織而成的語言困境:一是后殖民時代由殖民統治遺產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沖突帶來的語言困境。 二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整合機制與重新肯定族群認同之間的沖突帶來的語言困境。
面臨著族群林立、宗教沖突和殖民裂痕等問題的嚴峻挑戰,喀麥隆在建立聯邦共和國時很自然地選擇“中立的”前殖民語言同為官方語言,以避免因為選擇某種本土語言或是選擇某一種殖民語言而可能產生的語言沖突。 “一個統一國家、兩門官方用語、多種土著語言”的語言信仰終被確定。 喀麥隆的英法官方雙語政策承載著文化共享、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神圣使命。 在過去近60年的發展變革中,歷屆政府一貫保持高度統一的擁護態度堅決捍衛雙語的平等官方地位,喀國的語言信仰頗為穩定。
4.2 語言規劃的缺失
1961年10月1日新生的聯邦共和國將官方雙語制視為促進國家統一的工具,因而在憲法中確定了這一制度。 之后的1971年憲法、1984年憲法和1996年憲法均重申了官方雙語制。 其中,1996年憲法第一部分第三條規定:“喀麥隆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法語,二者地位平等。 國家保證在全國范圍內促進雙語。 ”1998年4月14日頒布的喀麥隆第98-004號法令第一部分第三條款中規定:“國家將在所有層次的教育中設立雙語,以此促進民族的團結與融合。 ”
從理論和法律上來說,官方雙語法語和英語在喀麥隆社會之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兩者是互補而非競爭關系。 然而,筆者通過逐一查閱列舉的關于喀麥隆的語言立法條款,發現除憲法中簡要的原則陳述之外,尚未有相關的專門立法對官方雙語制進行界定和說明,沒有制定有關官方雙語政策或雙語教育的具體法規,沒有確定過官方雙語政策的短期和長期目標,沒有設立專門的執行亦或監督機構負責推動這一制度的落實等等。
由此可見,喀麥隆的語言規劃政策缺乏明確性、連貫性、權威性和執行度,導致原本相對比較平衡的雙語特征明顯地向不平衡方向加速變化。
4.3 語言實踐的困境
喀麥隆多部憲法雖反復重申打造官方雙語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迄今為止,這一核心語言政策的內容并未得以有效落實,在喀麥隆語境中,法語享有絕對主導地位,其影響力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一方面,從講法語的人數來看,法語較之英語更具優勢。 由于殖民時期的歷史遺留,喀麥隆全國劃分為十個大區,其中八個為法語區,兩個為英語區。 根據喀麥隆最新人口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總人口約為2520萬,講法語的群體總人數將近1965萬人占比78%,講英語的僅占總人口的22%。
另一方面,語言實踐與政府倡導的官方雙語政策背道而馳。 在教育領域,獨立后的東、西喀麥隆各自保留了殖民時期構建的教育和司法系統,然而國家入學考試由法語子教育系統指定,試卷僅提供法語版本。 在政府行政部門,政府文件幾乎全部使用法語; 雙語版的政府公告在排版上通常采用法語版本在左、英語版本在右的形式,法語版本常被特殊標記出來或使用大寫字母以示強調; 講法語的人一直占據著政府和公務員的高層職位。
例如,根據2017年統計數據,36位部長級官員之中僅有一位來自英語區。 在司法體系中,一些來自法語群體的法官對英式司法制度一無所知卻占據高位,他們對相關法律條文的解讀與闡釋嚴重影響著司法公正。 類似案例層出不窮,不斷積累的挫折感導致英語區和法語區的疏離以及英語區民族主義情緒的激化。
綜上,通過對官方雙語政策的探析,筆者認為,缺乏系統規劃和行動能力的官方語言政策是引發英語區社會危機的直接因素。
5. 外交政策利益導向
喀麥隆獨立初期,阿希喬總統倡導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在同前宗主國英國和法國的關系上秉持“中間態度”。 然而鑒于1960-1961年喀麥隆和法國簽署了涉及經濟、教育和軍事領域的全面合作條約,兩國已形成事實上的聯盟。 隨著各項合作協議的實施,法國在喀的商業、工業、貿易和其他經濟領域的利益占有壓倒性地位。 近年來,喀法兩國友好合作關系日益加強,喀麥隆在許多重要國際問題上都追隨法國步伐,保持與法國一致的立場。 反觀英國,隨著1961年英屬喀麥隆并入喀麥隆共和國,喀麥隆脫離英聯邦,同英國的政治經濟關系逐漸弱化。 經過6年努力,直至1995年喀麥隆才重回英聯邦,雙方關系最終趨于正常化。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 喀麥隆和英國、法國外交關系的差異化折射出了兩國在喀的影響力以及喀麥隆對兩國的依賴度。 對此,我們將借助喀麥隆與英、法兩國近十年的經貿數據一探究竟。
5.1 外貿規模
對外貿易在喀麥隆的國民經濟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如表5所示,近年來喀麥隆的貿易伙伴呈現多樣化的特點。 以2017年為例,喀麥隆主要進口來源國是中國(17%)、法國(9%)、泰國(5%)、多哥(5%)和尼日利亞(4%); 同年,主要出口對象國是意大利(13%)、中國(12%)、法國(10%)、荷蘭(9%)和西班牙(9%)。 其中,法國既是喀麥隆的第二進口國,又是其第三出口國。
2009-2019年期間,喀麥隆從英國進口的商品總值是970.089百萬美元,從法國進口貿易總額達到7459.211(百萬)美元。 相比之下,喀麥隆在國際貿易中對法國的依賴度更高。顯示的2009-2019年期間喀麥隆對英國的出口商品總值774.294百萬美元,對法國的出口貿易總額則是2787.152百萬美元,即對英出口貿易額的4倍。 無論從商品進口亦或是出口,法國始終是喀麥隆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在喀國的整體經濟發展戰略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5.2 雙邊援助
外援是影響喀麥隆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作為雙邊政治關系考量的關鍵指標。 20世紀初以來,英國和法國均是喀麥隆雙邊援助的提供國。2008至2018年期間,英國對喀援助凈值總額(126.71百萬美元)不及法國援助總額(1868.4百萬美元)的十分之一。
同時,通過世界銀行相關數據的整理,我們發現2008-2018年期間法國對喀的雙邊救助流量凈值占總額的23%至46.5%,平均占比32.7%,其中歷史最高值出現在2018年,達333.89百萬美元,占雙邊援助總額的46.5%。 法國對喀歷年來的經濟和財政援助使之成為喀麥隆最重要的援助國和投資國之一。
綜上,國內的政治變革和經濟發展影響著對外政策的制定、實施,影響著對外政策實施的優先方向以及效果。 反之,外交關系則反作用于一國國內的政治變革、經濟變革以及一國參與國際體系的方式與程度。 對喀麥隆而言,發展經濟一直是外交政策的出發點。 在現實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喀麥隆與前宗主國英國和法國之間外交關系的親疏有別必然影響國內各項政策的抉擇和施行,影響著英語區和法語區地位的平等。 可見,外交關系的利益導向成為英語區社會危機產生的外部誘因。
政治論文投稿刊物:思想政治課教學是思想政治工作資料性刊物。內容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內容、各條戰線與各階層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先進人物、集體及其事跡。
四、結論
本文從殖民歷史、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語言規劃和外交關系五個方面探究了喀麥隆英語區社會危機產生的內外誘因。 以“英法語言之爭”為表象的英語區危機實則是由語言沖突引發的政治社會沖突,是語言利益和多種其他非語言利益,諸如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外交的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目前,英語區危機仍呈現出擴散蔓延的態勢。 面對著分離主義活動頻繁、地區局勢動蕩不安、身份認同危機加劇等安全挑戰和內部沖突,喀麥隆政府亟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當前局面繼續惡化。 在對待英語區問題上,一方面,政府應摒棄暴力,采取和平對話的方式開展協商與談判,安撫民眾情緒。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切實有效的行動回應英語區人民的訴求,如在憲法框架下賦予西北省和西南省特別地位,加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權,改革國家教育、司法體系,繼續推廣雙語政策并監督貫徹執行,加強英語區災民救助和重建工作,給予英語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傾斜等等。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能否正確處理英語區社會危機問題將成為喀麥隆社會穩步發展的關鍵。
作者:白琰媛 張皓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