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教育人學內涵
時間:2020年06月28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
摘要: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教育人學內涵豐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教育與人性的生成為主題的核心內涵,一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為特征的精神內涵。前者包括自然教育的‚兒童天性發展‛指向和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的‚美好人性、智慧、道德和文化修養‛指向。后者指向肯定人的價值和地位,彰顯人的尊嚴和高貴;尊重人的理智和理性;讓學生在快樂和幸福中接受教育;讓學生擁有虔誠的宗教修養。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教育人學內涵指向呈現自然主義、古典主義、以人為本、宗教性等特色。
關鍵詞: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教育人學;內涵指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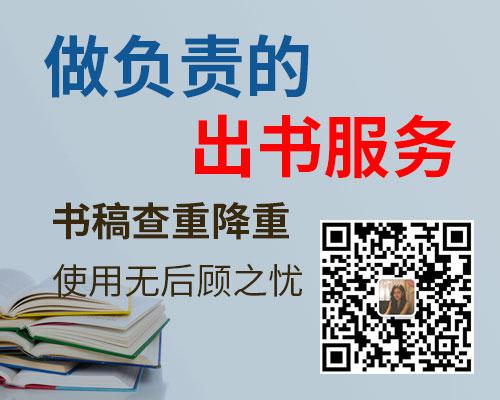
自然教育人學內涵的闡釋與人文主義人學思想息息相關。人文主義人學思想是自然教育人學建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而自然教育人學是使人文主義人學思想得到彰顯和落實的主要路徑。自然教育人學是對人文主義人學思想的反映,它聚焦于人,立足于人,力圖在教育活動中喚醒人的潛能和創造力,實現人的價值、尊嚴、高貴、理性、自由、快樂和幸福;力圖把學生當人看,并視其為教育活動中的主體,彰顯其主體性,使其擁有獨立的人格和自我意識;反對經院主義教育對人性的壓抑和束縛,倡導人的個性解放,力圖用人文主義教育的“以人為本”,取代中世紀經院教育的“以神為本”,使“人的發現”“人的覺醒”“個性解放”落到實處。
教育論文范例:素質教育在小學語文教育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自然教育人學認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人領悟到人的價值和使命,才能使人有建功立業的素養,才能使人更加完美,才能使人活得像人。教育提升了人生的品味,提升了人生的境界,教育使人走出野蠻和蒙昧,使人遠離低級的存在,使人君臨塵世,卓然而立,成為塵世的上帝。”[1]1顯然,揭示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教育人學的內涵及特色,對于我們準確把握這一時期自然教育人學的本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自然教育人學的核心內涵
教育與人性的生成構成了自然教育人學的核心內涵,其主要內容是,要立足于人,以人為本,力圖使教育人性化,使人的價值、尊嚴和創造力得到肯定和彰顯;解放被中世紀經院主義教育所禁錮和壓抑的人性,關注和促進人的身心自由和諧發展。無論是學生天性的發展,還是學生美好人性的彰顯,抑或是學生身心的和諧發展以及個性的解放和張揚,都是自然教育人學關注的重點。具體地說,自然教育人學要求,通過自然教育喚醒兒童的內在潛能和創造力,解放兒童天性的發展;通過古典人文學科的教育發現人,使人的精神得以覺醒、美好的人性得以彰顯;通過和諧教育、自由教育,促進人身心自由的和諧發展;通過個性化教育使人的個性得到解放,使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得到塑造。
(一)自然教育的“兒童天性發展”指向
人文主義教育家關注自然教育與兒童天性的發展問題。他們強調,兒童的天性是教育的基礎,也是教育活動取得實效的關鍵,教育者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兒童的天性、個性特征以及教育過程的內在規律,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教學效果。無論是意大利的人文主義教育家維多里諾、弗吉里奧、西爾維烏斯,還是北歐人文主義教育家拉伯雷、蒙田、伊拉斯謨、維夫斯等,都很重視這個問題,他們對此都有過重要的論述。維多里諾把兒童天性提高到重要位置,要求教師尊重兒童的天性,他說:“我們并不希望每個兒童都表現同樣的嗜好;無論怎樣,兒童總可以有他自己的所好;我們承認我們必須跟隨兒童的自然本性前進。”[2]
173弗吉里奧強調教師要認識和研究兒童的天性,并以此為根據安排科目,讓那些能力有限的兒童學習其力所能及的學科。伊拉斯謨反對在教育教學中虐待兒童,他主張廢除體罰,教師要懂得兒童的天性以及教育過程內在的規律。他認為天性訓練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進步。為此,“教育家必須研究兒童的身心發展,尊重兒童的個性特征,具備心理上的洞察力和行之有效的方法”[3]66。在他看來,“孩子都擅長真正屬于他本性的活動。
因此,要按大自然的規律辦學,在學校中消除過重的勞累現象,要盡量使學習能夠自由和愉快”[4]45。法國教育家蒙田的自然教育觀念是:依順自然,就是最高的訓練。他認為,自然是我們偉大的母親,她給我們畫好了美滿的道路。他要求人們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思考問題時,都要遵循自然的教導。維夫斯的最大成就,是把心理學的方法引入教育領域,用來理解和處理教育問題。他認為,“教學工作不應單純地依據學科本身和教學過程,更為主要的是研究學習者的本性,并且依據學習者的本性來安排教學過程”[2]191。
就是說,要根據學生的年齡來選擇和擴大其學習內容和范圍。如果僅僅強調學生的努力和勤奮,而忽略兒童的本性,不按自然的方法教育一個人,那么就會適得其反,難以取得好的效果。“在任何年齡階段都要糾正錯誤,我們不允許兒童被任何錯誤抓住,并且日益發展。因此,當一些事情學生還不能理解時,教師應把他們推遲到以后適合的年齡做或學。同時警告學生,他要做的事要經過批準,要按照他的發展進程去做。”[3]281維夫斯的這種尊重兒童天性,按照兒童天性安排教學的論述,充滿著心理學的意味,是對教育心理學發展的一大貢獻。總之,自然教育的“兒童天性發展”指向要求:教育要立足于兒童的天性,適應和促進它的發展,圍繞它來展開,始終把它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
(二)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的“美好人性、智慧、美德和文化教養”指向
古典人文學科教育也稱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從詞源的本義看,“人文主義”就是教育。意大利學者克里斯特勒認為,人文主義是由人文主義者和人文學科兩個詞構成的。前者是指講授人文學科的人;后者由語法學、修辭學、法學、歷史學和道德哲學等組成。“從這一定義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就是上述意義的人文學科的偉大興起與發展;人文主義對其他文化領域,諸如文學、藝術、科學、宗教可能產生的任何影響必定都是間接性的。”[5]人文主義者從古典人文主義學科的復興中發現人以及人的理想狀態。
“古典的人性不僅使生活充實與和諧,而且還通過思想和藝術作品,令人驚奇地反映出生活的充實與和諧。欣賞或閱讀這些文藝作品,就可以使我們接觸這些作品傳遞的思想,也就意味我們開始同完善的人進行對話,從他們那里學習所謂完美生活的含義。虛心地學習這些優秀作品,將其內容觸類旁通,也就是通過認識人類豐碩的精神財富,從中汲取精華來更新自己的思想。”[6]要把人文主義者發現的人性、完整人格、充實生活和和諧之美,內化到學生的知識結構和心靈教育中,離不開古典人文學科教育。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的旨趣是發現和解放人的本質,塑造人性和人格。所以說,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的內涵指向,包括美好人性的彰顯、美好智慧的獲得、美德的塑造等內容。
1.美好人性的彰顯
關注人,彰顯人性之美好,是古典人文學科的核心,它的使命就是通過古典人文學科的教育,使人性教育更加完美,精神變得更加崇高,使人能夠自由地主宰自己的人生,聆聽自己的聲音,成為完美的人。“人文主義者認為教育是把人從自然的狀態中脫離出來發現他自己的humanitas(人性)的過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studiohumanitatis(人文學)中,語法和修辭不僅引導學生熟悉古典研究并培養他們有效的說寫能力,而且也引導他們熟悉文學、歷史和道德哲學,不僅僅是熟悉他們所學經典作品的形式,也有這些作品的內容,他們從荷馬和修昔底德,從維吉爾和西塞羅那里學到humanitatis的含義。”[7]這就是說,古典人文學科教育是發現人性、充分了解人性的重要途徑。
對此,很多人文主義教育家做過重要論述。瓜里格認為:“學習古典人文學科的目的,不僅要從古典文化中汲取有益于個人發展的教育因素,使人性變得更加豐富,還要深刻地了解古典文化本身。因此,他把學習古典著作的語法、修辭學和文學置于重要地位。”[8]94伊拉斯謨把古典人文學科看成是人性變得完美的手段,他指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自然是寬厚仁慈的,如果閱讀經典著作的話,那人的本性就會變得更完美。”[9]
對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的人性作用論述得最精彩的是布魯尼,他指出,古典著作的學習和研究,不僅能使學生充分了解人性,而且能使學生的精神世界發生根本性變化,變得更加崇高。他著重論述了作為“人性之學”和自由學科的古典文學的功能和價值:它不僅能使學生獲得淵博的知識,而且還能使學生涵養人性,獲得精神的自由,成為具有完美人性的完整的人[1]61。這提示我們,古典人文學科教育不僅在培養人性、塑造人的自由精神方面有巨大作用,同樣對培養完整的人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2.美好智慧的獲得
人文主義者對古典人文學科的智慧價值做了深刻的闡釋。他們認為文學、歷史和哲學著作不僅能為人們提供歷史、道德、政治學方面的智慧,而且可以增強個人的判斷力。例如,帕爾梅利就認為,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不僅對國家事務有益,對個人事務同樣有用,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對事物進行判斷,使我們從歷史中去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人文主義者普遍認識到,學習和研究歷史可以彰顯多種功能。“首先,對于那些可能被要求去處理事務的人來說有很大的價值。因為通過這種學習,我們深入了解了其他國家的各種制度和習俗,我們也認識到我們自己發展的秘密。
其次,我們理解了過去已被證明是有益的各種美德,以及已被證明對國家來說是致命的各種罪惡,我們能夠追溯增強或削弱其權力的政策。從歷史中,我們了解了國王和自由民的不同命運,從而確定了今天我們自己管理國家的本領。因為任何人,無論是軍人,還是政治家,都可以從他自己的個人經驗中獲得用閱讀書籍提供的如此淵博的智慧。”[10]546在古典人文學科中,人文主義教育家最推崇的是文學和哲學,因為它們是引領人們進入智慧殿堂的階梯和工具,能給人以智慧的啟迪。薩多萊托直截了當地指出:“文學和哲學的學習充當精神登上最高智慧的階梯,這是自我和上帝的有意識的統一。
它們提供的重要幫助是使思想擺脫了感官中的事物,并使心靈思考超出合理現象的變化和缺陷的事情。它們是宗教和道德的正當補充,因為它們挖掘并反映更優秀的本能,抑制較低級的沖動和不適當的偏見。”[10]194西爾維烏斯認為:“沒有文學和哲學本身難道不是無法理解嗎?通過這種雙重智慧,王子得到的訓練以便了解上帝和人類的法則,我們每個人都通過它受到啟發從而理解我們周圍世界的現實情況。文學指引我們對過去有一個真正的了解,對現在有一個正確的估計,對未來有一個全面的預測。在沒有文學的地方,黑暗將籠罩大地;一個讀不懂歷史權利的君主是奉承和陰謀的犧牲品。”[10]481
可見,無論是歷史,還是文學、哲學,都能讓我們回溯過去汲取歷史教訓,也都能正確地估計現在,全面地預測未來,彌補道德和宗教的不足,增強我們的判斷力,提升我們的智慧。古典人文學科的學習和研究,不僅能給人們提供理論智慧,而且還可以提供實際智慧。人文主義教育家認為,古典人文學科中蘊含著豐富的實踐智慧,為人們的正確行為提供了指南。維夫斯說:“書是發現、判斷真誠的有力工具,它們能幫助我們走向實際智慧。”[3]248
人文主義者普遍意識到,“幾乎對于現實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從古典著作的學習中獲得最好的指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最明智的治國之學術手冊;維吉修斯和愷撒是戰爭技藝的最好的指導者;維吉爾是農業的最好指導者;在管理家庭方面,西塞羅、普魯塔克的《論教育》以及弗朗西斯科•巴巴羅的《論妻子》在貴族朋友中被視為很重要的和可靠的依賴。在各級政府部門中,在戰爭、司法、議會和國內政策上,文學是實踐智慧的一個可靠來源”[10]518。總之,無論是治國,還是戰爭指導、農業指導,抑或是國內政策改革,古典人文學科教育都能夠提供最好的指導。
3.培養良好的道德
古典人文學科的著作蘊含著極其豐富的道德教育因素,人們通過古典教育可以消除經院教育的愚昧、自負和粗俗,造就有淵博知識、精神充實、行為舉止優雅的有文化、有教養的人。最重要的是,人文主義教育家的共識和傳統就是:學生品德的形成,文明素養的形成,離不開古典人文學科,只有接受了古典人文學科教育,才算是受過教育。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人文主義者把受過古典人文學科教育視為學者和紳士的標志。古典人文教育的知識和訓練也成為真正受過教育的有文化人的共同背景。可見,古典人文學科教育是造就有道德、精神充實、有文化、有修養的全面發展的人的重要途徑。對于伊拉斯謨而言,道德的訓練和宗教信仰的養成被視為教育的最高目標和任務。
實現這一目標和任務,依賴于倫理學家、歷史學家和詩人的著作,因為它們構成了古典教育的主要內容,能承擔起系統的道德教育的責任。西塞羅、塞內卡、特倫斯和維吉爾等人的作品是值得信賴和學習的,它們有助于學生養成良好的品德。當然,伊拉斯謨并不是把道德建立在純粹古典書目的基礎之上,家庭生活的組織和榜樣仍然是道德教學的根基。對于意大利的西爾維烏斯而言,哲學就是對美德的探究,特別適合王子們的學習,它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一種責任,體現了法律的獨斷。“沒有人能比對成千上萬的人的幸福或痛苦有重要意義的人更需要儲存豐富的心靈。”[10]
480對于意大利的格里諾而言,選擇歷史作用的標準是道德,符合道德的目的和要求就保留,反之就拋棄。他反復強調,古典人文學科包含著道德的因素,只要善于處理,它就富有道德的意義。對于韋杰烏斯而言,古典人文學科是自由的學科,對自由人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通過這些古典人文學科,我們無疑會獲得智慧和美德。總之,無論是歷史學、詩歌、文學,還是哲學,都有助于完善人的品德,使人成為一個有文化、有道德、有教養的文化人。
二、自然教育人學的精神內涵
自然教育人學的精神內涵指向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在中世紀,經院主義教育存在很多弊端,這表現在它過于教條僵化,崇尚權威和壓抑人性,使學生的身體和心靈被嚴厲的制度和狹隘的紀律所束縛。教師“無休止地叫喊著往我們的耳朵里灌輸,猶如往漏斗里灌水一樣;我們的任務不過是重復曾告訴我們的東西”[4]52。
學生對知識的學習,只能死記硬背,生搬硬套,不能靈活地理解和消化知識。這種學究式的教育成為學生精神世界發展的障礙。人文主義教育家力圖改革舊的經院主義教育,把學生從各種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們新的教育理念,就是肯定人的價值,彰顯人的尊嚴和高貴,尊崇人的理性和理智,使人在教育中能體驗到快樂和幸福,確立虔誠的宗教修養,從而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解放和提升。
(一)肯定人的價值和地位,彰顯人的尊嚴和高貴
古典人文學科著作的學習和研究,不僅可以點燃學生心靈中的火焰,豐富學生的人性,而且還可以使學生認識到人的價值和地位,彰顯人的尊嚴和高貴。“虛心地學習這些優秀作品,將其內容融會貫通,也就是通過人認識人類豐碩的精神財富,從中汲取精華來更新自己的思想。而對人的教育境界就是使人們普遍認識人的價值,并通過自由文藝等人文主義學科去喚醒和增強這種價值。”[1]61–62對于人文主義者而言,“真正的教育者在乎對人的心智和身體兩個方面予以有效的訓練,進行心智訓練可使人能明智地控制自己的行為,進行身體訓練,可使人能更好地服從理性的命令,能保護我們的權利和捍衛我們的尊嚴”[1]63。
他們認為,古典文化的學習和研究,不僅能使學生的精神和個性得到自由和解放,而且能為學生精神世界的構建奠定理論基礎,帶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文學、詩歌也被認為是增強心靈力量,使人精神變得高貴的工具。對于人文主義者而言,學生的智力本能和感性詩性與詩意的和諧之間有直接的對應關系。因此,“詩被表明為更好的訓練心靈的適當工具。„„從我們最早的青少年時期起就有啟發心靈的力量,所有這一切使得我們給予崇高的詩歌在教育中很高的地位。總之,沒有有關詩人的良好知識,就沒有人能夠獲得文學卓越”[10]544。
(二)尊崇人的理性和理智
尊崇人的理性和理智是自然教育人學的重要內涵。它的旨趣在于通過古典人文教育引導學生的理性發展,培養學生的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伊拉斯莫認為,人性為人的成長和進步提供了可能,特別是人的理性的存在使人的發展和教育成為可能。人之為人的特性以及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分野,就是人有動物所沒有的理性,正是理性的存在使教育和訓練有了可靠的基礎,同時理性的發展也成了教育和訓練的重要任務。他希望優秀的王子從幼小時期開始,就要用理性滋養他的頭腦,“必須使他的心靈充滿有益的思想”[3]125,使其獲得理性發展。
法國人文主義者拉伯雷也論述過理性教育的優越性,在《巨人傳》中,他塑造了兩個不同的人物——卡岡都亞和尤德蒙。前者是按照經院主義教育培養出來的,盡管他能把讀了20年的書倒背如流,但他變成了思維呆板、沉迷空想的書呆子;后者是按照人文主義教育方法塑造的學生,他能獨立思考,說話得體,行為舉止優雅自信。“這兩個行為舉止完全不同的學生,是拉伯雷對兩種對立的教育方法擬人化的表現:機械式的記憶訓練會使智力變得衰弱遲鈍;只有自由的教育方式才能發展學生的智力,塑造學生坦誠開放的個性。”[11]德國人文主義教育家蒙田主要從理解能力和判斷力兩個維度闡釋自然教育人學的旨趣。蒙田反對死記硬背,倡導兒童自主思考和消化知識,學會自我判斷。因為“死記硬背,生搬硬套并不是知識,那不過是把一種東西存放在記憶中而已。
一旦一個人完全知道并理解了,能夠隨意自主地靈活運用,無須查書據典,那才算得上是知識。書呆子式的學識是一種可憐可鄙的學識,我們可以說:‘西塞羅是這樣講的’;‘這是柏拉圖的思想’;‘這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話。’一只鸚鵡也這樣學識,但是,我們自己能說些什么?我們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們怎樣去判斷”[4]50。這也就是說,學生對知識的學習,要先理解、消化、融會貫通,再轉化為自身的養料,成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否則,所學知識是沒有用處的。有了理解,才能看見與聽見;有了理解,才可以利用一切、支配一切,才可以行動、掌握與統帥。其余的東西都是瞎的、聾的、沒有靈魂的。
當然,不讓理解有自由發揮的余地,就會失去活力與豁達[12]7。教師要引導學生理解課本中所學詞的意義與要旨,舉一反三,能觸類旁通地掌握知識,而不是僅僅記住所學過的詞。因為后者只是“生吞活剝,消化不良”。在理解的基礎上,自我判斷是最為重要的,“教師要讓學生自己篩選一切,不要僅僅因是權威之言而讓他們記在頭腦里,亞里士多德的原則就不是原則,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的原則也不是。要把這些豐富多彩的學說向他提出,他選擇他能選擇的,否則就讓他存疑”[12]8。“存疑”就是要培養學生的自主選擇能力和判斷能力。
(三)讓學生在快樂和幸福中接受教育
實施快樂教育和幸福教育,讓學生擁有快樂和幸福,是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教育人學的重要使命和主要旨趣,無論是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還是其他國家的人文主義者都很強調這一點。率先提出快樂教育理念的是但丁和維多里諾。但丁把人生的目標確定為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和永恒生命中的幸福,認為兩種人生目標獲取的途徑是不同的,“前者是通過哲學的教育使人鍛煉和發展自己的理智與德行;后者是通過心靈的教育,依靠神的啟示和幫助,超越人的理性,形成神學上的信仰、信念和博愛等美德。他認為教育是引導人們追求知識和美德,將使人獲得現世的幸福,并將人帶入天堂”[8]85–86。
但丁把教育與人生目的實現聯系起來,意在強調通過哲學和心靈的教育,讓學生在知識、真理、德行、信仰的追求中獲得快樂與幸福。維多里諾倡導快樂教育理念與快樂教育的實踐相結合。在理念上,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強健的身體、淵博的知識、良好的德行、虔誠的宗教信仰、精神上快樂的人;所建學校必須環境清新優美,不但有益于學生身心健康,而且有利于學生從事各種活動,獲得身心的愉悅。他把自己創辦的孟都亞宮廷學校稱為“快樂之家”,其意蘊體現了這一點,也反映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理想。維多里諾熱愛和尊重學生,被稱為“仁愛之父”。
在教學實踐中,他力圖貫徹快樂教育原則,不斷變革教學方法,采用多種方法,使教學充滿樂趣。例如,教授讀寫時使用活動字母;教授算術初步知識是在游戲中進行;教授拉丁語是通過信札往來的游戲來進行。他還組織學生登山參觀城堡,游覽嘉特湖等戶外活動,使學生在欣賞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之美中,陶冶性情,獲得審美的快樂。英國的人文主義者莫爾把烏托邦人的快樂分為身體的快樂和精神的快樂,并特別強調后者的快樂,這種快樂就是“有理智以及默察真理所獲得的喜悅,還有對過去美滿生活的愜意回憶以及對未來幸福的期望”[3]219。
他認為,烏托邦人特別看重這種精神的快樂,把它放在所有快樂中最重要的“第一位”,“它來自德行的實踐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識”[3]220。人文主義者都強調通過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獲得快樂與幸福。弗吉里奧特別重視閱讀古典文學作品之樂之雅,認為通過閱讀文學作品,我們不僅可以把握過去、現在和未來,并使三者在我們的精神中融于一體從而呈現出無與倫比的文學魅力,而且所獲得的樂趣勝于人生的其他種種樂趣。
布魯尼認為,詩歌的優美和高雅折射出非凡的感受力,令我們尊崇,它的節奏、格律與人的情感世界具有特殊的關聯,能夠深深地打動學生,影響其情感。“詩歌在知識方面能給人提供有價值的幫助,在表現形式上較之其他形式的文學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在精神方面能給人帶來高貴的愉悅,若有人對其價值漠然置之或無動于衷,那他就不配稱之有教養的人。”[13]92西班牙的維夫斯則贊美歷史學給人類的生活和精神帶來的愉悅,認為歷史學可以使我們從過往年代的情況中獲得興趣,這種興趣是非常多的,它不亞于我們對時代的興趣。
學習歷史,“是愉快的事,因為它有益于清新人類的靈魂。我們以高度的愉悅和專心去聽的唯一理由是它與歷史有關,假如從豐富的歷史中聽到不尋常的、偉大的、壯麗的和杰出的事跡時,誰不豎起耳朵和喚起他的心智呢”[3]287–288。同樣,哲學也能讓學生獲得快樂,薩多萊托認為,哲學是本能地對人生目標的科學闡述,不僅能發展學生的智力,而且能塑造學生的心靈世界,指導學生的行為,引導學生從哲學的學習中獲得快樂,“通往最大的幸福”。因此,對于擔任重要職務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學習;而對于知識領域的探尋者來說,只有它能夠使他立足于牢固的基礎之上[10]194。總之,古典人文學科的教育是使學生通往快樂和幸福的重要之途,能給學生帶來精神的愉悅和幸福的體驗。
(四)讓學生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
人文主義者很重視宗教信仰的培養,維多里諾把培養宗教信仰視為教育目的的重要內容,并力圖將其貫徹到自己的教學活動之中,使學生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以此來提升學生的精神境界。西爾維烏斯把學生的宗教信仰當作精神領域最迫切的事情來對待,認為它是任何世俗利益無法比擬的。在他看來,人與生俱來的精神天賦是指向宗教信仰的,是“為我們進入天國做準備”。作為一個王侯,“你的整個生活和人格都應對上帝充滿感激之情,感謝他賜予你的并非由于你的優點而帶來的各種好處,應對上帝飽含敬畏之心,認真對待宗教儀式,虔誠信仰上帝并遵奉教會的權威”[13]132。
而學生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獲取知識和美德、提升精神境界的最佳途徑,是學習和研究文學、哲學、文藝。伊拉斯謨和維夫斯是最注重基督教與人文教育完美結合的教育家,他們的教育學說被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學,或者是人文主義基督教育學,其內在的含義是指把基督教與人文主義教育融通,使基督教教育滲透人文主義色彩,使人文主義教育充滿基督教精神。伊拉斯謨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向兒童的心靈播下虔誠的種子。
他理想中的君主教育,是基督教的君主教育,其旨趣是培養基督教精神,使君主虔誠地信仰上帝。因而他強調指出,必須牢記耶穌的故事,使之在王子的心靈里扎根,使他更加純粹,更加有效地暢飲耶穌的教旨,因為“耶穌的教旨最適用于王子”。伊拉斯謨還認為,應“仔細地避開一切粗俗的行為,這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責任;以純潔的性格和智慧超出一切人,這是一個王子的本分。你強迫你的臣民學習和服從你的法律,你應該以更大的努力強制你自己服從上帝耶穌的法律”[3]135。伊拉斯謨把古典人文教育看作培養基督教道德和精神的主要途徑。
在他看來,古典人文教育對宗教教育有強化作用,能滲透基督教的成分,無論對基督教道德和精神的培養,還是對改革教育,都有重要的價值,“其一,對古典語言的熟知和對人文主義方法的運用,有益于深化對圣經和早期基督教作家著作的研究,這樣可探知基督教的本質精神,把基督教從教會所造成的迷信和腐敗中拯救出來,而使之成為一種活生生的力量。其二,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中包含很多基督教有益的成分,這些東西有助于促進基督教信仰”[1]250。無獨有偶,維夫斯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他把學習所進行的心靈的陶冶和精神的教育,直接指向培養兒童的“永生的精神”。“他們必須牢記,這種培養是上帝交給人類作為慈恩的最大禮物,它不可能從任何其他來源得到;而且這肯定是一種追求,沿著這條路,他們能取悅上帝,到達上帝那里,這是他們最大的幸福。這樣,他們將喜愛這種心靈的陶冶,把它當作他們必需的事情,并且尊敬它,崇拜它,把它當作神圣的,天賜的東西。”[3]278
三、自然教育人學內涵的特色
綜上所述,文藝復興時代的自然教育人學內涵極其豐富,其指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教育與人性的生成為主題的核心內涵,一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為特征的精神內涵。前者包括自然教育的“兒童天性發展”指向和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的“美好人性、智慧、道德和文化修養”指向。這種核心內涵的揭示,反映了教育與人性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它們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內在機理,對于我們把握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教育文學的內在意義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
無論是自然教育的“兒童天性發展”指向,還是古典人文學科的“美好人性、智慧、道德和文學修養”指向,都是這個時代自然教育人學的核心構成,都反映了這個時代教育人學的本質。后者指向肯定人的價值和地位,彰顯人的尊嚴和高貴,尊重人的理智和理性,讓學生在快樂和幸福中接受教育,讓學生擁有虔誠的宗教修養。這種精神內涵凸顯了文藝復興時代自然教育人學的內在旨趣。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教育人學內涵指向蘊含著多種特色。
參考文獻:
[1]褚宏啟.走出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情懷[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2]滕大春.外國教育通史:第2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
[3]吳元訓.中世紀教育文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勞倫斯.現代教育的起源和發展[M].紀曉林,譯.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5]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八個哲學家[M].姚鵬,陶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4.
[6]加林.意大利人文主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74.
[7]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M].董樂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45–46.
作者:劉黎明,劉雅真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