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土地文化模式對隴南白馬藏區民族關系變遷的影響研究
時間:2021年08月12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內容摘要:甘肅省隴南的鐵樓藏族鄉是我國白馬藏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通過在該地某藏漢混居村落的田野調查發現,當地的白馬藏族和漢族分別屬于“共享型產權”和“私有型產權”兩種不同的土地文化模式;兩種土地文化模式在歷史上既有過相互包容,互補共存,也有過糾紛矛盾,互相排斥;兩種土地文化模式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能否包容共存的問題,事實上是當地民族關系變遷的決定因素,其本質是兩個族群在山地—溝谷型生態圈內對資源競爭與合作的博弈。
關鍵詞:白馬藏族;土地文化模式;資源競爭;民族關系;經濟互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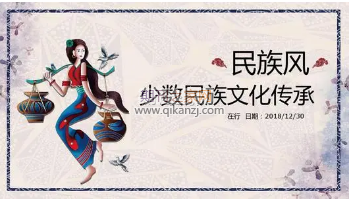
一、土地文化模式的研究視角
我們基于對甘肅隴南鐵樓藏族鄉某村(以下簡稱C村)的田野調查發現,作為一個白馬藏族與漢族混居型的村落,當地兩個族群的關系非常融洽,甚至在白馬藏人的節日儀式里漢族也會“扮演”成白馬藏族參與其中,以至于很難直觀確定一個人屬于漢族或是白馬藏族。但根據搜集到的資料和對村民的訪談來看,歷史上兩族的關系其實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從當地居民可追溯的記憶中發現,當地的漢族與白馬藏族的關系經歷了互補互需—矛盾糾紛—最終和解三個階段。而主導兩族關系變遷的決定因素,則是兩個族群間不同的土地文化模式。
“土地文化模式”是以土地的所有權、用益權等權屬為核心,在群體內部形成穩定的觀念、關系、制度以及人們所遵循的其他慣常。而不同的土地所有權與用益權歸屬又受到生產方式和上層政治結構干預的共同影響。“土地文化模式”這一概念不同于常見的土地產權、所有權等概念,更加關注不同的群體基于土地的利用模式差異所形成地不同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包括、但不僅限于土地的所有權、用益權,更多地關注在背后兩族對不同類型土地利用模式形成的原因和建立在這基礎之上的社會聯系。
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白馬藏人的土地文化模式。筆者將這一模式概括為“共享型土地文化模式”,在這一模式下,白馬藏人對財產所有權的觀念呈現出整體以公有制為主,穿插部分私有制的圖景:土地屬于每一個寨子中的族人共享,任何族人都有權在未開墾的土地上燒荒、耕種;族群領地內打獵所得的獵物也由族群共享;牲畜屬于私人財產,在白馬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與這一模式相對應的,漢族則屬于另一種模式,即“私有型土地文化模式”,這種模式強調對土地和其他財產的私人占有,各個家庭之間對于土地具有清晰、明確、嚴格的邊界。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將土地部落公有制歸結為野蠻時代初級階段的財產所有制:“雖然土地為部落公有,但耕地的占有權這時則被承認屬于個人,或某個集團,成了繼承的對象。聯合在共同家庭里的集團,大多數人都要屬于同一個氏族,而繼承法也不會容許耕地脫離氏族占有。”[1]382并且他認為,人類對土地的占有從氏族公有制到家庭私有制是一個線性的過程,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1]392。
馬克思對于土地公有制到私有制的線性進化觀點可以被看作是民族學古典進化理論的代表,然而這種觀點在進入20世紀后受到了以博厄斯為代表的文化相對論的挑戰。博厄斯認為文化是復數,而不是古典進化論的單數,文化取決于地方的需要,有特殊的發展史,而非古典進化論中的單線進程①。在博厄斯之后,他的弟子露絲·本尼迪克特進而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書中提出:“每一文化之內,總有一些特別的,沒必要為其他類型的社會分享的目的。在對這些目的的服從過程中,每一民族越來越深入地強化著它的經驗,并且與這些內驅力的緊迫性相適應,行為的異質向就會采取愈來愈一致的形式。
當那些最不協調的行為被完整整合的文化接受后,它們常常通過最不可能的變化而使它們自己代表了該文化的具體目標。”[2]本尼迪克特繼承了博厄斯對古典進化論的批判,認為基于特定的環境下,不同的民族基于其對自身環境的“體驗”而逐漸整合形成自己獨有的文化模式。筆者認為,白馬藏人的“共享型土地文化模式”正是他們在當地獨特的“內驅力”塑造下不斷適應的結果。在以往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中,艾德蒙R.利奇在《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中對于克欽人與撣人的關系論述對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可借鑒的藍本[3]。
雖然利奇在他的著作中更加關注克欽人“貢薩”和“貢勞”制度的相互轉換,對于土地問題并未給予過多關注,但是其研究依然暗示了不同生產模式和土地文化模式下的多民族基于對自然環境的利用差異而存在著“相互依居”,甚至相互轉換的可能性,而這一點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而在我國國內近年來針對多民族雜居型社區內部的民族關系變遷研究中,學者們對于影響民族關系的因素分析可以歸納為五種類型:資源競爭、歷史記憶、文化差異、經濟互嵌、文化共享。王明珂基于對華夏文化圈、吐蕃文化圈等主要文明和依附于邊界的青海河煌、鄂爾多斯、西遼河等區域社會地歷史學考古學研究,從宏觀的視角下提出了一個針對民族關系和民族認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框架,在這一框架內,資源關系與歷史記憶作為兩個重要因素相互影響,共同塑造了民族認同和對他者邊界的劃分[4]。
王明珂還在《藏漢關系的新思考:一個反思性歷史研究》[5]和《地盤、遷徙與歷史記憶:藏彝走廊兩種社會形態分析》[6]中從更加微觀具體的人類學視角出發,基于特定的民族社會田野調查(藏族、彝族)進一步完善了這一理論框架。王明珂的資源競爭、歷史記憶理論對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他之后,大量的學者在這一理論框架內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拓展,結合中國當代城鄉一體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和重構,提出了“文化差異”“文化共享”和“經濟互嵌”理論視角。
例如劉志揚基于資源競爭視角,認為擁有相同歷史記憶的白馬藏族村落在針對資源競爭是的不同反應,表現為對自己族群認同的不同反應[7]。韓雪將蒙漢關系的近代變遷歸結為歷史記憶、人口交流和由資源競爭推動下的文化因素[8]。楊洪林將歷史上的族際關系變遷歸結為文化差異與資源競爭[9]。蘇二龍將視角焦距于回漢間的歷史記憶與商業往來[10]。而在經濟互嵌和視角下,郝亞明[11]、馬麒等人[12]分別從宏觀的理論邏輯和具體的田野調查中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在“資源競爭”“歷史記憶”這一大的理論框架下,不同的地區的族群社會會基于自然環境、地理位置和生產方式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具體交融路徑,例如馬麒、韓富祥的《甘肅夏河回藏經濟交往與民族和諧共生研究》中體現為回漢間的“熟人關系網”“貿易往來”“資源互補”三重關系[12]44;在劉志揚、曾惠娟的《四川松潘藏寨族群身份變遷研究》中體現為藏漢間的通婚關系[13]。
而在針對白馬藏族地區的民族關系研究中,王萬平基于美國學者摩爾根、克羅伯和懷特等人的“三層結構”理論構建出影響馬藏族地區民族關系的三層結構和三種作用力:其中,最基層是經濟基礎,中間是社會結構,最上層是意識形態。在這一結構中,白馬藏族與漢族在文化引力和經濟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漸形成一個互嵌社會[14]。白馬藏人自古沿襲著以農耕為主,兼具畜牧、采集和狩獵的計生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白馬藏人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文化。在土地文化模式上表現為:土地所有權的邊界是模糊的、由族群共享的,而在土地上的勞動及其成果是私人所有的。
相對而言漢族對土地邊界的概念是精確的、私人所有的。當兩種模式(事實上也是兩個族群)未達到持平的狀態時,“共享型”模式是可以包容“私有型”模式的,這也是兩族歷史上能夠共存,白馬藏族能夠接納漢族進入的原因,而隨著當地人口的增長,村落的合并,居住空間互嵌,漢族的“私有型”模式變成主導時,事實上就是對“共享型”模式的分割、破壞與挑戰,使得“共享型”模式名存實亡。在這一過程中,人是“演員”,不同的土地文化模式才是族際關系真正的驅動力。下面,筆者將詳細梳理以兩種土地文化模式為核心線索的三個歷史時期,證明這種文化模式的不同是如何對該村百年來兩族族際關系產生影響的。
二、共生共存——早期兩族關系的構建
作為一個藏漢混居型村落,C村“藏族占山頭,漢族居水頭”的基本格局早在清朝初年就已經初步形成。但當時的白馬藏人山寨和漢族村落不論是生活、生產,還是社會關系上,基本可以看成是兩個分開的村落。而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混居村,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
在最初接觸的階段,雙方的基本關系為:白馬藏人為主,漢族人為客。白馬藏人在早期愿意接納漢族進入他們的“生態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在白馬藏人的土地文化模式當中,位于低海拔河谷地區并不屬于白馬藏人的“核心領域”,而是意味著洪災風險的“邊緣領域”。因此當最初的漢族移民提出“租借”河谷的土地用來定居時,白馬藏人并無不準。而雙方這種主客關系,隨著白馬藏人對漢族所提供的商業通道和物資交換的依賴而逐漸穩固,形成了雙方互補共存的相處模式。
三、鄰里嫌隙——空間互嵌下的糾紛與矛盾
明清時期,當地白馬藏族與漢族融洽的族際關系得益于雙方互補的計生方式和錯位差序的土地價值排序,在這種錯位排序下,白馬藏人并不將土地視為排他性的私有財產,因此漢族的進入定居并未引起白馬藏人的排斥與矛盾。然而,從清朝末年開始,兩次社會大環境的重大改變使得白馬藏人的土地觀念和計生方式經歷了重大變革,也直接導致了當地白馬藏族和漢族之間的族際關系走向轉折。
(一)白馬藏人土地價值序列的提升
清朝末年,隨著更早時期漢人的遷入,這一地區建立起了對外界——其他以漢族為主體的、更大規模社會網絡之間的聯系。雖然事實上該地區從古至今一直處于封閉狀態,地理環境與交通條件并沒有得到改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搬入C村的漢族是一個流動性更大的群體。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職業(經商),另一方面,作為遷入移民,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與曾經的生活地保持聯系,這種聯系包括商業關系上的和親屬關系上的。基于以上兩點,漢族移民事實上成為一個傳播媒介,打通了白馬藏族山寨和漢族農耕地區的交流渠道,并將這種聯系的結果間接作用于本地的白馬藏族居民之中,構成了整個社會網絡的一個單元。
以這一社會網絡單元作為基礎,罌粟作為一種新的特殊作物傳入并改變了白馬藏人的整個生產結構,進一步影響了白馬藏人的土地觀念。1858年,清政府開始逐步在中國推廣鴉片種植,期望通過這種方式與英國1858年,清政府開始逐步在中國解禁鴉片種植[19]。在之后的數十年里,鴉片和罌粟種被帶入隴南,白馬藏人開始接觸到這一外來物。正如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鴉片在白馬藏人群落中一 經傳入,就立刻迅速地蔓延開來,以至于當時的白馬寨中,不論男人、婦女還是老人吸食者占十之八九之多。由于川北隴南地區的光熱條件非常有利于罌粟的生長,在中央政府解禁鴉片之后,這里的鴉片種植量開始大規模增加。在這一大環境下,四川平武到甘肅文縣一帶的白馬文化圈①[20]也開始種植罌粟。罌粟種植在文縣地區白馬藏族社區內的興起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鴉片的藥用價值和生物成癮性,使得其成為一種剛性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當時鴉片在全國的廣泛傳播,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成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硬通貨之一,鴉片膏與其他貨物的兌換比率極高,種植罌粟帶來的利潤遠遠大于白馬藏族地區傳統貿易中的其他貨物,“鴉片除了具有能夠滿足人們消費的作用外,在民國時期,四川的一些地區鴉片就充當一般等價物,作為商品交換與支付的手段,具有貨幣的功能。”[21]根據當地的老人們回憶,在民國時期,在罌粟種植園工作的工人每天早上會去罌粟地里采集罌粟花的乳白色汁液(被初步加工提煉后就成為鴉片膏),作為東家和長工之間默認的一項傳統,在清晨這一固定時間段內采集到的鴉片膏被視為長工合法收入的一部分。
一般情況下一天一個熟練工人可以為自己掙得1-2錢的鴉片膏收入②。四、土地制度的變遷與民族間共享式發展在改革開放后,當地兩族圍繞土地所產生的矛盾開始逐漸地化解。這種化解存在著多方面的原因。我們將當地兩族間關系的改善與矛盾的化解從時間軸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0-1999年,這一階段由于中國藥材市場價格走高,傳統耕地農作物價值的下降而使得山上林地重新變成當地村民眼中的寵兒,使得雙方之前矛盾聚焦的河谷耕地不再被人們所注意。
第二個階段是從黨的十八大召開直到今天,隨著五位一體戰略的提出和國務院精準扶貧基本方略的要求,地方開始尋求新的經濟增長、脫貧致富的出路。在文縣,縣委縣政府大力推動民族特色品牌和文化產業、生態保護相結合的新模式,農民擺脫了過去對土地的依賴,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無形之中從根本上化解了兩族之間的矛盾與糾紛,走向了最終的和解、合作、共贏之路。
五、結語:兩種土地文化模式的交融之路
將C村白馬藏族與漢族關系變遷的歷史加以梳理,可以發現:在兩族記憶長達三百余年的歷史中,雙方的族際關系一直是緊緊圍繞著土地這一核心線索變動的。在第一個階段,即交易接觸階段,由于白馬藏人的空間利用主要集中在半山處和更高海拔的林地與草原,而漢族進入后定居在河谷,雙方的居住空間呈現出錯位互補的關系。對于白馬藏人來說,河谷地帶的土地價值并沒有體現出來。在這一階段,由于居住空間的錯位和商品交易的互補,雙方形成了相互接納的局面,白馬藏人對于土地模糊、籠統的共享型觀念與漢族邊界嚴謹明晰的私有型觀念之間并未產生沖突。到了第二個階段,即土地沖突階段,原本兩族之間不同的土地觀念在新中國建立后,由統一的集體所有制所代替。
這一階段,山上的白馬山寨和山下的漢族村落被整合為一個混居型村落,雙方在居住空間上也開始嵌合,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在空間錯位下被隱藏的兩種土地觀念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而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的主糧政策和指標——壓力傳導模式成了這一矛盾的一針催化劑,使得兩種觀念間的矛盾具體轉化為兩個集體——白馬藏族為主體的四社和漢族為主體的其他三個公社之間圍繞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矛盾,而矛盾的激化也直接導致了當地居民對于雙方族際矛盾的“悲情敘事”式記憶,形成一道創傷的心理刻痕。對此,我們也應當科學地、客觀地看待。
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的調整具有滯后性,具體到C村,兩族之間在居住空間嵌合后,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并探索出一條雙方共存的合作模式,這一過程是充滿艱辛的,也是必然需要經歷的“陣痛”。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經濟互嵌階段。兩族之間終于迎來了最終的和解,這就是從“空間互嵌”到“經濟互嵌”的轉變[26]。在改革開放后,從藥材熱潮到電商旅游,新的經濟增長點將人們的目光從土地之中轉移到了對生態空間資源的復合利用當中。
C村作為文縣旅游扶貧的試點村,以旅游和電商兩駕馬車齊頭并進,給與了兩族村民合作的平臺。C村的綠水青山和獨具民族特色的歷史文化共同形成了一種“情景體驗”式的無形旅游資源,這種資源充滿了包容性,可以將所有的村民納入進來共同參與,同時又不可分割、不可被私人占有。新的資源和新的發展模式將人們緊緊的聯系在了一起,形成“命運共同”“共享發展”“融合發展”的三種全新發展模式。王萬平曾在針對白馬藏區的研究中提出白馬藏人文化交融的三種動力,其中第三條“互補性經濟的推力”[14]42正是筆者所調查到2000年以后C村藏漢兩族在新的發展模式下所找到的交融和解之路。
民族文化論文: 發揚民族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建設研究
C村藏、漢兩族矛盾的根源在于雙方“錯位的”土地文化模式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政策背景下能否相互包容。而“命運共同”“共享發展”“融合發展”的全新模式從根源上跳出了這一命題,找到了一條兩族能夠共同發展致富的道路,形成了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框架下真正的合作、共享、共贏。在今天,人們的目光更多的聚焦于如何提升合作質量、細化分工,在共有的空間中尋求資源利用的最大化,而曾經的矛盾,也必將隨著兩種傳統土地觀念的替換而被人們所淡忘,迎來最終的和解。
參考文獻
[1]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85-392.
[2](美)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錫章,黃歡,譯.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56.
[3](英)艾德蒙R利奇.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楊春宇,周歆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123.
[4]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7:410.
[5]王明珂.藏漢關系的新思考:一個反思性歷史研究.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12(38):221-252.
作者:張同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