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藝發展之“中道”
時間:2020年06月17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文藝的發展離不開繼承與創新。繼承通常與過去相連,創新又指向未來。然而,與過去相連的繼承和指向未來的創新畢竟只能落實在當下。因此,我想將話題帶到當下,如何在當下將過去與未來連接起來,如何在當下解決傳承與創新的矛盾。不過,對當下的認識也是最困難的事。就像“認識自己”是一件難事一樣,認識當下也是一件難事。因為認識無法與認識對象拉開距離,而距離又是我們獲得認識的必要條件。“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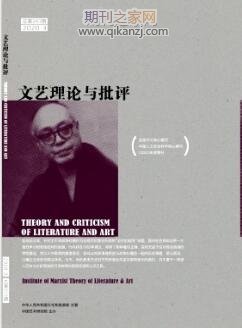
”不與認識對象拉開距離,就無法獲得關于對象的認識。我們之所以難以認識自己和當下,因為我們缺乏距離。就自己來說,是缺乏空間距離;就當下來說,是缺乏時間距離。對于我們認識當下的現實來說,馬克思主義有重要的啟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于我們擺脫過去和未來對現在的遮蔽以及對于我們逼近當下來說,非常有效。在馬克思之前,黑格爾的辯證法已經流行開來。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法突破自己的正反合模式,很容易走向妥協或者和解,我們可以稱之為和解辯證法。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文藝理論與批評倡導以跨學科的、綜合的文藝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框架來觀察、分析和評論當代中國以及世界的文藝現象和思潮,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作積極貢獻。本刊探索中國的、第三世界的文論和批評方法,倡導鮮明的問題意識,重視對1980年代以來的學術范式和話語進行清理和反思。
在馬克思之后,法蘭克福學派的否定辯證法引人關注,在否定辯證法中永遠沒有和解的時候,否定辯證法具有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或許我們可以將黑格爾的和解辯證法稱之為保守辯證法,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否定辯證法稱之為激進辯證法。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發展、經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經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檢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指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先行的理論建構。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稱之為溫和辯證法。
盡管溫和辯證法既不像保守辯證法那么有系統,也不如激進辯證法那么有鋒芒,但是對于我們認清當下的現實來說卻比較有效。因為當下的現實總是處于過去與未來的遷徙之中,它既不如過去那么穩定,也不如未來那么浪漫。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當下的現實比過去的傳統和未來的理想要更加溫和。但是,我們今天的文藝,無論從批評還是創作的角度來看,似乎都不那么溫和。如果我們將基于當下的現實的文藝稱之為“中道”的話,我們的文藝似乎有點偏離“中道”。
首先,從文藝批評的角度來看,當前的文藝批評顯得“過”和“不及”,偏離了“中道”。文藝批評偏離“中道”的現象有若干種,我這里簡單說三種。一種是“不及”,也就是缺乏批判精神。一種是“過”,也就是“批判”過猛,甚至上升為謾罵和約架。特別是在今天這個自媒體時代,過激批評容易博得眼球。在充斥商業批評的時代,文藝批評的“過”和“不及”表面看起來是相互沖突的,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批評家通過怒懟引人注目,通過吹捧獲得利益,這符合商業批評的邏輯。為了破除商業批評的魔咒,我曾經嘗試提倡學院批評。[1]但是,學院批評也有它的問題。由于專業競爭的壓力,學院批評家喜歡做過度批評。
為了標新立異、獨抒己見、乃至語不驚人死不休,學院批評家們會過于強調自己的發現,不管他們發現的內容是否重要、是否符合藝術家的意圖、是否符合受眾的接受心理,只要是所謂的新的發現,就會被放大成為批評的全部內容,難免有穿鑿附會之嫌。學院批評家采取的這種專家式的讀解,作為一種學術訓練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常規的藝術批評就值得警惕。這種批評對于文藝創作和欣賞沒有什么好處,因為批評家既非基于創作經驗也非基于欣賞經驗,而是基于所謂的學術邏輯。學院批評可以生產知識,但是生產出來的是脫離文藝實踐的知識。
因此,學院藝術批評會形成另一種過激批評。避免文藝批評中的過激和不及,就需要回到“中道”。文藝批評的任務就是文藝創作和欣賞,而非標新立異。因此,文藝批評家要甘于說平常話,而不去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語不驚人死不休”是藝術家的追求,而不是批評家的追求。其次,從文藝創作的角度來看,目前也出現了“過”和“不及”的現象。我自己是做藝術理論研究和教學的。為了了解當前文藝實踐,我首先嘗試做文藝批評,側重美術領域。
后來嘗試做些創作,集中在戲劇和電影領域。理論研究是我的主業,批評是愛好,創作是第二愛好。因此,我講的創作和批評都會不夠全面。在美術領域,我們的創作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就,而且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美術領域的成功,源于保持了較好的生態,“過”和“不及”的現象不那么嚴重。在美術界,傳統、現代、當代能夠和諧共處,做到相互促進,和而不同。但是,其他藝術門類在國際舞臺上似乎沒有明顯的優勢。
原因很多,尤其是電影和戲劇這樣的藝術形式,不僅涉及藝術創作問題,還涉及產業體系的問題。但是,保持良好的生態,堅守“中道”,不跑偏,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就。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一方面是國家的崛起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是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如果文藝家們能夠不舍近求遠、標新立異,創作出體現這個時代特征的作品,就一定是偉大的作品。
作者:彭鋒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