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話語的堅守與傳承以《盛京時報》文藝副刊為考察中心
時間:2022年05月30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 要:《盛京時報》文藝副刊“神皋雜俎”的語言既有白話又兼用文言;文體形式多樣;題材豐富多彩,既有描寫社會生活、軍閥混戰的現實主義作品,又有志怪、志異的通俗小說。從“神皋雜俎”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的辦刊理念可以看出其并不是一味逐新,也未果斷棄舊。隨著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加劇,“神皋雜俎”各欄目的女性題材、女性形象也在發生嬗變,彰顯了東北社會對待女性解放、女權等新思潮的傳播和存疑。“談業”“諧文”等專欄一直堅持文言創作,以一欄目之微薄之力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輸出,體現了對民族話語的堅守與建構。“神皋雜俎”的報載文學在日本報人殖民“共榮”的主辦方針下,通過自己的特色專欄堅守民族獨立的語言與文化,在關乎新舊的討論中推進東北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呈現了東北現代社會面對日本早期殖民語境下的掙扎與堅守。
關鍵詞:報載文學;《盛京時報》;文藝副刊;“神皋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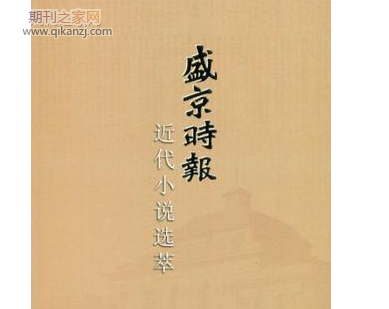
報載文學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承載大量文學作品、文學評論的文藝副刊或者專門的文學類報紙、雜志開啟了中國近代民智。如果以時間線性發展來界定文學史的發展歷程,那么報載文學在經歷新文化運動、新舊二元是否真正對立、殖民場域等過程中的嬗變可見一斑。考察東北現代文學發生期的發展樣態,放至20世紀初期的政治語境下,任何文化行為的外在表象與意識形態建構之間的對應與對立都有重新檢視與深入檢討的必要。《盛京時報》的文藝副刊“神皋雜俎”即勘為一個較好的視點,成為東北現代文學發生期的重要維度。日本自明治維新后踏上向外擴張的資本主義道路,因此 1905 年日俄大戰后,日本妄圖以“東亞合作”①為粉飾而向亞洲其他地區擴張。《盛京時報》是日本報人中島真雄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主辦的,也有人說中島真雄是“文化間諜”②,無論何種身份,中島真雄和日本政府的目的都是要在東北掌控輿論,以利日本實現“東亞共榮”的長遠目標。
《盛京時報》雖為日報,但每日的版面不固定,多為8版,也有4、12、14和16版的時候。文藝副刊“神皋雜俎”的版面大多在第3、5或7版,其他版面還包括“論說”“中外要電”“東三省新聞”等欄目,甚至還有專門兩個版面的廣告。“神皋雜俎”由該報著名編輯穆儒丐在1918年1月12日創辦。學界對《盛京時報》作為近現代東北社會傳媒的研究成果較多,如《〈盛京時報〉新年獻詞對“國家”觀念的消解與構建》《〈盛京時報〉“新年號”小說征文考略》《近代日本人在華中文報紙的殖民話語與“他者”敘事——以〈盛京時報〉〈泰東日報〉的偽滿洲國“建國”報道為例》《近代東北災荒史研究中的新聞資料使用探討——以〈盛京時報〉為中心》《日本殖民政策與“滿洲共同體”認同的制造——基于〈盛京時報〉的考察》等。對該報文藝副刊展開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有單獨一種文體的考察,如《民國初期〈盛京時報〉 文言短篇小說傳播考》《20 世紀初東北舊體文學研究——以 〈盛京時報〉 舊體詩為中心的考察》《抗戰時期東北報載戲劇生存樣態研究——基于〈盛京時報〉與〈大同報〉的對比考察》等。
也有將《盛京時報》或者文藝副刊分時期研究的,如碩士論文《東北淪陷區〈盛京時報〉副刊〈神皋雜俎〉研究》《〈盛京時報〉研究——1906至1931年有關文學和歷史的研究》,更有博士論文專門對擔任《盛京時報》文藝副刊主編的穆儒丐展開研究——《穆儒丐論》。但考察其文藝副刊作品所折射出的中國近代東北區域報載文學在特定語境下進行獨立話語建構問題的成果相對較少。“神皋雜俎”的語言既有白話又兼用文言。文體形式多樣,有小說、詩歌、散文、游記、劇本、評論等;題材也是豐富多彩,既有描寫社會生活、軍閥混戰的現實主義作品,又有志怪、志異的通俗小說。這些文學作品豐富了現代報載文學,即使在1931年后日本炮制的偽滿洲國文學圖景中也是不可忽視的存在。
一、白話與格律詩:“兼容并包,眾聲喧嘩”
從“神皋雜俎”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的辦刊理念可以看出其并不是一味逐新,也未果斷棄舊。“新”“舊”只是新文化運動后出現的被簡單化賦義的用詞,這種二元對立涉及一切社會領域,文學語言也不例外。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二元對立”,不如說是“兼容并包,眾聲喧嘩”。白話小說是“神皋雜俎”的特色之一,因為這種文體讀者面較廣,有利于報紙的傳播,小說連載更是發行量的保證。早期作品有穆儒丐的《女優》(1918年)、《梅蘭芳》(1919年)、《毒蛇罇》(1919年)、《香粉夜叉》(1920 年)、《落溷記》(1920 年);于忠祿的 《離恨艷史》(1919 年);王冷佛的 《珍珠樓》(1922年)等,開東北白話小說創作的先河。
副刊上小說的語言由最初的半文半白逐漸向純白話轉變;格式上由最初的無標點向句讀之間有隔點轉變,非常有利于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早在“神皋雜俎”創刊之前,《盛京時報》就有“白話”專欄,而且以白話的形式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主題大多討論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一些大政要事與具體措施,如晚清預備立憲運動開始之后,1906年發表的《大隈伯爵演說中國創設憲政論》這樣寫道:上論中國也要立憲了,這個時候人人都聽說了,也有說立憲好的,也有說立憲不好的。說立憲好的人就打算往后君民聯絡一氣,上下的意思就是一樣,君有君權,民有民權,漫漫的也就跟各國一樣了。說立憲不好的人,大概是做官的居多,他們心里想著要是立了憲,百姓們就敢說話了。皇上家什么事也都不能由著自己辦了。皇上將來可就沒有一點法子了。你說這可怎么好哇!①這里的白話已經非常接近人們的口頭語言,貼合“白話”的真正含義。
副刊“神皋雜俎”創辦之后,白話小說成為其主要報載文學形式,例如《女優》已經呈現比較自如的“白話”,沒有“之乎者也”,不稱“汝”“吾”,基本上完成了文體、文辭與文風的轉換。《女優》人物云紅、愛如的對話可見一斑:愛如說,我不能照你這樣瞻前顧后的。我既把話說出來,就不能改悔。云紅說,你以為我有后悔的意思嗎?那我成了什么人。你要知道,凡是都不能由人算的。我們這樣想,后來就許辦不到。俗話說得好,盡人事聽天命。我們以后的運命,固然在我們去作,一半也得歸老天爺主持。②從某種程度上講,“神皋雜俎”并不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使用白話的,使用白話的“傳統”早已有之,原因可能與文體有關,如政論、小說適合用白話表現,也有利于報紙的發行、傳播。“文苑”是專門刊登舊體詩的專欄,是《盛京時報》創辦伊始就有的專欄,“神皋雜俎”創辦后才移至副刊中。
格律詩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神皋雜俎”并沒有一味推廣白話小說,而是將“文苑”專欄作為副刊的編輯與讀者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梁和文人間唱和的主要陣地,刊登的題材大多是傳統格律詩常出現的詠史、抒情、送別、唱和等。唱和詩是“文苑”的主要內容。唱和詩是古代詩人相互間應答酬謝所作的詩詞,分為依韻、用韻、步韻及和詩四種形式。如何恨蝶的 《和怡園先生落花詩》、漢南鶴的 《和冷佛先生感懷詩步原韻并序》等。也有根據奉天時事唱和的,時間往往長達一個月,如根據《劉問霞拈花微笑圖》展開的唱和詩。
分別有署名伴琴、趙錫斌、幻石、竹儂、樞忱、伯璋、塋鶴、恂如等人發詩和紅豆詩人原韻,包括《再疊紅豆詩人題劉問霞拈花微笑圖原韻》(伴琴)、《題劉問霞拈花微笑圖次紅豆詩人韻》(趙錫斌)、《題劉問霞拈花微笑圖步紅豆詩人韻》(幻石)、《再題劉問霞拈花微笑圖步紅豆詩人原韻》(竹儂)、《奉和紅豆詩人題劉問霞拈花微笑圖原韻》(樞忱)、《題劉問霞拈花微笑圖用紅豆詩人韻》(伯璋)等,韻腳分別為身、神、春、身、塵、顰;華、涯、花、栽、開、來。又如1919年4月3日,花奴發表詩作《梅蘭芳說部殺青在即 爰題四絕并柬儒丐》贊賞穆儒丐的小說《梅蘭芳》:膾炙何須烹頂鮮,耐人咀味亦堪傳。孤情我自憐幽賞,豈為難林賈客錢。穆儒丐隨后發詩《和花奴見贈》回贈花奴君:梅舌調羹味已鮮,箴時誰肯作奇傳。
輸他肉食多豪興,日擲纏頭十萬錢。①接下來,8日—19日,瘦吟館主發詩 《踵花奴題〈梅蘭芳〉說部韻并寄儒丐》,竹儂發詩 《儒丐君〈梅蘭芳〉說部脫稿率題四律》,趙錫斌發詩《讀〈梅蘭芳〉說部爰題四絕并呈儒丐》,周興發詩《〈梅蘭芳〉說部絕麟而后花奴瘦吟館主各題四絕,余亦敬踵前韻而合之并柬儒丐》,瘦吟館主又發詩《同瘦龜花奴識儒丐于福照樓歸賦四絕以志景仰》等等。這一組詩都圍繞穆儒丐的小說《梅蘭芳》而題,這種形式也是“文苑”中較為常見的詩歌模式,展現了報載文學的文人情致、活躍了文藝副刊的作品氣氛。這種類似讀后感又表達文人間沙龍性質的詩作,往往發表在“神皋雜俎”主筆穆儒丐發表作品的時候,除了小說《梅蘭芳》,他的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的《香粉夜叉》連載時也有這種情況。很多讀者通過“文苑”專欄發詩,發表讀后感,如杏林公子發的《讀香粉夜叉有感》《再題香粉夜叉七絕四首》,連廣發詩《讀香粉夜叉率成七絕二首》等。《盛京時報》是刊發唱和詩最好的媒介平臺之一。
首先,該報幾乎天天出刊,文人們唱和的詩作能夠及時刊登,得到彼此的反饋是寫作唱和詩的主要目的。其次,穆儒丐作為文藝副刊的主筆,他結識了很多文致相投的朋友,大家常在一起舉辦沙龍性質的活動,大家對于他的作品都是非常支持的,這也是為什么獨穆儒丐的作品刊載后,讀后感即唱和詩多的原因。“文苑”中除了刊發唱和詩,還有很多格律詩描寫社會現實,單純抒發個人情感,如早期疑為日本人宮崎所作的《對酒遣懷》:沬泗文章欲廢時,紛紛理學競新奇。讀書萬卷果何用,茶后酒前資作詩。②整首詩有韻腳,對仗工整。
內容抒發了在傳統學術受到質疑的時候,自己的所學只能作為寫詩的資歷和資本了,感慨新學頻出,舊學受沖擊的現實,生動寫出了當時的社會現狀。劉大白的《送斜陽》及《花前的一笑》刊登在“新詩”專欄,從中可以窺見新文化運動后新詩倡導者對新詩、舊詩的態度。其中《送斜陽》有韻腳、對仗工整,句數不同于傳統絕句和律詩:又把斜陽送一回,花前雙淚為誰垂?舊時心事未成灰,幾點早星明到眼。一痕新月細于眉,黃昏值得且徘徊!③《花前的一笑》則屬于當時完全意義上的新詩:沒來由呵,忽地花前一笑。是為的春來早?是為的花開好?是為的舊時花下相逢。重記起青春年少?——都不是呵。
只是沒來由地一笑。為甚不遲不早,恰恰花前一笑?——靈光互照,花也應相報。悄悄,沒個人知道,到底甚來由?開花也不會了了。……1923年3月20日在紹興①劉大白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力倡導新詩,他本人在新文化運動前就嘗試用白話寫詩,從《花前的一笑》中可以非常明顯感受到中國古典詩詞中寫景抒情的意境,還有古詩常用的“甚”字,不過有新詩非常明顯的特點:句數靈活、沒有工整對仗,但卻明晰押韻,讀來朗朗上口。新詩作為一種完全不同于“文苑”舊詩韻腳、對仗的詩歌體裁是1920年登上《盛京時報》頭版的,刊登了當時新文化運動干將胡適的《歸家》和羅家倫的《雪》。繼而在1921年開設了“新詩”專欄,副刊在1923年的8—10月期間刊登了大量文章討論新詩、舊詩問題,副刊的編輯不做任何表態,期間大量理論觀點及新詩、舊詩大量涌現,呈現了當時東北文學獨立的文學論爭的聲音。
二、女性文學:彰顯民族解放
隨著社會的流衍,“神皋雜俎”各欄目的女性題材、女性形象也在發生嬗變,彰顯了東北社會女性解放、女權發展等新思潮的傳播和影響。“神皋雜俎”刊登大量女性照片,很多照片展現的是外國婦女的形象與風情。如《美國婦女之繪足》表現婦女夏天赤腳在小腿上作畫,“爭奇斗巧,妙不可言”;又如《美國學生之開放日》,講述美國女學生畢業或者放假情形;還有美國紐約發明的《兒童汽車》;上衣伴有印度刺繡的《倫敦上級婦人之新服裝》,以及《美國上院女議員》《美國婦人之海浴衣》《最近之英后即皇女》等,還刊登過“西洋名畫”《莫那利沙》(《蒙娜麗莎的微笑》)。《盛京時報》充分發揮了報紙傳媒的特點,利用照片等非常形象的表現形式向遼沈大地的民眾展現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以西方女性的形象啟發遼沈女性突破傳統枷鎖的桎梏。
“品花”專欄登載的是文人品評妓女的文章,隨著女性解放的呼聲日益高漲,“品花”專欄逐漸銷聲匿跡。“神皋雜俎”刊登過一封作者來信,作者在信中除了表明欽佩穆儒丐的文筆,還建議“不必再作那種無意識的花評,將貴報花評欄改作香粉地獄的變相圖,用莊嚴的筆墨描寫,拒絕那種卑下肉欲鼓吹的惡文字”②。由此可見,社會現代化進程讓更多的讀者希望得到更多健康、新鮮的內容,這其中自然與女性地位受到日益重視有關。不過在當時,包括女性解放在內的很多新思潮在出現之時還是飽受爭議的,“神皋雜俎”中的很多文章都在議論女性解放或者發表對女子的看法。
除了各類評論之外,小說也是討論女性問題,表達對女性、女權思想看法的重要文學形式。穆儒丐在他小說連載前的預告就探討過此類問題,如在《落溷記》連載前的“新小說預告”:書敘一舊家之女已字人矣,一日偕其父母赴滬上探親戚,兼購妝奩。不意其女感受新思潮背舊婚而締新盟,卒至淪落北里為倚門賣笑之人。情節多有可觀,對于新舊思想持以公正之評判,誠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也,不日刊布,喜閱儒丐小說者當以先睹為快也,此啟。①
《落溷記》描寫了李鳳樓由一個千金小姐最終淪為妓女的故事。在作者眼中,“父母之命”雖有弊端,但倡導“女權”等一切“解放”的事物更是害人不淺。鳳樓正是在上海接觸了雜志《解放》,里面倡導女權的一系列白話文章打開了鳳樓的視野。上海作為口岸,經濟文化都非常發達,鳳樓舅舅家的姐妹穿著時髦,這些都沖擊了準備接受父母包辦婚姻的鳳樓。穆儒丐在小說正文敘述中,總忍不住跳出敘述來發表議論:習俗難移,比什么都厲害……既肯教子女入校讀書,也可證明他們不是十分頑固的。可是到了議婚一事,偏生不教兒女與聞,蒙席蓋井的,生怕兩個人知道了,有許多不便似的。……結婚的當事人就當兩個傻子一樣。
……入了洞房,男女兩個甚至有彼此不知姓名的。這種頑固,不知是那位圣人留的。真不亞隔山買老牛,好壞盡憑個人運命。②茲僅演義如此,亦足以作新世女子當頭棒喝矣。③在《香粉夜叉》里穆儒丐也發過議論:現在的新人物,沾染點文明氣兒,動不動便說家庭專制,婚姻不自由,于是便有提倡自由結婚的,男女對說對講,應當沒毛病了。殊不知這自由結婚,也有不滿人意的。作書的有個朋友,他的老婆便是自由來的,兩個卻時不常的打架拌嘴,鬧得家庭里一點幸福也沒得著。
夫婦的愛情更說不上了,如今只落得男子跑平康里,婦人在家里講自由。街坊四鄰誰不笑話。④可以說,穆儒丐對待傳統婚姻制度和新的女權解放思想各打了二十大板。同為“神皋雜俎”主筆的王冷佛的著名小說《珍珠樓》,開篇就諷刺媒妁之言、指腹為婚等封建婚姻陋習:天下萬國,莫不以婚嫁為重。獨有我中國習俗,于此人倫大道,全不講究。上等的富貴人家,擇門第、講闊綽;下等的爭彩禮、論聘資。至于小夫婦的本身,也不問人品志趣是否相合;身體的長短肥瘦是否相稱。只憑那媒妁之言,模模糊糊就訂成夫婦了。⑤作者提到有個財主谷次竽因自覺相貌丑陋,對不住他貌美的妻子,只能聽憑悍妻刁蠻,在家“不敢大聲出氣”。
這個例子雖顯荒誕,卻也是道出夫婦不相配的尷尬之狀。《香粉夜叉》發表在1919年,《落溷記》發表在1920年,《珍珠樓》發表在1922年,新文化運動雖已傳播至東北,但女性解放的合理性尺度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直到1932年,《裙》的發表表明女性解放在東北大地依舊是個熱度不減的話題:一股保守派而自命為老成些的人常常說:“目下世風不古,人欲橫流,廉恥道喪。女子們赤臂露腿,怎么直線曲線,傷風敗俗,莫此為甚。”①女主人公——密司陸雖然認為此話過分,還是把短裙換成了長至腳踝的長裙,結果走在校園里被議論紛紛,甚至嘲笑;除了男性,很多女性也有微詞。大家說她“長裙曳地,這是林妹妹的東西”“似乎是戲臺上的蘇三起解”,“她平常穿的裙也是短得最利害,現在物極必反,以今之長補昔之短了……”密司陸成了學校師生的圍觀對象,窘迫難耐。于是她被迫無奈,只能再度換上“長不滿三寸的黑短裙,赤露了兩條在寒風中打戰的大腿,披起了洋絨衫,著著新式的油皮鞋,充一個所謂摩登式女郎”。②
短裙—長裙—短裙,作者通過換裙的敘述比較生動地刻畫了當時大部分人對于新事物的一種態度。學校的學生自詡勇于接受新事物,但他們屬于激進的一派,即接受新的就完全拋棄舊的,長裙屬于傳統服飾,自然得拋棄。密司陸并沒有深刻認識到女性解放的根本,而只是糾結于服飾等外在的事物,太在意世俗的評價,造成自己糾結矛盾的心態。與之相對,反而很多底層的女性觸碰到了女性解放的真諦,想要自我掌握命運。《女優》中借愛如的口說出當時女性思想解放的縮影:“什么老天爺,我就沒這些迷信。老天爺若有眼睛,還不教我們當唱戲的呢,將來什么叫人事,什么叫天命,我一概不管。我就是我,正了呢,我也不喜歡;歪了呢,我也不發愁,倒落個痛快。”③
其他討論女性和新舊婚姻的文章還有很多,如李澤田的短篇小說《什么夫婦?》。小說描寫了舊式婚姻下的兩對夫婦,一對是時髦青年白秋和鄉下老婆,抽旱煙、“苞米式的尖腳”;另一對是土頭土腦的劉老大和在師范學校卒業的女學生。兩對夫妻的生活沒有一天和美,結果白秋與劉老大妻暗生情愫、海誓山盟,最終結局是兩對夫婦各自離婚,再重新結合——白秋娶劉老大妻,鄉下老婆嫁劉老大,這時,兩對夫婦反而受人羨慕。世人皆認為此事“不在人倫之內”,作者卻認為這些都在“情理之中”。④乍看故事,未免荒唐,可在當時新舊文化沖突強烈的背景下,不甘“父母之命”,順從個人意志,似乎這一切又是逐“新”的表現。這說明在當時的東北社會,女性地位、婚姻制度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引起了社會各個層面的廣泛關注。“神皋雜俎”刊登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人物胡適在協和醫校發表的演講,題目為《中國歷史上婦女的地位》。⑤胡適提到著名外交家錢恂的夫人——單士厘歷時十多年出版完成了《清閨秀藝文略》5卷本,胡適受邀寫的序言,題為《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這本書告訴我們在近三百年有一千三百一十個婦人寫作詩文,并有大部分的作品已曾印行。這個數目本身對于我是一個啟示。”⑥
接著,胡適將這些女作家按出生地進行了統計,統計出各個省份女作家的人數;還按類別對作品進行了分析,得出這些作品99%是詩。胡適進一步闡明受教育是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手段,“文藝教育雖然淺浮,不足實用,但卻曾提高了婦女的地位”。因為“在中國受教育的男子是很少的,而受教育的婦女更為罕見,所以她們也就更被尊敬”。⑦接著胡適從母教角度談了婦女受教育的好處,就是她們能夠更好地教育下一代,舉例歐陽修和顧炎武的母親對他們的影響。可以說,胡適對中國傳統女性的評價比較中肯,傳統女性受教育實屬不易,還有如此多的詩作問世,確實應該得到更多的尊重。雖然認為“文藝教育淺浮”,但“母教”的觀點突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放至21世紀依然有其合理性和先進性。三、特色專欄:傳承民族語言有研究者將九一八事變后無明顯反殖民性特征的一類作品稱之為解殖文學①,認為居住在殖民地或者在殖民地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在殖民歷史現場創作并發表多種多樣的文學作品,屬于隱去了作者情緒的“零度寫作”。
20世紀提及“零度敘事”的就屬盛行于90年代的“新寫實主義”小說思潮。該小說思潮描寫生活的雞毛蒜皮,事無巨細,將作者話語隱匿,完全展現人物的瑣細生活。從這一點來看,“神皋雜俎”的某些專欄確是只關乎文字、語言、生活,無關政策和反抗。上文提到“文苑”里的很多詩詞屬于唱和、詠景狀物之作,而另一專欄“談業”里的短篇小說則以純文言的方式講述奇聞軼事。這些都可以看成解殖場域下,東北報載文學另一種不附和日本殖民的聲音。“談業”是被研究《盛京時報》文藝副刊的大量學者所忽視的一個專欄,此專欄是副刊的一個傳統欄目,刊登國內外傳聞、鄉村軼事、志怪、志異,早期有《左忠堂軼事》,描寫西藏風俗的《藏風瑣述》,也有《林肯》《波斯王討阿梭斯山檄文》《撒克遜童謠》《希臘力士之殺怪物》等。比較獨特的是此專欄一直堅持文言創作,刊登志怪、志異的小說,沒有長篇連載,都是短篇。
可以說“談業”專欄以一欄目之微薄之力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輸出,用中國古典的獨有語言續寫《聊齋志異》式的傳奇,這何嘗不是在殖民話語強壓下的文學主體話語建構。渠道和載體之一就是我們中國獨有的話語——文言,題材和體裁都接續傳統的古典小說——《聊齋志異》。《芙蓉瑣聞》《成仙奇聞》《劉四姐》《孝子尋親記》《冀州二兄弟》《崔某》《殺誤》《謀殺奇報》《女鬼撩人》等小說或是仙狐題材或是記錄天賦異稟的奇人軼事,彰顯善惡有報的中國古典小說主題,成為“神皋雜俎”獨具特色的招牌。而且此專欄中故事大多發生在遼寧地界,對于報紙的傳播和讀者接受都非常有利。“芙蓉”舊指鴉片,《芙蓉瑣聞》中寫了幾例吸食鴉片人的特殊癖好。《劉四姐》中描寫劉四姐被自家嫂子和其奸夫冤枉,遂投井自殺,被新來的知縣昭雪的故事。② 《崔某》寫了遼河附近漁民崔某尤其擅長泅水、捕魚,異于常人,利用自己的異秉為民除海怪,因傷勢過重而犧牲的故事。漁民感恩于崔某為民除害,為其購買棺槨葬于河濱。③
《殺誤》敘述的故事發生在清朝光緒年間的遼寧丹東鳳城,也是因果報應的傳統敘事模式。“此事固為村俚之談。其中實藏因果之理,蒼蒼者天,孰謂一無靈應耶?”④在清朝光緒年間,殺通奸者是無罪的。甲某和妻子結婚多年無子嗣,甲某聽信了村中流言,懷疑妻子有外遇。“殺誤”乃誤殺之意,甲某本欲殺其妻及奸夫,不料陰差陽錯將自己弟弟行里的更夫誤認作“奸夫”殺害了,“淫婦”即為本欲趁甲某不在家去甲家行竊的鄰居婦人。《成仙奇聞》寫了舊時一座神廟的傳聞,廣行善緣,被人們稱為“活佛廟”,主要原因在于該廟“每年必有一人羽化而登仙”。新來的知縣總覺其中有蹊蹺,遂令手下“李二張三”去廟里一探究竟,終于發現端倪,將寺廟圍住,住持交代:“本寺冬令收養貧民,使之豐衣足食。選其面貌魁梧者,留備成仙之需也。以鐵柱貫肛門者,令死者面色不改也。”⑤僧人得到懲罰,百姓稱贊。《攜眷》講述柳生嫌棄妻子葉氏因貧血而逐漸衰老病弱的容顏,拒絕攜其隨己赴省城任職參謀,遭其父訓斥。作者評價:“柳生者,襄平人,性機警,能以小善結人心。”幾年后,葉氏病更不起。
柳生一日從省城返家,一反常態,帶上妻子隨行。六日后,葉氏在省城去世。因為柳生“以小善結人心”,固無人懷疑。柳生不旦在葉氏死后再婚一嫁妝豐厚的女子,而且之前在省城寓所已經有了煙花女子為伴。偵探雪君了解了事情經過,判斷此一謀殺案,是柳生間接殺害了葉氏,明知葉氏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還帶其車馬勞頓,致其殞命。眾人感慨柳生:“嗟嗟陰賊險狠,咄咄逼人,偶一不察,生命莫保。柳生攜眷之事,其小焉者也。若夫今日賊民之舉,隱微難見,形勢無惑,其陰毒之甚于此者,何可勝言。”①此專欄也有很多固定的作者和單位投稿,如署名趙北布衣子的發表了《冀州二兄弟》《老周志異——驚喜》《老周志異——柳妻》等,鳳城市省二師范學生白世俊、婁萬成、蕭玉崑等都分別在此專欄發文,如白世俊的《趙飛雄》、婁萬成的《王孝子復仇記》、蕭玉崑的《奇女子言行錄》。
從很多題目不難看出,志怪、志異題材不勝枚舉。文言的寫作并不等于迷信封建,善惡因果的題材只是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之一。隨著現代文明的進程,“談業”也用文言敘說反封建的故事。《青年枉死記》記聞了作者在街頭看見王裕生被封建迷信貽誤致死的真事。王裕生才23歲,只因“忽患時疾”,“其父母素尚迷信,崇拜偶像,每日惟買香燭錠帛,祝禱于偶像之前。或曰汝兒病篤,可速為醫治。曰吾兒病雖重,有菩薩保佑,不致有傷生之虞”。幾日后,病情加重,裕生父母更是請巫師到家里“捉鬼”,裕生受到這些巫師的驚嚇,病情加重。他的父母經親友勸說才將裕生送去就醫,為時已晚,“青年已溘然長逝矣,嗚呼哀哉,真可謂枉死者矣”②。
如果說“談業”和“文苑”無關乎反抗與激情,那么日本報人更希望看到的是暴露中國國內矛盾的文章涌現。1920年直皖大戰、1922年和1924年直奉兩次大戰造成東北地區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盛京時報》無論其他版面還是文藝副刊都在詳細跟進軍事動態,與對待反抗殖民題材作品的政策不同,控訴戰爭時局的作品占了文藝副刊的很多篇幅。其中大量的作者就是戰爭的經歷者,他們用自己的語言控訴了當時混亂的社會動態,留下了東北文壇獨特的聲音。“諧文”欄目發表了很多相關作品,大多用文言,或幽默、或諷刺、或憤慨,表達了東北人民對時局的關心,對百姓生活的憂慮。有以諷刺語氣發表的《新千字文》:“神號鬼哭,諸村逃光,果真黎難,臭蟲皆僵。直奉事起,居然很像,纛旗火毀,鳥官盡惶。此處知事,乃服洋裳,推位讓戰,因懷奉張。匪兵不去,賽過毒瘡,強奸婦女,搶劫紳商。”③
有用東北獨有的二人轉語言形式發表的《大帥好糊涂》④,全文13個小節,每段都是五句話,前兩句是實寫,后三句統一皆為:“大帥你好糊涂!哼噯噯咳喲!大帥你好糊涂!”實寫的部分全系時局的抨擊,如“內閣改組有政府,何苦用你瞎擁護”“三月進關旌旗舞,橫壓京畿據津沽”“四月開火全軍覆,黔驅一蹶自取辱”“地盤失掉歸舊窟,還教議員拍屁股”等。作者用通俗上口的語言、戲謔的語氣痛訴了當時奉天的政局。《時事諧聊》中也都是對仗順口的句子,共10小節,每小節19—23字不等,調侃當時混亂的軍事政局:“同人變作仇人,軍政府你去我辭……嘉偶偏成怨偶,某院長嫌貧愛富,何時破鏡重圓……參謀部忽而被圍,蔣尊簋雖覺尊榮,也鬧得束手無策。”
署名徐少谷的《黑暗時代賦》寫道:“日月晦冥,江山失色,遍地干戈,滿途荊棘,水混混兮不清,天沉沉兮否塞,雷轟轟兮炮發,雨飄飄兮血滴……”⑥從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只傳承了屈原的《離騷》形式,還油然發出類似當年屈原的悲憫痛心,戰亂使得社會民不聊生,百姓怨言四起。還有仿照《蘭亭序》所作的《選舉非常總統序》:“民國十年,歲在辛酉,季春之初,聚于廣州之非常國會,選總統也。佞黨畢至,議員咸集,此處有雪茄香檳,餅干咖啡,以及選舉票匭,分列左右。已預用金錢買妥,投票期間,雖無督軍省長之富,一訛一索,亦足以慰彼私情。”⑦
作者嘲諷了軍閥割據時期選舉的腐敗亂象,“佞黨”云集,只為私欲,不顧百姓死活。《武人禍國記》是仿《醉翁亭記》所作,依舊是對戰亂時局不滿的作品。“環國皆亂象也,其湘鄂川粵,子彈累累,槍炮多而輜重積者,戰場也。南北六七省,聲勢赫赫驚人,而吹胡瞪眼于上者,督軍也。”①作者諷刺了軍閥爭權奪利的丑陋嘴臉,武人對地盤的欲望導致了無休的戰亂。“賦”“序”“記”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主要體裁,仿古文是“諧文”專欄刊登反戰題材作品的主要形式,“諧文”和“談業”在作品語言上傳承了中國的傳統,保持了獨有的聲音,沒有在新舊二元對立中自我舍棄,這在報紙追求發行量的當時是比較難得的。
四、結 語
《盛京時報》作為現代紙媒,不知是信息傳播的滯后,還是報人刻意為之,關于巴黎和會的相關信息,1919年5月22日的副刊中才刊登了名為“意大利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拂袖離去”的“漫畫”,更不要說與此緊密相關的新文化運動了。因此,某種程度上東北地域的現代化進程較之內陸地區是緩慢而滯后的。體現在文藝副刊“神皋雜俎”中,比較明顯的特征就是并不一味刊登白話作品、提倡一切所謂新的東西,而是繼續刊發傳統欄目“文苑”“諧文”“談業”等。關注現代女性解放,文藝副刊的大量作品通過女性地位、婚姻關系中的形象嬗變表達社會對女性態度的轉變。
歷史的進程證明了這并不能稱之為“滯后”,恰恰多了這許多可供東北傳統文人感悟“現代”的時間,用中國傳統的文學語言和體裁堅守了民族性的主體話語。在此過程中,也得以窺見日本報人內藏“共榮”野心的主辦方針。一味像新文化運動那樣立“新”并不可取,東北社會一旦加快現代化進程,那么日本妄圖在意識形態或地理意義上霸權東北的野心便難以實現。可以說,“神皋雜俎”的報載文學見證了東北一隅現代文學發生期的樣態,不同于1931年后日本在東北的強勢殖民話語,早期的“神皋雜俎”在穆儒丐等一批較好掌握中國傳統語言的文人編輯下,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特色鮮明。文藝批評曾經將“語言”作為研究文學文本的根本,包括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批評方法。
語言絕不是文本的全部,但確實承擔了從創作到接受的最主要載體。如果說民族性的表現分為現實層面和觀念層面的話,那么語言無疑是屬于現實層面的展現形式之一,這是一種一脈相承的語言傳統,也是最直觀的表現。“神皋雜俎”的專欄作品正是以民族語言堅守和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學傳統,從“文苑”“諧文”“談業”等專欄作品中可見一斑。以穆儒丐、金小天、王冷佛為主要編輯的理念和身體力行地創作讓東北地區的很多文人堅守住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語言,并在整個社會的進程中逐漸厘清新與舊、破與立的論題,在關乎新舊的討論中推進了東北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新舊不是二元對立,民族與現代也可以兼容并包。民族性的觀念層面即是報人們在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中一直堅守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基因,是潛在的對文學體裁、語言等外在表達的價值內刻。從“神皋雜俎”的專欄設置到具體的文學作品,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民族國家認同讓這一時段的“神皋雜俎”顯現出無論社會形態還是文學進程都呈混合性的復雜面相,呈現了東北現代社會面對日本早期殖民語境下的掙扎與堅守。
作者:馮 靜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