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邊疆學”學科構建的幾個基本問題
時間:2019年03月06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近年來“邊疆學”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但“邊疆學”學科構建則處于困境沖突之中,包括在沒有一般“邊疆學”的條件下出現了構建“邊疆政治學”的情況,也有將“邊疆學”框定在中國范圍內構建“中國邊疆學”的情況。走出困境,需要以按照學科構建的一般規律構建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為目標,將民族國家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并在這一起點上將邊界作為研究的核心問題;從邊疆現象中揭示邊疆規律是“邊疆學”的基本任務。
關鍵詞:“邊疆學”,邊界,民族國家,學科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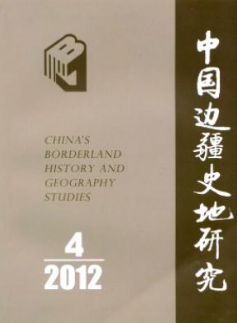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邊疆研究的積累與進步,許多學者不斷呼吁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學科體系。近年來,又有不少學者提出構建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但有些學者對其進展不是很樂觀,如孫勇等認為,“近年來學科建設的進展卻不大,很難說中國邊疆學的這一學科已經構建完成,學科體系已經基本成型”[1]。
筆者認為,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需要建立一個核心問題以及與此聯系的核心概念,正如張世明所指出的那樣,“每當談及邊疆學的建立,在筆者腦海里立即浮現的圖景,就是這一學科要爭取獨立‘建國’偉業。這不單是口號,更是行動的落實,不單是學科主權的蒼白宣示,而是要對智識領域進行有效占領。其中必然涉及其疆域四至的確定,涉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邊界劃分等一系列問題”[2](14)。
如果沒有深入研討這些涉及“邊疆學”的基本問題,那么無論是構建“中國邊疆學”還是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都會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筆者不揣谫陋,對這些問題發表初步的看法。
一、特殊與一般:當前構建“邊疆學”的困境
針對“邊疆學”的構建,張世明認為“一般而言,學科的內核地帶是比較穩固的,但學科的外圍邊疆地帶則往往比較模糊,并且多系未開發的空白或者低度開發的區域”[2](14)。伴隨著人們對“邊疆學”這一“未開發的空白或者低度開發的區域”開發,當前構建“邊疆學”出現了兩種奇怪的現象:一是將“邊疆學”框定在中國范圍內,不少學者執意要構建“中國邊疆學”;二是在沒有“邊疆學”總論的條件下,出現了“中國邊疆政治學”,并有相關著作問世。通過仔細研讀這些著作,筆者認為需要從特殊與一般的邏輯關系中思考構建“邊疆學”學科所面臨的困境和沖突。
(一)一般意義的“邊疆學”與“中國邊疆學”
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倡議可謂不絕如縷,如邢玉林先生較早發文提出要構筑“中國邊疆學”[3],馬大正教授也較早提出要構筑“中國邊疆學”[4],方鐵教授力主創建“中國邊疆學”[5],周偉洲教授近期所著的《關于建構中國邊疆學的幾點思考》急切倡議構建“中國邊疆學”,鄭汕編著的《中國邊疆學概論》是回應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嘗試。這些著作都是了不起的成果,在推動所謂“中國邊疆學”的發展上有著里程碑式的地位。
201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有“中國邊疆學原理研究”,反映了“邊疆學”構建的最新嘗試。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將“邊疆學”框定在中國范圍內,最近,有學者仍然堅持“真正擁有邊疆并需要創建一套理論體系來滿足實踐需要只是國家的一部分”,并認為“在目前情況下,‘邊疆學’如果成立的話,要限定它的范疇是‘某國邊疆學’,才具備應有的研究對象”[6]。
“中國邊疆學”天然與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糾纏在一起,給建立“中國邊疆學”帶來了不少麻煩,出現了被學者們認為是“跨學科悖論”[1]或者“學科殖民”的現象[7](67)。但從完成“中國邊疆學”學科構建的情況來看,其事實上已成了一項“爛尾工程”①。筆者認為,將“邊疆學”學科框定在中國范圍內,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因為科學是不分國界的,將“邊疆學”框定在中國,則最多是中國的邊疆問題研究。
一個國家有其自己的邊疆形成歷史和邊疆運動規律,在解決現實的邊疆問題時,有自己具體的國家利益、價值目標、原則和手段。作為一個學科,“邊疆學”應當超越某一個具體的國家,是人類對知識的探求,是對邊疆現象做出理論闡述的科學。一個國家要想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只有先掌握作為一般性學科的“邊疆學”為其提供基本知識和具體的邊疆運動規律,這一目標才能夠實現。當然,將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直接簡化為“中國邊疆學”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
一是將一般性的學科與中國的具體問題混為一談有先例。例如,通常當我們說“經濟學”,可能其中講的是中國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度的界限,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過去講的是蘇聯經濟問題,現在講的是中國經濟問題,這是中國學科構建中的普遍問題。
二是在世界范圍內,“邊疆學”本身沒有建立起來。中國現代科學是在西方的影響下誕生的,或者說中國各個現代學科基本上是從西方引進的,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在“西學”中,直到目前為止沒有“邊疆學”學科。1976年在美國成立的“邊疆研究協會”(AssosiationforBorderlandsStudies)是全世界最大的有關邊疆問題研究的學術組織,它使用的仍然是“BorderlandsStudies”,即一個問題集研究,說明“邊疆學”并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體系。這兩方面都有可能給中國學者帶來影響,這種影響將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直接簡化為“中國邊疆學”。
筆者認為,中國完全有條件創設自己的“邊疆學”,但關鍵問題是,創設新的學科需要相應的知識儲備和其他學科的支持。對中國學界不利的是,西方世界創立的民族國家給現代邊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基礎性架構,或者說,邊疆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西方思想占了上風,中國只是學習西方。例如,使用“中華民族”去構建中國的民族國家[8],而中國邊疆問題及其解決思維也基本上源自這一概念。
同時,在其他學科方面,中國整體上相對落后,無論就理論體系還是研究方法,中國基本上處于學習和應用階段。這兩點決定了中國暫時無法在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上有大的作為,但能夠做的事情是將已有概念、理論體系進行集成化開發,并在此基礎上創設“邊疆學”。縱觀構建“邊疆學”的歷史與現實,筆者發現,在中國倡導構建“邊疆學”的學者從開始就將其與中國的邊疆問題聯系。中國的邊疆問題又與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以及相應的中國疆域的形成演化等問題密切相關。
因此,當這些學者將這些問題說清楚或力圖說清楚的時候,構建所謂“中國邊疆學”的任務就旁落了。不少學者抱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所倡導構建的“中國邊疆學”是一個“爛尾工程”,更說明繼續沿著構建“中國邊疆學”的路線前進,可能是一個方向性錯誤。
(二)一般意義的“邊疆學”與“中國邊疆政治學”
如前所述,在沒有“邊疆學”總論的條件下,出現了“中國邊疆政治學”。2005年,吳楚克教授出版了《中國邊疆政治學》;2015年,周平教授帶領的團隊出版了《中國邊疆政治學》。這些鴻富巨著的出版,是對邊疆學研究前輩們“構筑中國邊疆學”期盼的絕好回應①。應該講,這兩位教授懷揣家國情懷,秉持學術使命,探究“邊疆治理”,著眼于中國邊疆政治的整體把握,對中國邊疆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構建了“中國邊疆政治學”的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周平教授寫道:“構建完整的邊疆政治學知識體系的條件也已經具備。
一方面,長期的邊疆政治研究,已經形成了關于邊疆政治的較為豐富的知識,為邊疆政治學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相關學科如政治學、邊疆史地研究、民族政治學等的快速發展,能夠為邊疆政治學的建構提供必要的支撐。”[9](20)
應當指出的是,周平教授要構建的是“中國邊疆政治學”,他寫道,“今日中國,之所以要構建邊疆政治學,一方面是由于現實的需要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則是已經有了構建邊疆政治知識體系的條件”,“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各種邊疆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前從來未達到這樣的程度。而目前之所以對邊疆政治的知識體系形成如此的緊迫的需要,是由于邊疆在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中的意義前所未有的突出”[9](19)。
(三)一般意義的“邊疆學”與其下屬學科
現就“邊疆學”及其下屬學科的關系進行討論。筆者認為,若沒有一般“邊疆學”對研究邊疆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以及其他具體問題的宏觀指導,那么被認為是“邊疆學”下屬的“經濟邊疆學”“邊疆政治學”“邊疆社會學”②等學科就無法萌芽,甚至在邊疆學下屬學科中一個廣泛認可的概念都沒有辦法形成。
一般而言,一個獨立的學科需要具備三個特征:一是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二是較為獨特的研究方法;三是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按照這三條標準判斷其獨立學科的性質,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建立起獨立的“邊疆學”之前建立“邊疆經濟學”“邊疆政治學”“邊疆社會學”等下屬學科是不可能的,因為后者沒有接受來自前者的指導,最多是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范圍內研究邊疆問題③。有的專家指出,沒有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就難以避免“學科殖民”問題,或者說,“邊疆政治學”是“學科殖民”的產物[7](67)。
總之,構建“邊疆學”面臨的上述兩大沖突將中國學界一直以來的努力置于尷尬境地,走出這一困境,最為重要的是尋找“邊疆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問題。如果不從一般意義上構建“邊疆學”,而直接構建“中國邊疆學”及其下屬學科,可能走上一條歧途。誠然,“中國邊疆學”天然與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糾纏在一起,給建立“中國邊疆學”帶來了不少麻煩,出現了“跨學科悖論”或者“學科殖民”現象。“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事實上已經成了一項“爛尾工程”,處于困境之中,因此需要構建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
“邊疆學”的價值取向應當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闡釋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形成一個對邊疆的一般性認識,推動人類知識的發展;其二是在此基礎上應用已經形成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為國家利益服務。從邊疆現象中揭示邊疆規律是“邊疆學”的基本任務,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邊疆學”作為一般性知識體系的價值追求。為達到構建“邊疆學”一般性知識體系的目的,走出“邊疆學”構建的困境,需要找到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的邏輯起點。
由于一般意義上的“邊疆學”需要建立固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參照系,所以,描述邊疆需要以邊界線作為參照系,由此“邊界”成為“邊疆學”的核心概念。“邊疆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應當是民族國家,或者將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既定前提,研究在成形的民族國家中的邊疆現象及其邊疆規律。“邊疆學”研究的角度應當以民族國家的邊界為邊疆的理想類型,主要是在對邊界的類型、形態、狀態進行分類的基礎上,對圍繞邊疆出現的沖突、交流等進行分析,特別是要形成關于邊疆爭端問題的規律與解決方式的一般性的理論解釋。
參考文獻:
[1]孫勇,王春煥,朱金春,等.邊疆學學科構建的困境及其指向[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2]張世明,等.空間、法律與學術話語:西方邊疆理論經典文獻[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3]邢玉林.中國邊疆學及其研究的若干問題[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1).
[4]馬大正.關于中國邊疆學構筑的幾個問題[J].東北史地,2011(6).
[5]方鐵.試論中國邊疆學的研究方法[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5).
[6]吳楚克,趙澤琳.中國邊疆學理論創新與發展報告[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
[7]朱金春.學科“殖民”與中國邊疆學的構建[A].華西邊疆評論(第三輯)[C].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
相關期刊推薦:中國邊疆史研究創刊于1991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邊疆研究領域的唯一一個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