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聯合體”:試論薩特《禁閉》中的精神生態
時間:2020年04月23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
摘要:“自由”的概念,一直貫穿于薩特的文學創作中,同時又有著極其深刻的哲思與廣闊的意義空間,進而薩特以獨特的文字構成一種社會性的自我闡釋。首先,我們以薩特戲劇中的精神意象為主題,探索薩特戲劇語言背后的文化內涵,突破形式的結構空間。其次,我們通過薩特戲劇內在的空間話語,尋找現象世界到意象世界的路徑,從而使世界清晰起來。最后,我們從薩特的書寫空間里,窺見自我和社會的精神生態,從而將薩特戲劇的空間程序表現為關于本質、關系、精神的研究,進而構建具有審美內涵的“自由聯合體”。
關鍵詞:自由聯合體;荒誕;精神生態;薩特;禁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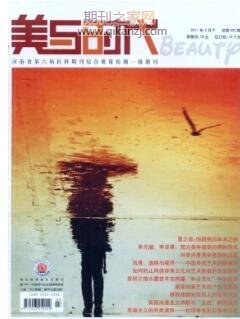
“人是自由的”這一哲學命題是薩特存在主義的本質。像他在《不惑之年》中對瑪塞爾懷孕的描述一樣:“在瑪賽爾的肚子里,那個小水泡正在膨脹,此時此刻它正在黑暗中努力,拼命要擺脫粘連,要從黑暗里脫身。在那渾渾噩噩的黏液后面,隱藏著一個小小的貪婪意識。相對于那團黑暗的黏液,意識就像一小點閃爍跳躍的光芒,兜著圈飛舞,最終變成一塊會思想的肉團”[1]。可知薩特認為人一開始就是會思想的肉團,借助意識的光芒才能從黑暗中掙脫,讓意識成為存在的先導。
一、語言碎片:自在存在的方式
自在的存在是一種不依靠他者視域的介入,是自我意識之外的存在。不管處于何種境地,這樣的存在都是處于混沌、沉寂的迷離狀態之中,并處在顯示不出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黑暗邊緣。就像《禁閉》中的三個鬼魂,同處黑暗的密室,重復著西西弗斯式的行動,他們失去了自我意識的先導,最后淪陷于虛無的困境之中。
要想清楚地了解薩特存在主義的自由維度,應該對其哲學的生成路徑做一個整體概觀。薩特的戲劇、小說都帶有濃郁的哲學意味。正是由于他強烈的哲學情思,使他的作品形成了獨特的哲學文本和觀念書寫,可見他哲學思想的深刻。早期他主要受胡塞爾的現象學影響,進入存在主義思潮后,主要受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以及黑格爾等人的理論滋養。于是在二戰期間,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形成了體系。而對于理性和自我的分析則受到笛卡爾的影響。進入20世紀中葉,他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形成了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晚期的存在哲學,則主要提倡存在的精神分析論。
克爾凱郭爾可謂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而薩特對于個體的研究主要以近代的理性主義為基礎,主要是以黑格爾和笛卡爾為主。薩特主要繼承了克爾凱郭爾的“存在先于本質”思想,在歷史中關注主體的生存境遇問題。與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相比,薩特主要運用“我”的意識去觸摸事物本身,將胡塞爾的純粹意識和克爾凱郭爾的存在體驗相結合。其實是一種具體經驗和具體世界的介入,使薩特能巧妙地避開單向意識或者具體問題的陷阱,從而走向個體意識的存在。
在海德格爾那里,薩特的存在主義主要是強調“自由”觀念。“只要此在作為其所是的東西而存在,它就是處于在拋擲狀態中而且卷入常人的非本真狀態的漩渦中。實際性是在被拋境況中從現象上見出的,而被拋境況屬于為存在本身存在的此在”[2]。存在是人自我的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人的存在是先于世界的。當人有了存在的空間,如何生存就是人自我選擇的結果,于是引出了自由的選擇作為人存在的行動。否則就像《禁閉》中的三個鬼魂,以一種無意義的選擇去確認自身的行為,這是毫無價值的。
這就是薩特所說的存在先于本質與自由選擇的意識行為。這表明了“近代歐洲哲學研究對象的重要轉向,一是從對本質(理性)的研究轉為對生存(個體)的研究;二是從對物(客體)的研究轉為對人(主體)的研究”[3]。按照這樣的轉向,我們可以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一對于主體哲學的論述來對照轉向問題。
我們知道笛卡爾對于主體(自我)的思考主要以理性本身為基礎,并沒有落實到身體(主體)本身。不管是尼采對身體的關注,還是福柯對身體的闡釋,都是從權力欲望對于身體的壓制和對立的角度出發的。他們都沒有從本質上把身體本身還原到主體的位置。以至于到梅洛龐蒂的對“我的身體”而非“我是身體”的建構,將身體還原到完整的結構當中,用知覺使身體在世界的建構過程中出場。因為人與世界的關系,小前提應該是一種身體與世界的關系。“身體是我存在的方式:我帶著我的身體置身于物體之中,物體與作為具體化主體的我共存”[4],以身體去探索世界和自我靈魂的價值。
因此,基于存在的思考,是獲得身份認可的根本。這也說明薩特的《禁閉》可以作為美學救贖的價值研究。簡而言之,薩特存在哲學的建構,是對以往哲學思潮的繼承與發展,于是潛移默化地在存在主義的精神生態中埋下了一粒思辨的“種子”。我們通過對語言、身份、理性等重要哲學范疇的比較研究中發現,精神生態的存在邏輯已經貫徹到薩特的多部作品當中,以及存在主義的思想里面。因此,薩特所說的“自由”是存在主義的邏輯內的表現,所以我們發現薩特所說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解放,而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自由。
二、他者角色:自為存在的困境
“自為的存在”是經過意識的指示作用,已經介入他者的意向,因此需要在特定的時空之中才能明晰自由的審美價值。由于我們從“自在的存在”過渡到“自為的存在”,主要是人的意識發揮作用。當人有了意識,就是“會思想的肉團”,在此前提之下意識就是自由,所以人、意識本身就是自由的。如果失去自由的價值,那么世界就變得荒誕、虛無。如薩特所言:“我命定是自由的,這意味著,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們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限制。”或者說,“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來變成自由的人,人的存在和他的自由沒有區別”。于是薩特引入“自欺”意識,換言之,該意識是偽裝自我的行為。
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選擇都處于一種被他者的眼光所左右的狀態,或者阻礙著我們本來目標的境況,這是暴力式的干預。正是這一強制性的介入,使得我們的選擇失去了自由,變得妥協與猶豫不決。所以薩特在戲劇《間隔》中用“他人就是地獄!”來解釋人物的悲慘遭遇。因此薩特說:“人被迫自由”,這就明確了自為存在的困境。
可見薩特一生都在為自由正名,反抗他者(地獄)。《禁閉》其實是薩特探討人與人之間生存主題的哲理劇。它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戲劇文本,而是一種關于存在觀念的闡釋。《禁閉》主要講述了郵政局的小職員伊內絲、巴黎貴婦艾絲黛爾、報社編輯加爾散三個罪犯在地獄里進行自我身份拷問的故事。隱瞞、虛偽、戒備是他們在地獄密室的初見話語,加爾散努力證明自己是英雄的角色,實際上他是個在二戰中因臨陣脫逃被處死的膽小鬼,同時他也有沉溺酒色、折磨妻子的“興趣”;艾絲黛爾的行為是玷污貞潔的語言意義,并掩飾色情狂的身份和殺嬰罪責;伊內絲則是封閉自己同性戀的丑行。虛偽的行徑將他們自我本身封閉起來,也在相互拷問對方的眼光中見證虛無的存在。這就是一種自欺意識的行為,一種沒有選擇意義的行動。
伊內絲:您受過許多痛苦吧?
艾絲黛爾:沒有。我那時是迷迷糊糊的。
伊內絲:您生的是……?
艾絲黛爾:肺炎。(跟剛才的表情相同,似乎又看見了陽間)好了,這會兒喪事辦完了,他們紛紛散去。您好!您好!人們頻頻地在握手。我丈夫悲痛欲絕,他守在家里。(對伊內絲)您呢?
伊內絲:煤氣中毒死的。艾絲黛爾:您呢,先生?
加爾散:十二顆子彈穿進了皮肉。(艾絲黛爾愕然)對不起,我可不是一個十分體面的死人。[5]
黑暗的密室是地獄空間的幻象。光是黑暗所懼怕的元素。光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西方《圣經》中傳統生存價值的隱喻。薩特以戲劇舞臺的形式展現虛無的困境。為什么以黑暗的密室為戲劇的舞臺?黑暗本身把人指向一種沒有方向的空間,從而達到不可辨析的目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黑暗”的色調是將人引向了更深的虛無世界中。
“鏡子”可以說是劇中關鍵的“證物”。加爾散說:“這兒沒有鏡子”,以及“要是能照一下鏡子,我什么都舍得拿出來”;艾絲黛爾也說:“您要是讓我一個人呆著,至少得給我一面鏡子呀”。那么鏡子作為生存的符號所指示的意義是什么?我們知道鏡子作為現實生活的物件,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模樣,甚至看到現實生活中的鏡像,用這些來確認我們生存的空間是否真實。當艾絲黛爾說:“當我不照鏡子時,我摸自己也沒用,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還存在”。因為鏡子是作為他們存在的證物,就相當于我們的身份或者生物學意義上的DNA編碼。雖然這是一種虛無的書寫,但是對于自我身份的證實說明了這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三個鬼魂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回避自我的丑惡和地獄的痛苦與折磨,這也是一種想獲取自由的虛無表達。但是在整個劇作的生存環境中,他們的爭取和努力其實都是一種徒勞,以至于最終都走向失敗。其實這隱喻人與人的關系是無形的刑具,這是比現實刑具還要悲痛的折磨,一直忍受著地獄的烈火與烙鐵。因為他者的目光是無法避開的,只要是存在于世界的,無形中就會陷入被限制的生存當中。比如加爾散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懦夫,解脫的方式就是通過他人的目光來完成。
還有艾絲黛爾在沒有鏡子的情況下陷入了恐懼與不安,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還存在,以及作為色情狂的她只能在男人的肉欲那里證明自己的存在,于是加爾散就成為她解脫的工具。而伊內絲則有一種以自我的眼光審視或者監督支配他人的傾向,她一方面把艾絲黛爾視為玩弄的工具,以鏡子去還原她的面目;另一方面則無情地揭發加爾散的虛偽、猙獰的丑惡面貌,從而使他們兩個失去平靜,陷入更深的漩渦當中。可見他們都妥協于他者的眼光以獲得虛偽的存在,用“自欺”的意識去獲取自我的解放和自由。
“他人的目光”就像無形的刑具和烈火,拷問著他們,互相折磨到都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和自由。“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我們總是把“他者”簡單地看成客體,這樣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很武斷的批評,不能以暴力方式去剝奪“他者”所擁有的主體性,這樣也會把人的主體性片面地看成“物”。于是,“我努力把我從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來,反過來力圖控制他人,而他人也同時力圖控制我”。這樣敵對的關系也許是《禁閉》所要揭示的存在哲理。
三、精神生態:審美自由的時空重構
精神生態是一種健全的人格,其精神世界具備自由、自律、自在等重要特征,是一種完滿的生命表達。薩特從意識的先導本質出發,推導出存在的天然本質,是人與生俱來的審美定律。從“自在的存在”到“自為的存在”,都是基于薩特存在主義的框架,去反映意識是自由的辯證邏輯。雖然“自在”與“自為”的區別之一,在于意識是否介入,可是二者的自由性是處在分離的過程,這就導致了自由陷入審美的困境之中。沿著自欺意識的虛無邏輯,荒誕是鏡子語言所建構的世界,而“鏡子語言”則是虛無的窗口。劇本《禁閉》所呈現的時空觀,是語言敘述中全部物態生活的再現。從時間流中,建構存在的空間,無關話語的意義與敘事功能,全在于空間的承載能力。如保羅利科所言:“小說是時間的藝術”。劇本的三個罪犯用自欺意識偽裝自我在黑暗的地獄中無法解脫的行動。他們想爭取自由、砸碎地獄,可是卻始終無法攻破無門的地獄。
薩特用死人的行動,去喚醒人們走向虛無和扭曲事物本身的盲目狀態。這樣是作繭自縛、制造自我的現實地獄,無法尋找出口,也就圍困了自我,成為一具沒有靈魂的尸體。劇中密室地獄的門曾開過一次,加爾散是有機會出去的,可是他沒有走該走的門。他陷入了他者的眼光,試圖以伊內絲的審判來獲得解脫,于是失去了機會。加爾散說:“難道能以某一個行動來判斷人的一生嗎?”這就引出了精神的性格問題。只有人才能通過自由的選擇去決定自我的存在位置,即行動的意義是人所能支配的意識行為。加爾散沒有通過自由的選擇和勇敢的救贖去證明自己是英雄,而是把希望限制在他者的肯定當中去,這樣的“自欺”意識只會讓他無法擺脫地獄的痛苦和拷問。
“他人就是地獄”的語言,在《禁閉》中闡釋了人與人的存在與虛無的對立關系。當加爾散他們無法看清對方的關系是一種虛無,那么只能讓自己陷入虛偽的惡性循環當中,永遠無法獲取自由的選擇。機會的大門一旦打開,你就無法遵從自我,那一刻你所擁有的自由就是一種死亡。最終加爾散讀到了自己:“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沒有刑具與烈火的地獄,是虛無的地獄。而三個已死的靈魂如何在虛無的地獄尋找自我的存在呢?這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式的荒誕,死亡是沒有選擇的資格,也就是沒有自由的選擇。《禁閉》的地獄是虛無的,所指向的存在空間就是虛無的狀態。不管是從非線性,還是從靜止的時間流里去塑造自我的生存空間,都是一種徒勞。就像三個靈魂在進行著虛無的行動,走向失敗、永陷痛苦的地獄是必然的結果。因此我們通過分析《禁閉》,發現自由與選擇的重要性,人正是因為有了自由的選擇,才可以擺脫地獄的圍困。只有拋棄“自欺”意識,還原本真才是獲取解脫的途徑。薩特所指向的時空,是要求我們逃離鏡子語言所描述下的時空,從而使人們的精神走向平衡與自由,才使分離的時空實現美學式的完滿。
四、結語
通過對《禁閉》的分析可知,從語言上我們要逃離鏡子語言的迷離與虛無;從行動上,我們不應該介入“自欺”意識去偽裝自我的身份以及自我的日常表達;從精神上,我們應該以健全的審美意識去建構自我的審美時空,而不是將時間處于靜止狀態,也不是將空間敘事截斷,而應該將時空放置于可選擇的自由世界當中去,進行自律、自由的延展與整合。只有避免自欺意識,沖破審美的虛無困境,才能重構精神生態的自由世界,人才有在自由世界中獲得選擇的能力。
參考文獻:
[1]薩特.不惑之年[M].丁世中,譯,香港:中國文學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8:55.
[2]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207.
[3]今道友信,等著.存在主義美學[M].崔相錄,王生平,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9.
[4]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42.
[5]Jean-PaulSartre.NoExitandThreeOtherPlays[M].Publisher:RandomHouseUSAInc,1989:280.
教育論文投稿刊物:美與時代創刊于1986年,是由河南省美學學會鄭州大學美學研究所主辦的以“創意”為標識,以設計美學為特色的刊物。本刊設立:創意信息、觀察思考、理念探索、形象品牌、造型創意、服飾設計、環境藝術、建筑裝潢、設計教育等欄目,介紹國內外設計領域最新動態,探討前沿理論,發表研究成果,是設計院校師生、專家、學者和設計師交流的平臺,也是當代公民提高審美意識,實現高品質生活的助手。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