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相對貧困的精準測度與分解
時間:2021年12月28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摘要:緩解相對貧困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本文構建包含心理健康、環境質量等維度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借鑒A-F貧困框架體系,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引入機器學習中的隨機權神經網絡(NNRW)法,精準測度并分解中國城鄉間、區域間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廣度、深度和強度水平。研究結論表明:無論城鄉間還是區域間,隨著相對貧困維度的增加,多維相對貧困的廣度、深度和強度指數呈下降趨勢,表明發生極端多維相對貧困的居民逐漸遞減。同時,居民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呈西高東低態勢,全國居民多維相對貧困水平大致與中部地區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相當;農村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顯著高于城鎮居民,且農村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程度與西部地區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相當,而城鎮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大致與東部地區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相當。此外,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分解結果顯示,金融產品、生活環境、耐用品和人均純收入等因素是城鄉間、區域間居民發生相對貧困的致貧主因,但是致貧主因對貧困廣度、深度和強度的貢獻率有差別。研究結論為制定解決多維相對貧困長效機制提供了理論參考和政策依據。
關鍵詞:多維相對貧困;相對剝奪;隨機權神經網絡;環境質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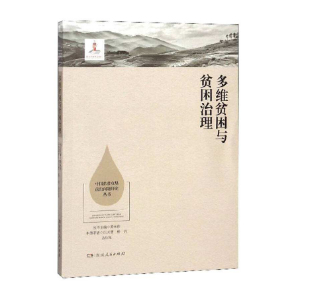
一、引言
2020年中國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性成就。進而,中國的貧困研究開啟了解決“相對貧困”的新征程。當前,區域間、城鄉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凸顯,同時,財富分配體系的不健全導致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階層固化趨勢有增無減,弱勢群體處境狀況堪憂,社會相對貧困問題日益突出,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穩定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使得相對貧困成為學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相較于絕對貧困,解決相對貧困的目標更高、對象范圍更廣、致貧因素更復雜、動態性更強。
隨著人們對貧困認知的深入發展,普遍認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還應該是教育、健康、住房等“可行能力”的不足(Sen,1976;車四方,2019)。換言之,從多維度衡量貧困更能描述和把握貧困的科學內涵。因此,相對貧困的研究也應該拓展到多維視角。目前,部分學者開始嘗試研究多維相對貧困問題(王小林、馮賀霞,2020;孫久文、張倩,2021;汪三貴、孫俊娜,2021)。
然而,大部分多維相對貧困的研究僅僅停留于定性層面,如葉興慶等人(2019)分析了中國的減貧歷程和緩解相對貧困的政策體系,邢成舉和李小云(2019)剖析了相對貧困與新時代貧困治理的機制,汪三貴和胡駿(2020)分析新中國反貧困70年的實踐后提出應該設計治理相對貧困的制度框架,左婷和蘇武錚(2020)從鄉村振興的視角提出治理相對貧困的戰略指向。但是,定量測度是了解和分析多維相對貧困程度并制定針對性減貧的關鍵。
于是,部分研究者也開始關注多維相對貧困的定量測度,而大多集中于多維相對貧困標準的探討(呂新博、趙偉,2019;張琦、沈揚揚,2020;萬廣華、胡曉珊,2021),并未形成專門測度多維相對貧困的方法,有研究者將流行于測度多維絕對貧困的A-F法①拓展到了多維相對貧困領域(王璇、王卓,2021)。不過,運用A-F測度多維相對貧困仍然存在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如(1)衡量多維相對貧困的指標體系如何構建,相對貧困標準如何劃定,目前尚無統一標準;(2)A-F法中對于各指標權重的選取多采用等權法,這種方法移植于多維相對貧困領域同樣不能區分各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這可能會導致測度多維相對貧困出現一定的偏差,因此,找到更為精確的權重法依然是值得探究的問題;(3)大多研究只關注多維相對貧困發生率和廣度水平,并未從不同層面探究城鄉間、區域間的多維相對貧困深度和強度水平。于是,本文嘗試構建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選取機器學習中的隨機權神經網絡(NeuralNetworkswithRandomWeights,NNRW)測算各指標權重,精準測度和分解中國城鄉間、區域間多維相對貧困。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
(1)構建了較為全面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包括居民收入、居民身體和心理健康、環境質量、工作質量、金融服務等維度,充分考察了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及城鄉間、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2)拓展了測度多維相對貧困的方法,引入NNRW法測算各指標權重,提高了多維相對貧困測度的精確性和科學性;(3)精準測度和分解了中國城鄉間、區域間多維相對貧困指數體系,多層次反映了多維相對貧困水平和致貧主因。
二、文獻綜述
相對貧困對應于相對剝奪,相對剝奪概念最早由Stoffer(1949)提出,而Runciman(1966)率先提出相對剝奪的操作性定義。學界對相對貧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相對貧困的內涵。隨著居民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水平的不斷提升,可能遭受到的機會缺失、能力或權利的相對排斥和相對剝奪成為相對貧困理論的基本內涵(Townsend,1979;Sen,1981)。學界尚未對相對貧困的內涵達成共識,且僅關注財富、收入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方面(李強,1996;陳宗勝等,2013;高強、孔祥智,2020)。同時,有研究者指出,相對貧困是由于收入水平差距帶來的教育、社會地位和生活質量等多維困境(邢成舉、李小云,2019),進而提出了多維相對貧困概念(王小林、馮賀霞,2020)。
第二,相對貧困的識別。學界也開始嘗試對相對貧困的標準進行界定,不過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大多采用收入比例法、收入中位數等方式識別相對貧困(Townsend,1962、1979;葉興慶、殷浩棟,2019;孫久文、夏添,2019;沈揚揚、李實,2020;李瑩等,2021)。
第三,相對貧困的測度。相對貧困的測度是衡量相對貧困程度的重要手段。Shlomo(1979)采用Gini系數解釋相對剝奪,開啟了相對貧困的測度研究。隨后,許多不平等指數(如Kakwani指數、泰爾指數等)也用于衡量相對剝奪(Berrebi&Silber,1985)。目前,對于相對貧困測算的研究還較少,李瑩等人(2021)采用模擬收入分布方法,測算了相對貧困規模;胡聯等人(2021)采用洛倫茲曲線法測算了中國2002-2018年的相對貧困水平。總體上,相對貧困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國內大部分研究均表明中國相對貧困呈上升趨勢(王祖祥等,2006;李永友、沈坤榮,2007;陳宗勝等,2013;Gustafsson&Ding,2020)。因此,精準識別和測度相對貧困,構建緩解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至關重要。
雖然中國的減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相對貧困尤其是多維相對貧困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其仍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如:(1)相對貧困的界定尚無統一標準。包括相對貧困的科學內涵界定和相對貧困線的劃定,已有研究大多僅關注財富、收入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方面,還應該關注從教育、醫療、生活水平等方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帶來的相對貧困。換言之,從多維度描述相對貧困更能把握其本質內涵。同時,隨著相對貧困的內涵的拓展,相對貧困線也應當重新劃定。(2)尚無成熟的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和測度方法。現有研究僅提出多維相對貧困的概念,且大多研究都是基于收入的單維視角展開,并未構建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框架和測度體系。雖然部分研究者將A-F法推廣到了多維相對貧困領域,但是并未關注A-F本身的缺陷,如等權重法帶來的測算結果偏差,也未深層次探究多維相對貧困的深度和強度水平。
(3)現有研究鮮少涉及城鄉間多維相對貧困的測算和分解,多是從農村視角探究多維相對貧困,事實上,城市的相對貧困日益凸顯,因此,城鄉間的多維相對貧困亦應該得到同等關注。因此,本文旨在構建中國居民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選取更為精確和合理的權重法,精準測度和分解城鄉間、區域間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廣度、深度和強度。
三、多維相對貧困的測度方法
相對貧困的識別和測度是了解相對貧困程度的重要手段。目前,學界還未形成識別和測度多維相對貧困的特有方法。本研究借鑒A-F多維貧困理論框架,構建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和測度體系,包括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方法和測度指數。
(一)識別多維相對貧困識別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是精準測度多維相對貧困的重要前提。本文借鑒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雙界線法識別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所謂雙界線法,是指在識別多維相對貧困過程中設定兩個臨界值,第一個臨界值稱為指標臨界值(對衡量相對貧困的每個指標設定一個標準),第二個臨界值稱為剝奪得分臨界值(對所有指標的相對貧困得分進行加總)。
(二)測度多維相對貧困識別出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狀態后,要了解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程度,還應該構建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
(三)分解多維相對貧困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從整體上描述了居民的相對貧困程度,但是并未找到驅動居民多維相對貧困的致貧主因。
四、數據、指標與權重
(一)數據來源與說明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據我們所知,該數據庫目前采集了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2020年關于社區、個體、家庭層面的數據,主要為了反映我國社會、經濟、教育、健康等方面的變遷情況,但是2020年的數據尚未發布。本文主要運用2018年的CFPS數據對區域間、城鄉間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進行測度和分析。
另外,空氣質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環境統計公報。本文根據下述方法對不同年度樣本進行篩選:①去掉各年度家庭、兒童問卷樣本中空白、缺省、不知道、無法判斷、拒絕回答以及不適用的數據樣本;②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選取成人樣本,所以將同年度的家庭、成人和社區樣本運用stata15.0進行合并;③通過篩選和匹配,本研究得到2018年中每一年的44645個居民樣本觀測數據。其中農村兒童樣本26242個,城市樣本18403個;東部地區①共14141份有效數據,中部地區共13062份有效數據,西部地區共17442份有效數據。
第一,居民收入。國內外大多數研究均是從單一的收入維度衡量相對貧困。但是,相對貧困的判定標準在學界并未達成一致。目前,國際上流行的相對貧困標準可分為三類:一是世界銀行提出的社會貧困線,其能綜合反映極端的絕對貧困相對維度的收入(消費)水平,計算式為社會貧困線=
①采用的相對貧困標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歐盟將相對貧困標準定為等價可支配收入的60%,李瑩等(2021)建議采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0%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作為中國城鄉的相對貧困線,汪三貴等人(2021)建議可按照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分別確定城鎮與農村的相對收入貧困線;三是基于基本需求設定的貧困標準,該類方法在計算上屬于絕對貧困的范疇,但其臨界值為收入中位數的30%,具有相對貧困線的特性。本文基于國際上的通用做法并結合中國的實際,采用人均家庭純收入中位數的40%作為相對貧困標準。
第二,健康水平。健康不僅是實現自我發展的人力資本(車四方,2019),其內在價值也是人類發展的重要目標。事實上,健康不僅指身體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世界衛生組織在1946年將健康概述為“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體魄強健,而是生理和心理的健康,以及社會的福祉和完美狀態”(王曲、劉民權,2005)。
于是,本文將居民身體和心理健康水平納入相對貧困指標體系中。基于CFPS問卷,對于居民的生理健康,本文采用受訪居民的自評健康水平來衡量,文中將不健康賦值為1、健康狀況一般賦值為2、比較健康賦值為3、很健康賦值為4、非常健康賦值為5,本文認為若自評健康未達到很健康和非常健康則居民受到相對貧困剝奪。同時,文中采用CES-D抑郁量表(SDS)評價得分來衡量居民的心理健康程度,其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程度越差,本研究基于中國常模結果①制定心理健康的相對貧困標準,將SDS標準分的臨界值的70%作為居民心理健康的相對貧困標準。
第三,教育程度。教育是人力資本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居民內生發展動力的重要手段。從長期來看,教育貧困是不可逆的,如果一個兒童失去教育機會,很可能在未來失去創造高收入的機會。因此,本研究將教育納入了衡量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基于CFPS問卷,本研究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其受教育水平的指標,現階段中國依然是實行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要緩解城鄉間、群體間的差距,九年義務教育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本研究將教育相對貧困標準定為12年(將居民受教育年限大于12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即在現行的教育標準上提高3年。其中,設文盲=0,小學=6,初中=9,高中=12,大學專科=15,大學本科=16,碩士=19,博士=22。
第四,醫療水平。醫療保險是促進居民健康的重要措施。如果一個身患疾病的兒童得不到及時的醫療救助,他很可能終身喪失勞動能力(車四方,2019),從而陷入長期貧困。有研究指出,我國居民醫療存在“三高”,即患病率高、就診率高和醫療費用高等突出問題(曲順蘭等,2009)。因此,居民醫療保險是解決兒童的“看病貴、看病難”基本保障。基于此,本研究也將醫療保險也納入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
基于CFPS問卷,本文將居民是否有公費醫療保險作為衡量民醫療的剝奪情況。若居民擁有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工費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第五,生活標準。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人民對物質的追求不再僅僅停留于吃飽穿暖,更重要的是追求生活的滿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本研究主要依據CFPS問卷選取做飯用水、做飯燃料、住房條件、生活環境、耐用品和互聯網使用等指標來衡量居民的生活標準。其中,做飯用水包括六種,即江河湖水、雨水、窯水、井水、自來水、桶裝水/水/純凈水/過濾水,相對而言,本文認為達不到用純凈水做飯就算做飯用水相對貧困。
因此,文中將桶裝水/水/純凈水/過濾水賦值為1,其余做飯用水賦值為0;對于做飯燃料,也包含六種,即柴草、煤炭、罐裝煤氣/液化氣、天然氣/管道煤氣、電、太陽能/沼氣,本文認為柴草和煤炭兩種燃料不清潔,但是若要不被相對剝奪,本文認為應該用電或太陽能/沼氣做飯,因此,本文將做飯燃料為電或太陽能/沼氣做飯賦值為1,其余燃料賦值為0;住房條件主要用是否擁有完全產權的房產,在擁有完全產權房產的情況下是否有房屋出租,若有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對于耐用品,本研究主要考察居民家庭是否擁有小汽車,若有則賦值為1,若沒有則賦值為0;對于生活環境。
本研究主要考察居民常年的居住環境,因此用家里是否空氣凈化器作為代理變量,若有則賦值為1,若沒有則賦值為0;對于互聯網,現在已是網絡時代,互聯網的使用是居民的基本生活品,因此本文選取互聯網聊天頻率來很衡量居民是否受網絡剝奪,通常,一周使用互聯網聊天3~4次及以上的頻率屬于較好狀態,因此,本文將互聯網使用的相對貧困標準定為周使用互聯網聊天3~4次,若低于該頻率則稱為受相對貧困剝奪,否則就不是相對貧困。
第六,金融狀況。居民獲取基本的金融服務是解決貧困惡性循環和實現自我發展的重要途徑(車四方,2019)。但是,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往往缺乏有效的、及時的金融服務,大量研究指出我國農戶特別是貧困農戶受到嚴重的金融排斥(王修華等,2013)。近些年,經過脫貧攻堅的奮斗,居民獲取基本金融服務雖然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滿足農村居民的需求。本文依據獲得金融服務的難易程度、金融服務對農戶貧困改善的影響差異,并結合CFPS數據可得性,將居民是否擁有股票、基金等金融產品作為衡量其獲取金融服務的指標,若有則賦值為1,若沒有則賦值為0。
五、多維相對貧困測度結果與分析
全國、東中西部以及城鄉間中國居民的單維相對貧困發生率情況。從表3中可以發現,就全國而言,金融產品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最高,達96.41%;空氣質量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次之,為95.37%;生活環境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第三,為95.24;醫療保險和受教育年限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緊隨其后,分別為88.24%和86.69%;心理健康、生理健康、耐用品、PM2.5和互聯網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介于60%~80%之間;做飯燃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59.9%;人均純收入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53.47%;工作環境、工作時間、工作晉升和工作安全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大約40%左右;屏幕。做飯用水、工作狀態和住房標準的相對貧困發生率都低于25%。就東中西部而言,除了工作維度和PM2.5等指標外,其余指標相對貧困發生率西部最高,中部其次,東部最小。
具體地,西部地區居民的空氣質量、金融產品、生活環境、醫療保險和受教育年限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較高,均在90%以上,82.04%的西部居民處于心理健康相對貧困狀態,生理健康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70.28%,人均純收入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65.61%,耐用品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76.02%,互聯網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67.65%,做飯燃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55.09%,PM2.5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38.45%,工作時間、工作晉升和工作安全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大約36%,工作環境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31.21%,做飯用水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31.95%,住房標準和工作狀態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分別為23.63%和14.71%。
中部地區居民的空氣質量、金融產品、生活環境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均達95%以上,醫療保險、受教育年限以及PM2.5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高達80%以上,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分別為71.33%和72.21%,耐用品、互聯網和做飯燃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接近70%,作時間、工作晉升和工作安全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大約43%,工作環境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35.19%,做飯用水和工作狀態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分別為24.61%和21.56%,住房標準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為11.23%。東部地區居民的PM2.5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最高,達94%;生活環境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次之,為92.89%;金融產品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第三,為92.77%。就城鄉而言,農村大部分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高于城鎮。
但是,生理健康、環境質量和工作維度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是城鎮高于農村。具體地,農村居民的金融產品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最高,達98.61%,換言之,農村有98.61%的人金融產品指標受到相對剝奪;農村的生活環境、空氣質量、醫療保險和受教育年限等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均超過90%,耐用品和互聯網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分別為75.5%和70.22%,其余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均在70%以下,其中工作狀態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最低,僅為15.40%。城鎮居民的空氣質量指標相對貧困發生率最高(95.54%),生活環境和金融產品的相對貧困發生率也高達90%以上。城鎮居民相對貧困發生率位于70%至80%之間的指標有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受教育年限與PM2.5,其余指標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均不超過60%,其中城鎮居民住房標準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最低(14.51%)。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多維相對貧困的緩解已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研究的焦點。本研究構建了中國情境下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包括居民收入、健康水平、教育程度、醫療水平、生活標準、金融狀況、環境質量和工作質量等8個維度共19個指標。相較而言,本研究特別將環境質量和心理健康等指標納入了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然后引入機器學習中的隨機權神經網絡法(NNRW)選取各指標權重,借鑒A-F貧困指數框架體系,采用2018年CFPS微觀調查數據,對城鄉間、區域間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發生率、廣度、深度和強度水平進行了精準測度,并對多維相對貧困指數進行了分解。研究結果發現:
(1)總體上,不論是多維相對貧困廣度、深度還是強度,西部地區的相對貧困程度最高,中部次之,東部地區最小,全國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大致與中部地區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相當。(2)農村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顯著高于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程度大致和西部地區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一致,城鎮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大致與東部地區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水平相當。
(3)不管是全國,還是東中西部以及城鎮和農村,隨著臨界值k的增大,多維相對貧困發生率、多維相對貧困廣度、深度以及強度指數均逐漸減小,這意味著隨著相對貧困維度的增加,發生多維相對貧困的居民逐漸減少且發生極端多維相對貧困的居民較少。(4)分解結果顯示:無論是東中西部還是城鎮和農村,金融產品、生活環境、耐用品和人均純收入等因素是我國居民家庭多維相對貧困致貧主因。
具體而言,中國居民多維相對貧困廣度指數的分解情況顯示,金融產品指標的貢獻最大,達30%以上;生活環境指標的貢獻度次之,達25%左右;人均純收入指標的貢獻率第三,占8%左右。中國居民多維相對貧困深度指數的分解結果顯示,金融產品指標對居民多維相對貧困深度的貢獻最大,達35%以上;生活環境指標的貢獻度次之,達30%以上;耐用品指標的貢獻率第三,為7%左右。中國居民多維相對貧困強度指數的分解結果顯示,居民多維相對貧困強度的主要致貧因素也是金融產品、生活環境和耐用品等指標,這三個指標對多維相對貧困深度的貢獻接近80%。 上述研究結論為緩解多維相對貧困提供一定的政策啟示:
(1)構建國家層面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可以更加細化的分析和考慮各區域的實際情況,中國現階段相對貧困不僅集中于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國家確定的集中連片特困區,城市居民相對貧困問題也日漸突出。因此,在構建國家層面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時還應該著重考慮城鎮、農村以及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為測度各區域多維相對貧困水平奠定基礎。
(2)進一步強化居民多維相對貧困的精準測度。第一,探索更加精確合理的指標權重方法,引入機器學習中前沿的深度學習法,并測試該方法測度權重的穩健性和適用性。第二,構建國家層面的多維相對貧困大數據庫。大數據不僅是精準測度的前提,更是測試機器學習法的關鍵因素。然而,無論是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均無專門的多維相對貧困大數據庫。可以在原有農村“建檔立卡”以及CFPS微觀數據庫的基礎上擴展成國家層面的多維相對貧困大數據庫。(3)建立監測居民多維相對貧困水平的智能化系統。在精準測度居民多維相對貧困的基礎上,還應該建立監測預警智能系統,形成事前防范、事中管理以及事后應急處理的一體化治理體系。
(4)大力改善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獲取能力和水平。第一,加強居民的金融服務,加大普惠金融力度,可以創新金融產品,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金融基礎社會建設,增加居民獲取金融服務的可及性,降低居民獲取金融產品的門檻。第二,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提高居民耐用品的消費能力。第三,繼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5)加強緩解多維相對貧困的頂層設計,加強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對接,調整相對貧困階段的治理策略并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收入分配機制。
參考文獻
[1]SENA.Poverty:AnOrdinalApproachtoMeasurement[J].Econometrica,1976,44(2):219-231.
[2]車四方,社會資本與農戶多維貧困:作用機制與影響效應[D].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3]王小林,馮賀霞.2020年后中國多維相對貧困標準:國際經驗與政策取向[J].中國農村經濟,2020(03):2-21
[4]孫久文,張倩.2020年后我國相對貧困標準:經驗實踐與理論構建[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2(5):166-178.
[5]汪三貴,孫俊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國的相對貧困標準,測量與瞄準——基于2018年中國住戶調查數據的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21(3):2-23.
[6]葉興慶,殷浩棟.從消除絕對貧困到緩解相對貧困:中國減貧歷程與2020年后的減貧戰略[J].改革,2019,310(12):5-15.
[7]邢成舉,李小云.相對貧困與新時代貧困治理機制的構建[J].改革,2019,310(12):16-25.
[8]汪三貴,胡駿.從生存到發展:新中國七十年反貧困的實踐[J].農業經濟問題,2020(2):4-14.
作者:車四方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