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八百米深處》《大斷裂》的人文關(guān)懷
時間:2021年10月08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shù):
【摘 要】地震文學(xué)是對地震災(zāi)難發(fā)生時人、事、物、情的記錄與延伸。 本文通過對《大斷裂》《八百米深處》兩部地震文學(xué)作品中小人物形象的研究,從人物價值的發(fā)掘、災(zāi)難文學(xué)的療救和災(zāi)難文學(xué)主題的拓展這三部分層層深入,展開論述,以探尋小人物的魅力,探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災(zāi)后精神重建中的人文關(guān)照,進(jìn)而思考災(zāi)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深刻意義。
災(zāi)難不只是斷壁殘?jiān)膽K象,因此災(zāi)難文學(xué)在還原之際更重要的是意義的拓展。 在細(xì)致的描寫中不僅見證災(zāi)難的慘劇,更是對人道、對生命的價值的見證,從而能夠喚醒更多的人,給予他們生存的力量和前進(jìn)的意義,讓他們看到人性、社會與未來,借文學(xué)產(chǎn)生反思,展現(xiàn)災(zāi)難文學(xué)的魅力與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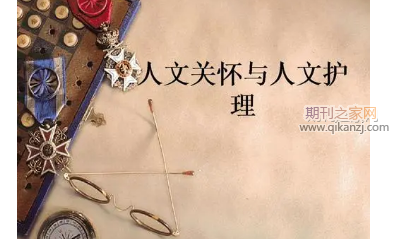
一、描摹小人物,體現(xiàn)人文價值
在一部文學(xué)作品中,作家筆下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有其存在的意義,他們或許不凡、或許平庸,但都必不可少。 正如社會中更多的是普通的小人物而不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災(zāi)難文學(xué)中小人物的刻畫與烘托更能顯現(xiàn)出所要傳達(dá)的人文價值。
文學(xué)教育論文: 人文關(guān)懷與心理健康促進(jìn)研究
(一)書寫群體命運(yùn)
“災(zāi)難文學(xué)將個體沉浸到群體命運(yùn)和國家存亡的激流與旋渦中去感知和表達(dá),由此集體情緒得以強(qiáng)化,對民族與國家的關(guān)切和愛得以放大,這是在當(dāng)代中國災(zāi)難文學(xué)爆發(fā)的特殊背景下體現(xiàn)出來的文學(xué)人類學(xué)特征。 ”[1]
因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無論是《八百米深處》中被困井下的張昆等人,還是《大斷裂》中明城廢墟中的“三劍客”等人,都被聚集在一起。 災(zāi)難將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他們會有面對食物時的爭奪,會有因個人情感而不愿施以援手的私心,會有面對災(zāi)難的手足無措和不作為等,但他們不是一個人,僅為私欲只會自取滅亡。 他們都擁有鮮活的生命,擁有生的權(quán)利,彼此平等。 于是他們都拋卻過往,用平等的角度關(guān)照著彼此的生命。 從為了彼此生命而團(tuán)結(jié)抗?fàn)幍倪@一刻起,他們的心真正地在一起,成為了一個共同體。 生命、人性、平等三者的統(tǒng)一,構(gòu)成了災(zāi)難中難得的美好。
災(zāi)難使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善良與丑惡的激烈沖突高度聚焦,人心的復(fù)雜和命運(yùn)的不幸被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與此同時,在這種關(guān)乎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也散發(fā)出了生生不滅的人性光輝,體現(xiàn)出了萬眾一心的氣勢,從而迸發(fā)出共渡難關(guān)、眾志成城的決心和毅力。
(二)展現(xiàn)生命偉大
地震摧毀了建筑和生存空間,但同時也建構(gòu)了一個全新的生命,拓展了生命的廣度與深度。 地震面前,每個人都微不足道而又無法逃避; 但地震過后,每個人也可以十分偉大,竭盡全力同時無所不能。 一如《大斷裂》中有被砸出腸子也要堅(jiān)持開到地點(diǎn)的老兵司機(jī); 有讓尸體開口的外科女軍醫(yī)楚欣; 有立功心切卻以身殉職的小兵耿樂……他們在生與死這個節(jié)點(diǎn)上沒有放棄、沒有退縮,活著就要活出意義,而若是死亡也要死得其所。 同樣在《八百米深處》中,四名礦工因地震深埋地底,相互支撐、相互援助,最終爬出礦井,譜寫了一曲蕩氣回腸的生命贊歌。
大地的深處是充滿危險的,沒有人知道地電、斷層會在何時來臨,災(zāi)難面前,每個人都是在與災(zāi)難抗?fàn)幍靡猿晒Φ倪^程中微小卻重要的一部分,無法分離,難以割裂。 人的價值在于對自己生命的負(fù)責(zé),在于對他人生命的尊重,在于對集體的貢獻(xiàn),在于人文關(guān)懷的無私顯現(xiàn)。 而地震將苦難與人文關(guān)懷血肉般聯(lián)系在一起,使令人苦痛的災(zāi)難中閃爍著人的價值的熠熠光輝。
二、借助小人物,展開文學(xué)療救
災(zāi)難是一個永恒且無法避免的話題,災(zāi)難中會涌現(xiàn)英雄,但災(zāi)難中更多的是一個個平凡的生命竭盡全力地求生。 救災(zāi)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治療,更是精神上的救贖,作家通過一系列的塑造去引起共鳴,從而傳達(dá)其作品獨(dú)特的作用——文學(xué)療救。
(一)鼓舞生存斗志
文學(xué)并不僅僅是一種欣賞,更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 當(dāng)天災(zāi)來臨時,人類難以逃避也無法預(yù)知死亡,《大斷裂》中提前在百里白沙灘深埋十八個小時體驗(yàn)震災(zāi)的男子不知道自己會在地震時三根肋骨折斷入心臟,但即使他胸口如洞也要跌跌撞撞跑去求救。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八百米深處》中被困地層深處的幾名礦工,在老工長張昆的鼓勵下,懷著對生的渴望爬出了礦洞。 恰恰是在這種廢墟、礦洞中,人類生存的本能和頑強(qiáng)的生命力才得以被激發(fā)出來。
災(zāi)難文學(xué)通過對每個人在生死存亡面前最真實(shí)、細(xì)致的描寫來告訴讀者:災(zāi)難來臨時,盡管人類的肉體是不堪一擊的,但人類的生存斗志是不滅的。 從而給處于全球疫情中的人以感觸,喚起內(nèi)心深處的珍惜與悲憐,在人性中的善和生存的權(quán)利中燃起生的欲望,找到生命的價值。
(二)實(shí)現(xiàn)自我救贖
災(zāi)難文學(xué)很大程度上給人帶來的就是一種救贖,“地震文學(xué)的呈現(xiàn)不僅是作品中小人物本身的自我救贖,也是作者的自我救贖。 ”[2]災(zāi)難讓死者永遠(yuǎn)定格在了昨天,而生者將帶著所有的悲痛繼續(xù)前行。 這種救贖讓人擺脫災(zāi)難后的痛苦,重新鼓起勇氣去生活。
劉宏偉借文學(xué)之筆,在現(xiàn)實(shí)的本真與藝術(shù)的虛構(gòu)中將自己的情緒灌注其中,用科學(xué)的知識架構(gòu)起一座虛構(gòu)的明城去銘記自己的軍旅生活,去感懷父輩的心血。 《八百米深處》的作者孫少山,在他下井挖煤謀生的間隙,以走出艱難為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物質(zhì)生活的艱難、政治上的人格歧視、社會環(huán)境里的人情冷漠淡薄,就迫使孫少山退守到主觀的精神世界里去求索。 ”[3]用那段銘心刻骨的苦難生活去構(gòu)建一個個礦井之下的小人物,用災(zāi)難中的種種轉(zhuǎn)變實(shí)現(xiàn)自我救贖。
作者之所以能寫出如此細(xì)致而生動的災(zāi)難文學(xué)作品,一方面來自其知識的積累,而另一方面也是來自其自身經(jīng)歷,寫作正是一種發(fā)泄和救贖,使他們從精神的廢墟中解脫出來。
三、深化小人物,拓展災(zāi)難主題
災(zāi)難文學(xué)不只有當(dāng)時性,更應(yīng)該有開拓性,“除了記錄當(dāng)下歷史和療救精神創(chuàng)傷外,它還勾連著對生存意義的哲學(xué)反思、群體身份的認(rèn)同等,災(zāi)難文學(xué)的書寫因此釋放出廣闊的意義空間。 ”[4]從災(zāi)難中的每一個主體聆聽來自命運(yùn)的聲音,看到人性的多面,看到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多重關(guān)系,見證歷史進(jìn)而引起未來之思。
(一)詮釋人物深度
文學(xué)也可以稱作是人學(xué),因而人物的書寫至關(guān)重要。 地震文學(xué)中的小人物不應(yīng)該僅是災(zāi)難親歷者的記錄冊或頌歌式的產(chǎn)物,而應(yīng)該是作為媒介去抒發(fā)人類在遭受災(zāi)難時的豐富情感、思想轉(zhuǎn)變,展現(xiàn)因深層創(chuàng)傷而凝聚起的巨大力量。
人性是不完美的,都具有多面性和復(fù)雜性,絕不僅僅只有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 因而無論是在《大斷裂》還是在《八百米深處》中,對于小人物的描寫都并沒有隱去他們的淺薄鄙陋,寫他們自私、短視,但在真正的危急時刻,又讓人們看到他們并非“愚民”。 身處困境中的他們,精神亦面臨著一場善與惡的拉鋸,而一番掙扎后,人性之善一步步地消磨曾經(jīng)的自私、仇恨,讓人在不斷的反思中慢慢感受到生命的價值。 這絕不僅僅是英雄主義或集體主義可以一概而論的,人性之所以復(fù)雜、人道主義之所以存在,便是為了人能夠從災(zāi)難、磨礪中走向成熟、走向超越。 人物的詮釋必然立足于人性、立足于人道,才能真正書寫出具有人本意識、具有普世意義的作品去引發(fā)更多的共鳴,啟迪更多的人。
(二)發(fā)掘社會積弊
災(zāi)難的存在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無論是地球的變化還是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都給自然帶來打擊,而最終這些不可逆的損傷都會一一回饋給人類。 因此對于災(zāi)難的書寫,并不只有人類的悲歡離合,還有對社會和自然的深思。
災(zāi)難像是一記警鐘,讓人在痛定思痛中學(xué)會反思,看到長久以來的社會積弊。 其實(shí)災(zāi)難并非沒有減少危險的可能性,只是無人做到罷了。 韓帆看到了明城建筑的弊病,但因資金問題只能看著建筑倒塌; 蘇紅蕾、邱老拼命地預(yù)知地震波段卻仍是晚了一步; 冷西軍面對張昆的提醒不以為意甚至惡語相向,最后張昆只能犧牲自己為同伴開路。 總有先行者會看到問題,但終是在一片不理解和不以為然中釀成大禍。 書寫災(zāi)難的文學(xué)作品并不少見,但對于災(zāi)難的反思和社會問題的深究才是災(zāi)難文學(xué)中罕見卻必需的。
(三)深化哲學(xué)思考
災(zāi)難文學(xué)是對災(zāi)難現(xiàn)場的真實(shí)再現(xiàn),它“記錄著從人類遠(yuǎn)古洪水泛濫的創(chuàng)痛到近代瘟疫肆虐的慘痛,再到現(xiàn)代地震、冰雪、洪水和海嘯的悲痛”[5]。 但災(zāi)難文學(xué)絕不是對自然災(zāi)難的簡單描述,而是以感性的生命存在為前提,進(jìn)而升華生命意義、反思生命價值的文學(xué)。
存在主義哲學(xué)認(rèn)為存在先于本質(zhì),而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人有權(quán)對人生和社會進(jìn)行自由選擇。 “中國人的‘在一起’感,則更是直接與團(tuán)結(jié)的傾向有關(guān)。 這種需求,使人不想‘掉隊(duì)’”[6],也使人不想團(tuán)隊(duì)中的任何一個人“掉隊(duì)”。 面對災(zāi)難,面對死亡,他們盡管恐懼過、迷茫過,但最終還是一致向往生的希望。
災(zāi)難突至給人造成的苦痛與恐懼,不僅是人物命運(yùn)的悲慘遭遇的重現(xiàn),更是人類生命延續(xù)性的生動體現(xiàn)。 正如蘇紅蕾的兒子繼承母志成為地震專家; 老工長生命不再,但其生存的斗志卻永不泯滅。 這種延續(xù)、這種生生不息讓災(zāi)難文學(xué)有了更多的意義。 “受到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寫作觀的影響,現(xiàn)有災(zāi)難寫作絕大多數(shù)都是‘傳達(dá)’性的,它將寫作視為一種工具論的符號學(xué)過程。 ”[7]因此對于災(zāi)難的書寫,當(dāng)“化悲痛為力量”,以災(zāi)難所造成的苦難記憶為基礎(chǔ),書寫生命的延續(xù)性,以昭示未來。
四、結(jié)語
災(zāi)難文學(xué),不僅僅是一份寫照,災(zāi)難文學(xué)中的小人物也不僅僅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塵埃。 災(zāi)難面前,人人平等,每一個人都值得尊重,也都有其存在的意義,無論是對于作家還是讀者,都在透過他們?nèi)ヒ娮C人性中的善與惡,借由他們的反思找到生命的價值,看到自己身處的社會的積弊,從而產(chǎn)生未來之思,明確生存的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嚴(yán)靜.當(dāng)代中國災(zāi)難文學(xué)的社會價值[J].大眾文藝,2014,(22):26-27.
[2]向?qū)氃?災(zāi)難文學(xué)的審美維度與美學(xué)意蘊(yùn)[J].社會科學(xué)研究,2011,(02):13-19.
[3]孫時彬.從地層深處走來——孫少山論[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8-24.
[4]孫曉迪.災(zāi)難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意義[J].創(chuàng)作評譚,2020,(04):41-44.
[5]范藻,范瀟兮.痛定思痛:災(zāi)難文學(xué)的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8.34-216.
[6]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04.
[7]支宇.災(zāi)難寫作的危機(jī)與災(zāi)難文學(xué)意義空間的拓展[J].中華文化論壇,2009,(01):58-64.
作者:牛蘇杰,趙 曉
- 水利旅游開發(fā)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結(jié)合探究—評《水利旅游概論》
- 從四川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園藝專業(yè)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探究地方農(nóng)業(yè)高校分段式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構(gòu)建
- 經(jīng)濟(jì)學(xué)一流本科專業(yè)建設(shè)問題探究
- 內(nèi)河水上貨物集裝箱運(yùn)輸監(jiān)管探究
- 丹噶爾皮繡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及成因探究
- 探究機(jī)械模具數(shù)控加工制造技術(shù)
- 課程思政融入植物學(xué)課堂教學(xué)的方法和途徑探究
- 增強(qiáng)大學(xué)生思想政治教育針對性與時效性的探究
- 信息化課程改革的探究與策略——以《康復(fù)心理學(xué)》課程改革為例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hù)SS
- 2025-01-22語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xué)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guān)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xué)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nèi)容?
- 2025-01-24醫(yī)學(xué)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xiàn)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