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制度功能與定位修正
時間:2019年09月05日 分類:政法論文 次數(shù):
[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包含對代表行為的理解與代表人選任模式兩個方面。對代表行為的理解,只能在“代理說”與代理規(guī)則體系中展開。以“代表說”與“代理說”體現(xiàn)出來的純粹民法學解釋選擇的區(qū)分不能引出實證法層面的不同價值判斷。經(jīng)登記公示并享有概括代理權的法定代表人在維護交易安全、提升交易效率方面具有明顯優(yōu)勢,是為其制度價值所在。
代表人的法定獨任制是我國經(jīng)濟體制轉軌時期的余音,其功能在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而非提升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當《公司法》外的治理因素淡出公司之后,法定獨任制已無存續(xù)價值,公司代表人應由“權責核心”回歸到“意思表示擔當者”的角色,我國宜改采以代表董事為默認規(guī)則、以共同代表為例外的代表人選任模式。
[關鍵詞]法定代表人;代表說;代理說;解釋選擇;制度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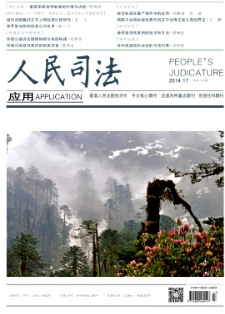
法定代表人概念的理解可以從“法定”與“代表”兩個方面展開。具體到公司領域,前者即公司代表人的選任規(guī)則,后者系立法者就“代表說”與“代理說”兩種有關公司及其代表人關系的不同理論解釋路徑的選擇。在我國,關于法人代表人尤其是公司代表人的討論經(jīng)久不衰。其原因不僅在于該問題包含著“代表說”與“代理說”兩種理論解釋路徑,而且還在于我國在實證法層面對代表行為效力認定與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上采取了有別于大陸法系傳統(tǒng)的立法體例。
既有的討論表明,對于“代表說”與“代理說”這一純粹民法學理論解釋路徑選擇的討論,在言說者秉持不同理論前見的前提下,純粹理論層面的解釋難以實現(xiàn)相互的理解與說服,基于代(表)理行為效力規(guī)則體系展開的實證法分析此時顯得尤為重要①。公司代表人的選任規(guī)則更多的是立法政策而非理論解釋問題,法定代表人制度更是其有力的注腳。
法定代表人制度誕生之初的社會環(huán)境扭曲了公司代表人在私法層面的定位。法定獨任制將大量的外部治理因素注入公司治理當中,這不僅引起立法者塑造代表行為規(guī)則的沖動,而且法定代表人在成為公司權責核心的同時也異化為“罕見的權力怪物”①。世易時移,當初法定代表人產生的社會環(huán)境已不復存在,法定獨任制已不具備延續(xù)的理由,公司代表人應回歸到其私法層面應有的定位之中。
一、法定代表人的緣起及其定位
法定代表人概念的成型在我國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早在民國時期,我國的法人代表人制度與傳統(tǒng)大陸法系國家相同,法人代表人尚未法定化、唯一化②,這一立法模式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也被沿襲下來③。不過,“一化三改”運動過后,我國將行政管理層面上的“一長制”延伸到企業(yè)管理中④。“一長制”的嵌入意味著企業(yè)的“首長”成為企業(yè)負責人,對內代表最高權威,對外代表企業(yè)并對企業(yè)經(jīng)營負最終責任。
不過,由于計劃經(jīng)濟時期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企業(yè)也不存在獨立的人格,因此企業(yè)負責人尚非私法意義中的代表人,但盡管如此,將企業(yè)權力與負責人綁定在一起的思路深刻地影響了法人代表人制度的立法活動。法定代表人的表述最早見于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其第44條Ⅱ規(guī)定:“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當事人,由這些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為法定代表人。”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貫徹執(zhí)行〈民事訴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對“法定代表人”的概念予以進一步解釋:“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的法定代表人,應是該單位的正職行政負責人,沒有正職行政負責人時,可以由副職行政負責人擔任法定代表人。”這種以行政負責人擔任法定代表人的思路直接貫穿到后續(xù)的立法活動中。
例如,《民法通則》第38條便將法定代表人定性為“行使職權的負責人”⑤,《全民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法》與《城鎮(zhèn)集體所有制企業(yè)條例》也明確規(guī)定廠長或經(jīng)理擔任法定代表人⑥。盡管1993年《公司法》第45條有關“董事長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規(guī)定在字面上不存在“負責人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內涵,但正如學者所言,雖然廠長、董事長、經(jīng)理并非從行政職權角度定義的,但因為公有制企業(yè)的廠長、經(jīng)理和董事長多數(shù)是通過“主管部門”予以任免,法定代表人的權力來源因此摻雜著明顯的行政授權色彩①。
與我國在公司代表人選任上體現(xiàn)出明顯的權責色彩不同,其他國家的公司代表人的選任規(guī)則更強調公司自治。例如,《德國股份公司法》盡管一方面將“共同代表制”作為默認規(guī)則,但其同時也認可公司采取其他代表模式②。日韓兩國同樣如此。比如,《日本公司法》第349條Ⅰ規(guī)定:“董事代表公司,但公司已指定代表董事或其他人代表公司的除外。”《韓國商法典》第389條規(guī)定:“公司應以董事會的決議選任代表公司的董事……在前款之情形下,可以指定由數(shù)名代表董事共同代表公司。”
這樣的差異揭示了我國與域外對公司代表人制度定位認識的不同。盡管域內外立法均視公司為私法主體,但結合我國《公司法》制定之初服務于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目的與國有企業(yè)為市場經(jīng)濟參與主體的現(xiàn)實,早前《公司法》語境中的公司并非完全私法意義上主體,其突出表現(xiàn)為國有企業(yè)在《公司法》的治理規(guī)則之外,同時存在著來自行政、黨紀監(jiān)督等外部因素的監(jiān)督。
正是基于這一深刻的社會背景,我國早期的公司治理現(xiàn)實不免延續(xù)了計劃經(jīng)濟時代下“一長制”的思維慣性,這使得法定代表人的選任必須遵循“誰負責、誰代表”的規(guī)則,法定代表人進而被改造為企業(yè)的“權力核心”③,其首先是公司的權力核心,其次才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者。
二、“代表說”的理論檢討與實證法檢驗
只要公司代表人存在,便有就代表人與法人關系作理論解釋的必要,對此,大陸法系向來存在著“代表說”與“代理說”兩種解釋路徑,究竟是“公司代理人”抑或“公司代表人”的理論解釋選擇更為可取,應當從理論自身與實證法的規(guī)則體系加以判斷。
(一)代表理論無法自圓其說
在法人代表人與法人關系的認定上,大陸法系素有“代表說”與“代理說”兩種觀點,前者系我國當前通說④⑤。兩種學說的核心差異在于法定代表人與法人是否為同一人格以及代表人行為是否直接由法人承擔。對此,“代表說”認為,“代表人為法人之機關,法人與代表人是同一個人格,雖名二而實一,不存在兩個主體”①,“代表人的行為就直接視為主體自身的行為,不需要發(fā)生法律效果的歸屬過程”②。
“代理說”則主張法人為法律擬制的主體,其本身沒有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代表人是法人的法定代理人,其行為后果不必然由法人承受③。僅從理論解釋路徑來看,“代表說”對代表人與公司關系的解釋路徑在維護公司與相對人的交易安全、提升交易效率層面顯然優(yōu)于“代理說”,然而這一解釋路徑本身存在諸多問題。
首先,在承認法人與代表人具有獨立人格的前提下,如何解釋代表人的人格被法人人格吸收而成為同一主體?退一步而言,即便“代表說”在理論上尋得相應的解釋路徑,其仍然存在一個悖論:如果代表人的行為就是法人行為,不存在效果歸屬的問題,則《合同法》第50條有關越權代表行為的效果歸屬問題應如何解釋?
在代表(理)領域中,如何解釋無權代表(理)行為效力是檢驗理論說服力的核心?依“代表說”有關代表人行為即為法人行為之觀點,《合同法》第50條應“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合同,該合同有效”而非“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這一矛盾恰恰揭示了“代表說”與“代理說”理論同質性的現(xiàn)實。
就《合同法》第50條而言,盡管該條試圖強調代表行為與代理行為在效力判斷規(guī)則適用上的不同,但這種區(qū)分卻又是建立在代理理論之上,即首先將代表人的人格與法人人格區(qū)分開,而后結合相對人的主觀善意判斷行為后果由法人還是法定代表人承受,這恰恰否認了代表行為的核心論點———代表人與法人同一人格。
在越權代表外,代表理論同樣要面對“自己代表”的問題。由于理論與實證法普遍不認可“自己代表行為”之效力,因此“代表說”仍需要回歸到“代理說”中去,至少要否定代表人從事“自己代表行為”時與法人同一人格。
綜上所述,在代表人行為超越其代表權限時,“代表說”同樣不認為越權代表行為效力當然地歸屬于公司,而是回歸到代理理論的路徑上,在法人與代表人人格區(qū)分的基礎上判斷效力歸屬。這意味著“代表說”不僅并不具有超越“代理說”的理論解釋力,而且在理論內核上與“代理說”一致。
其次,從理論層面上而言,“代表說”與“代理說”均系針對同一社會現(xiàn)象存在的兩種不同的理論解釋進路,作為對同一社會現(xiàn)象的理論解釋,兩種學說的差異僅僅是純粹民法學意義上解釋選擇問題,客觀對象不會因解釋選擇的不同而發(fā)生變化,何種解釋更為可取,除該理論自身邏輯是否自洽之外,尚需與實證法規(guī)則相兼容,脫離實踐而討論規(guī)則的理論解釋無法有效地回應實踐問題。
學理解釋是法律理論及其術語對現(xiàn)實世界的一種轉述,具有相當?shù)娜我庑耘c不確定性,由于解釋選擇與決定實證法規(guī)則的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并無直接關系,因此,與基于同一實證法規(guī)則存在不同理論解釋不同,以現(xiàn)實世界為規(guī)范對象的實證法不會因理論解釋路徑不同而針對同一民事法律事實異其規(guī)則適用。換言之,當對同一社會現(xiàn)象存在多種解釋時,實證法是先驗正確的,實證法決定了理論解釋的空間。
由于“代表說”在法人人格、代表人人格同一的主張上背離了實證法的區(qū)分兩者人格的體系基礎,因此“代表說”在解決越權代表行為問題時只能回歸到與實證法相契合的代理理論當中。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域外多通過立法或判例明確代理規(guī)則適用于代表人之上,拒絕將純粹的民法學理論解釋爭議延伸到立法與司法中①。
(二)《合同法》第50條與“代表說”關系之檢討
1.《合同法》第50條并非“代表說”的實證法基礎
盡管從理論上來說,“代表說”的理論構建無法脫離“代理說”,但在公司交易行為效力的判斷上,我國的立法的確存在以締約人是否有法定代表人身份為標準的效力判斷規(guī)則,其最為典型者莫過于《合同法》第49條與第50條②。同樣是對越權簽約行為,在簽約人并非法定代表人的情況下,依《合同法》第49條有關“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的規(guī)定,相對人若主張該行為有效,其“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③。
在簽約人為法定代表人之情形,根據(jù)《合同法》第50條有關“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的規(guī)定,司法實踐普遍認為,除非公司證明相對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權或因重大過失不知法定代表人越權,否則公司須承擔該行為后果,相對人不負有審查法定代表人權限的注意義務④。可見,較之于《合同法》第50條,第49條對相對人提出的注意義務更為嚴格。那么,這種區(qū)分是否構成了“代表說”的實證法基礎?
三、法定代表人的功能定位及其現(xiàn)實錯位
(一)法定代表人的特殊性及其制度功能
在“代理說”的語境下,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其他代理人本質上均是公司代理人,在“職務代理規(guī)則”創(chuàng)設后,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其他代理人之間的距離便被進一步拉近,隨之而來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即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其他代理人的差別究竟何在?在澄清兩者在理論層面上的區(qū)分后,差異只能來自于實證法層面上的制度設計,具體而言主要有三點。首先,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資格具有法定獨任性。
盡管我國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使其法定性特征得以緩和①,但立法者限定法定代表人選任范圍的立場卻并未改變②,公司仍然只能從限定的公司成員中選任一名代表人。與法定代表人不同的是,公司其他代理人不存在人數(shù)限制,其身份資格也不具有法定性,即便其職務具有法定性,但也并非是為了明確代理權歸屬而設定的。
其次,法定代表人享有概括代理權是其與公司其他代理人的核心差異。盡管“職務代理規(guī)則”在效力判斷模式上已與法定代表人趨同,但前者的適用仍被嚴格地限制在“職權范圍之內”,而法定代表人就公司事務享有概括代理權,除非章程或決議對其代表權予以限制。代理權限上的差異意味著,相對人當與法定代表人簽約時,無須再就其代表權限進行事前審查,交易后果直接由公司承受。
再次,法定代表人的登記公示不僅突出了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且也輔助于代理行為的效力評價。依《公司法》與相關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的規(guī)定,法定代表人不僅是公司的必要登記事項③,其唯有登記后方才能取得代表人資格④,而且,登記主管機關還必須將登記信息通過企業(yè)信用信息公示系統(tǒng)向社會公示⑤。對于法定代表人之外的代理人,行政法規(guī)僅將之列為備案事項⑥。因此,經(jīng)過登記背書的法定代表人經(jīng)由公示之后一躍成為權利外觀最為充分的公司代理人。結合我國區(qū)分公司締約人之身份而異其規(guī)則適用的現(xiàn)實,登記公示對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塑造作用又進一步強化了以身份區(qū)分規(guī)則適用的現(xiàn)實⑦。
四、公司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的重塑
眼下,外部治理因素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早已大為削弱,代表人的法定獨任制也失去其意義,公司代表人應由“權責核心”思維中的“權力核心+意思表示者”的身份向服務于提升交易安全、交易效率的制度目的回歸。我國公司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的修正①宜以任意代表制中的代表董事模式為默認規(guī)則,以共同代表制為例外。
首先,以代表董事為公司代表人選任的默認規(guī)則。在任意代表制中,大陸法系立法例中主要存在各董事均有公司代表權與代表董事有公司代表權這兩種模式,代表人的代表權均獨立行使。前者以《日本公司法》為代表。依該法第349條Ⅰ前句與Ⅱ之規(guī)定,各董事得各自獨立代表公司②。
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以代表董事為代表人選任的默認規(guī)則。《韓國商法典》第389條Ⅰ規(guī)定:“(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應以董事會的決議選任代表公司的董事……”就有限責任公司而言,該法第562條Ⅱ同樣規(guī)定:“有數(shù)名董事時,若章程另無規(guī)定,則應在社員大會上選任代表公司的董事。”筆者以為,各董事均有代表權模式雖更為靈活,但其也會激化代表權濫用問題,反而存在矯枉過正的風險③。
相較而言,在代表董事模式下,公司可以根據(jù)自身情況選擇一名或多名董事,如此便可規(guī)避代表權濫用問題④⑤。另外,代表董事的登記公示也符合我國的實踐共識。法定代表人制度的長期實踐使得公司代表人必須登記公示已成為實踐共識,相對應的是,由于代表董事模式下并非所有董事均具有公司代表權,因此代表董事也存在登記公示的必要⑥,這與我國商事實踐既有的觀念相契合。
其次,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應在反映公司共性的基礎上兼顧公司的客觀差異與不同訴求。從比較法的視角而言,諸如德國、日本、韓國與我國臺灣地區(qū)在公司代表人選任上皆采取了“原則+例外”的體例。例如,盡管德國公司法以共同代表制為原則,但《德國股份公司法》第78條Ⅲ同時規(guī)定“章程也可以規(guī)定,董事會的各個成員有權單獨或與一名經(jīng)理人一起代表公司”。再如,《日本公司法》第349條Ⅰ第一句雖然明確規(guī)定各董事均有代表公司之權利,但該款第二句則指出,當公司指定代表董事或其他人為公司代表人時不適用默認規(guī)則⑦,可見日本也允許其公司采納代表董事模式⑧。
韓國亦是如此,《韓國商法典》第389條與562條在明確公司應選任代表董事的同時,其第二、三款均規(guī)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或者股東會議決定采行“共同代表制”①。同樣地,我國臺灣地區(qū)“公司法”第108條規(guī)定:“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zhí)行業(yè)務并代表公司,最多置董事三人……董事有數(shù)人時,得以章程特定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可見,靈活、融合是大陸法系法域在公司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中的共同特征,此種靈活的立法體例可資借鑒。在我國,股權高度集中的現(xiàn)實傾向于公司代表權集中、高效地行使,實踐中不存在實施共同代表制的普遍訴求,其不宜作為代表人選任的默認規(guī)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共同代表制無適用空間。
股權高度集中并不等于“一股獨大”,在股東持股份額較為均等的情況下,不可概然否認該類股權高度集中的公司缺乏通過采納共同代表制以防范大股東濫用代表權損害公司利益的制度訴求。而且,一旦我國將代表董事作為公司代表人選任的默認規(guī)則,公司期望通過采納代表權共同行使規(guī)則以防止代表權濫用的需求也會隨之而來。為此,可以考慮將共同代表制度作為代表董事模式之例外的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原則+例外”的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雖然在尊重公司自治、兼顧實踐需求上更勝一籌,但增設代表人選任例外規(guī)則的同時也會增加第三人識別代表人及其權限的困難,對交易安全產生一定影響。由于第三人原則上并不負有查證公司是否以及采用何種例外規(guī)則的義務,因此第三人不應承擔由此產生的額外風險。譬如,若公司例外地適用共同代表制,則公司不得以相對人僅與其一名代表人簽訂合同為由,主張其不受該意思表示拘束,除非公司舉證證明相對人明知或應當知道公司適用何種例外的代表人選任規(guī)則②。
五、結語
法定代表人制度存在兩條主線:其一是對代表行為與代理行為的區(qū)分,其二是公司治理的外部因素。從理論層面而言,當代表行為與代理行為的區(qū)分仍停留在純粹的民法學解釋層面時,公司代表人制度仍舊可以在代理理論及其規(guī)則中展開。然而,當法定代表人在交易中的身份被不當?shù)赝怀龊螅緦儆诩兇饷穹▽W解釋選擇的問題隨之便轉化為價值判斷問題。
以公司“權責核心”身份誕生的法定代表人與早期公司治理存在大量外部治理因素的社會環(huán)境具有密切關系,法定代表人由此兼具“公私”雙重色彩,而這也使得其在私法交易中的作用被不當?shù)貜娬{。當外部治理因素退出公司之后,代表人的法定獨任制便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相應地,以權責定義的公司代表人便應當向以意思表示擔當者的方向回歸,法定代表人制度應在代理規(guī)則體系中①圍繞維護交易安全、提升交易效率的目的予以修正。
相關期刊推薦:《人民司法》系最高人民法院機關刊,載文闡述司法解釋,分析典型案例,反映審判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報道社會各界所關心的重大案件審理情況,研究解答司法實踐中的疑難問題。
SCI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yī)學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