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懸崖之上》看中國諜戰片的類型敘事
時間:2021年10月16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內容提要】電影《懸崖之上》是近年國產諜戰片的翹楚,它以嚴謹的敘事結構、精彩的人物設定、濃郁的家國情懷及出色的視聽語言,為主旋律電影的類型化樹立了新的標桿,也彌補了當下中國諜戰片創作的不足。 本文以《懸崖之上》為主要案例,進一步探析中國諜戰片的類型敘事,以期對今后中國諜戰片的創作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懸崖之上》; 諜戰片; 類型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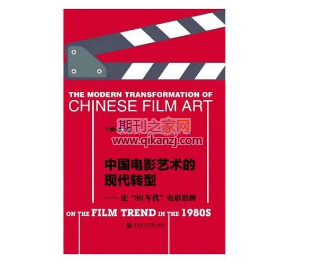
諜戰片是一個重要的商業電影類型。 它融合了懸疑、驚險、動作等元素,通常圍繞情報或隱秘任務展現敵我陣營的斗智斗勇與生死搏斗,“借助繁雜的敵我人物關系搭建起處處充滿伏筆與陷阱的暗戰世界,如同一個變化詭異的魔方,讓每一步驟的背后都蘊含多種可能性”[1],通過強戲劇性情節與極具刺激感的視聽效果,贏得大批觀眾的青睞。 在中國電影史上,諜戰片的發展一直比較曲折。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美國電影的影響下,諜戰片曾曇花一現,出現過一些頗受歡迎的作品,如《天字第一號》(1946)、《第五號情報員》(1948)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諜戰片演化為頗有本土特點的“反特片”,出現了《羊城暗哨》(1957)、《英雄虎膽》(1958)等眾多優秀作品。 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八九十年代,諜戰片偶有面世,但總體處于低潮,直至新世紀《十月圍城》(2009)、《風聲》(2009)的出現,諜戰片再次登上大銀幕。
但與風起云涌、高潮不斷的諜戰題材電視劇相比,中國諜戰電影的發展還是比較遲緩的,在《風聲》(2009)、《東風雨》(2010)等影片之后,又基本陷入停滯狀態,直至2021年《懸崖之上》的熱映一舉打破了這種沉寂的局面。 首次執導諜戰片類型的張藝謀,緊跟新主流大片的發展潮流,打造了新一代諜戰片的類型風格 —— 商業性與藝術性的高度有機融合,為中國諜戰片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文結合《懸崖之上》和其他同類作品,對中國諜戰片的敘事結構、人物塑造及影像敘事等問題進行分析,旨在把握中國諜戰片的類型敘事的特質,為后續同類型作品的創作提供經驗與啟示。
一、中國諜戰片的雙層敘事結構
新世紀的中國諜戰片繼承了“十七年”“反特片”的很多元素,同時也形成了新的類型特征。 在敘事上,它們基本遵循雙層敘事線索結構,使用“接受任務—組隊合作—完成任務”的線性結構,同時圍繞這個線性結構編織敵我人員身份甄別的第二條敘事線索。 《懸崖之上》便是如此,張憲臣、王郁等四名在蘇聯接受訓練的共產黨特工空降哈爾濱,執行代號為“烏特拉”的秘密行動。 盡管故事的主體內容是小組成員由于身份暴露而經歷種種困難和犧牲,“烏特拉”行動本身也僅僅作為一條暗線貫穿,但影片最終還是以行動小組順利完成任務作結。 所謂的“烏特拉”行動,是接應和護送從背蔭河實驗場逃脫的王子陽同志。 背蔭河實驗場即731部隊的實驗場之一,是日本法西斯進行人體實驗的秘密基地,也是日本法西斯迫害中國人民的鐵證。 有幸逃脫的王子陽同志是向國際法庭揭露日本人罪行的重要證人。 因此,《懸崖之上》的敘事主線關系到公理正義,關系到抗日戰爭和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反映的是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中的重要一頁。 其他經典諜戰片如《風聲》《東風雨》等皆是如此,特工們所要完成的任務基本都關系到革命的勝利、戰爭與和平的大局,而主要角色都是代表正義一方并最終完成任務[2]。
因此,盡管諜戰片的故事內容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但總體上一直遵循著接受并完成革命任務的敘事設置。 這樣的敘事設置給商業性較強的諜戰片賦予了豐厚的思想性,畢竟,“當諜戰與革命歷史結合為一體時,這樣的敘事便無可選擇地具有了革命正義的立場”[3]。 將中華民族的抗戰史、革命史植入諜戰片,這對增強觀眾的歷史認同感與民族凝聚力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商業類型與意識形態和主旋律結合的一個重要路徑。 因此,革命歷史成為諜戰片的敘事外殼,這成為了中國諜戰片的一個常見的敘事特征,也保證了此類型影片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緊密縫合。
身份甄別是中國諜戰片雙層敘事結構中的第二條線索。 如果說“十七年”的“反特片”是發動群眾尋找“潛伏”或“派遣”的特務,那么新時代的諜戰片則轉變為敵我雙方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內鬼”故事,這其中可以明顯看到以《無間道》(2002)為代表的香港電影的影響。 “抓內鬼”劇情包含著兩個層面,分別為我方特工如何潛入敵方內部、隱藏身份并順利完成任務,以及如何設法挖出潛藏在組織內部的敵方特務。 這種情節線索在諜戰片的敘事結構中,容易營造強烈的懸疑感和戲劇沖突,從而吸引觀眾的眼球。 《風聲》中的人物就基本處于一個密閉空間內,在固定人群中尋找“內鬼”,排查過程富有懸念感和壓迫感,形成了飽滿的戲劇張力。 在查找“內鬼”的過程中,抗日地下組織成員“老鬼”設法傳出計劃取消的信息,最終在另一位特工“老槍”的配合下,以死亡為代價將情報成功傳出。 同樣的,《秋喜》(2009)、《聽風者》(2012)等影片也都講述了情報人員與敵斡旋的故事,它們雖然在故事設置、人物發展脈絡上各有不同,但都基本遵循這樣的敘事結構。
《懸崖之上》在一開始便設定了謝子榮叛變的劇情,前半段主要講述在出現叛徒的情況下,張憲臣等人隱藏身份、逃脫敵人追捕的故事,明顯繼承了革命題材電影的傳統敘事特征。 后半段則出現反轉,將敘事引向尋找潛伏在警局內部的中共特工的情節,周乙開始成為敘事的新核心。 他試圖幫助張憲臣逃跑,又親自抓捕楚良,同時將密碼母本放在金志德的車中以引起警方對金志德的懷疑,從而洗清自己的嫌疑。 總之,特工周乙與敵人的心智較量成為影片后半段的主要情節內容,暗合了新世紀以來諜戰片常見的“抓內鬼”劇情設定。 此外,在影片開頭,張憲臣識破接頭人的特務身份,王郁通過火車洗手間內被改掉的暗號猜測接頭人是敵人,這些劇情都充實了影片中身份甄別的部分,提升了影片的刺激感與吸引力。
“抓內鬼”具有明顯的娛樂效果,其本身便包含著極強的懸念感,是諜戰片最大的看點。 關于懸念感,喬治·貝克認為,懸念就是興趣不斷地向前延伸和預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 而不管觀眾愿不愿意,他的興趣都非向前直沖不可[4]。 在中國諜戰片中,這種懸念感便表現為觀眾不斷地揣測究竟哪位人物為“內鬼”,對己方特工如何擺脫敵方懷疑產生期待,又因己方特工暴露身份而陷入危局感到緊張。 無論哪一種情況,都刺激觀眾的心理,為觀眾帶來猜謎般的快感。 “抓內鬼”便是依賴這種觀影心理為諜戰片增添了娛樂化的觀影效果。
關于諜戰片,學者胡克曾指出:“時代雖然變化,但是諜戰片的本質并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那就是政治性與娛樂性的完美結合,變化的是不同的政治性與不同的娛樂要求,需要更多地適應社會心理和主流觀眾的欣賞口味。 ”[5]的確,新世紀的中國諜戰片用嚴肅的革命歷史外殼,結合帶有娛樂性質的“抓內鬼”情節,以一種雙層敘事結構的形式,實現了思想性與商業性的緊密結合。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相比于“十七年”“反特片”,新世紀的諜戰影片努力擺脫臉譜化的人物設定,增加了人物身份甄別的復雜性,因此娛樂性更加突出,顯示出新主流電影對大眾文化的適應性,它們在弘揚主旋律的前提下,完成了大眾娛樂時代的諜戰片類型轉向。
二、歷史之維
中國諜戰片的革命歷史敘事決定了其自身的時間之維,即故事往往設定在以往帶有傷痛記憶的歷史時期,以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面臨內憂外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代表時期,并多以真實歷史事件為敘事背景。 借此革命歷史的維度,新世紀中國諜戰片實現了激發愛國情感、增強自身觀賞性的雙重功能,與西方主流的間諜片形成對比。 后者受冷戰思維的影響,大多數將故事設置在當下時間或至多回溯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西方間諜片也稱特工片,成熟于冷戰時期,多表現特工憑借非凡身手與高端諜報技術,獲取敵方秘密情報的故事。 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對潛在威脅的恐懼彌漫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兩大陣營相互視為敵人,在不見硝煙的環境中展開暗斗,這樣的冷戰思維側重于宣揚自身的價值觀,而貶低和丑化對方。 諜戰片是完成這一宣傳目的的極好武器。 即便是在后冷戰時期,由于“9·11”事件的持續影響,以及西方國家對自身國際地位的追求,冷戰思維仍舊陰魂不散。 在西方間諜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真實情報組織的身影,比如經典諜戰片“007”系列里主人公邦德所聽命的英國軍情六處、《變臉》(1997)中的聯邦調查局(FBI)、《諜影重重》系列里的中央情報局(CIA)等,通過描寫這些情報組織的特工與其他國家的特工或恐怖分子的博弈,這些諜戰片成為西方國家確認安全、削弱恐懼的有力工具。 同時,西方諜戰片也擅長展示高科技諜報手段,如《碟中諜》系列中的口香糖炸彈、監控眼鏡,《諜影重重》系列中的互聯網手段等,它們既成為影片的特殊景觀,使影片具有吸引力,同時也隱晦地展示出本國的科技實力,從中依舊可以看出冷戰思維的深遠影響。
相比之下,中國新世紀以來的諜戰片更偏重于歷史敘事,是在中國革命歷史的記憶中展開敘述的。 《東風雨》以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夕為背景,講述的是“孤島”時期多方勢力在上海的較量; 《風聲》的時間設定在1942年汪偽政府統治期間,展現了在日本法西斯與汪偽政府控制下危機四伏的中國社會; 《秋喜》的故事發生在1949年解放戰爭第三階段末期,勾勒了那一時期廣州的混亂景象; 《聽風者》的時間則設置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講述國共兩黨特工間的較量。 《懸崖之上》將故事設置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展現了抗日戰爭前期哈爾濱的歷史景觀。 當時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地區,建立“偽滿洲國”,并安排偽警來進行社會管控。 導演在電影中增添了背蔭河實驗場、逃脫的王子陽同志等真實歷史事件與人物,表現出偽滿政權控制期間東北地區的緊張局勢。 同時,在歷史設定下,電影又對大環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虛寫。 影片并沒有展現日本人或其他民眾,而是將故事重心放在革命黨人與哈爾濱特別警察廳特務科的較量上,使用更集中、緊湊的敘事手法,使觀眾感受到國家與民族曾遭遇的嚴峻挑戰,再次體驗到深沉的民族情感和對正義的信仰。
同時,受到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的影響,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已逐漸擺脫了簡單的宣教功能,以類型突破、類型雜糅等手法適應市場需求。 這使得新世紀以來的諜戰片注重歷史的奇觀化表現。 在《懸崖之上》中,導演將“偽滿”時期偽警到處鎮壓的景象與動作片的類型元素相結合,小巷圍捕、汽車追逐、激烈槍戰等橋段都具有很強的景觀性,既表現出偽警的殘忍、斗爭的殘酷,也滿足了觀眾的觀影快感,無疑對激發觀影興趣起到助推作用。 同樣,《風聲》中的大尺度刑罰鏡頭,在控訴日本法西斯殘暴行為的同時,也成為影片的宣傳熱點與市場賣點; 《東風雨》對“孤島”時期上海夜總會的影像呈現,其紙醉金迷的場景具有較強的觀賞性與娛樂性。 以上表明新世紀諜戰片在革命歷史敘事的基調下,都十分重視平衡思想性與商業性、人文性、娛樂性的表達,這也成為新時代諜戰片的共同追求。
另一方面,中國諜戰片對革命歷史的講述也各有特點。 《懸崖之上》與《風聲》都以“抗戰”為背景,日本法西斯與漢奸特務是影片中最大的敵人,但《懸崖之上》更多展現了共產黨特工為革命任務前仆后繼,勇于付出和犧牲,在表現與敵人明爭暗斗的曲折性上著墨不多。 《風聲》則將故事重心放置在身份甄別上,著重刻畫特工的各種潛伏手段、敵人的誘捕計劃等。 由于處理的手法不同,《懸崖之上》在“抓內鬼”的劇情層面上刺激性不足,而《風聲》則在思想的感召力上稍遜一籌。 但可以肯定的是,兩部作品都實現了歷史深度與商業追求的較好平衡,展現出新世紀諜戰片的新變化和新趨勢,在統一的革命歷史敘事基調下,實現了創作的多元化。
三、犧牲的集體英雄
新世紀的諜戰片繼承了“十七年”“反特片”塑造英雄人物的傳統,保留了英雄在組織、同伴的扶持幫助下順利完成任務的經典敘事結構。 同時,在塑造集體英雄時,更注重勾勒英雄的復雜人性,實現了英雄從“神性”到“人性”的回歸。
在《懸崖之上》中,主要的英雄人物是以張憲臣為代表的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四位特工,以及默默潛伏在哈爾濱特別警察廳特務科內部的特工周乙。 兩組人物一組在明,與敵人展開生死搏斗; 一組在暗,克服著潛伏所帶來的巨大精神壓力。 而最后“烏特拉”行動的成功則得益于兩組人馬的共同努力。 《風聲》也塑造了數位英雄,除足智多謀的顧曉夢外,吳志國豁出自己的血肉之軀設計了一出計中計,還有潛伏在雜工隊伍中借機向外傳遞消息的勞工。 《東風雨》描寫了誓死保護重要情報的不同國家及陣營的成員,這些都在昭示諜戰行動的成功絕非一人之力,而是需要不計其數的同志的共同努力。 這樣的人物形象設計符合中華民族重視集體智慧和集體合作的文化傳統。 這些影片通過表現個人之間的相互支持表現出集體的重要性。
在強調集體主義倫理的同時,新世紀諜戰片也克服了人物臉譜化的特點,塑造出更復雜、更鮮活的英雄人物,以滿足當下觀眾更高的觀賞水平和要求。 《風聲》中地下黨特工顧曉夢表面驕縱,實則心懷大義,同時她對為偽軍工作的李寧玉又懷有一種曖昧而隱晦的感情。 這種并非革命感情,而是明知有錯卻無法控制的私人情感,使顧曉夢這個人物形象更為復雜,也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說顧曉夢的運籌帷幄使她還略帶一絲“神性”的話,《懸崖之上》的英雄人物則完全實現了“人化”。 《懸崖之上》中楚良因見女友小蘭被警察帶走,情急之下向偽裝的特務說出了小蘭的身份; 小蘭也會在深夜擔心楚良的安危而倉皇流淚; 甚至是老練的張憲臣也會一次次失手,被敵人突然出現的車輛撞倒而被抓,想駕車主動犧牲卻未能如愿。 這些情節均使片中的英雄人物從無所不能變為擁有某些性格弱點的普通人。 正是這些弱點使他們成為時代洪流中個性鮮活的個體,不僅實現了對個體性的凸顯,也使影片散發出人性關懷與藝術氣息。
在刻畫了有個性的英雄集體的同時,新世紀中國諜戰片還講述了令人淚下的犧牲精神。 英雄集體在執行任務期間不得不面對成員的犧牲,最后以個體的犧牲換來集體的光明,這是中國諜戰片感動觀眾的一個重要敘事元素。 《懸崖之上》中的張憲臣被敵人毒打拷問卻寧死不屈,在被臥底周乙救出后,自知時日無多,甘愿以自身的犧牲讓周乙擺脫敵人的懷疑,以一人之死成全隊員,最后順利完成革命任務; 同樣犧牲的還有四人小組中的楚良,他主動暴露自己,幫助同伴王郁順利逃出,以生命的交換譜寫著理想的延續; 臥底周乙眼睜睜看著同志們一個個倒在自己腳下卻無法施以援手,忍受著幾乎與肉體折磨一樣殘酷的精神折辱,詮釋了另一種犧牲。 通過塑造犧牲的集體英雄形象,中國諜戰片在緊張刺激的類型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悲壯美的情感基調,完成了對觀眾的情緒感召,使觀眾對電影所傳達的革命理念產生認同,從而大大增強了影片的感染力。
設計受難、犧牲的英雄人物形象,也進一步拓展了諜戰片暴力美學的表現形式。 新世紀諜戰片融入了動作片、武俠片等類型電影的暴力美學,通過藝術化的表現形式緩和了暴力的恐怖,但它們依舊滿足了嗜血欲望,只是經過包裝,不再過于觸目驚心[6],這樣就在保證藝術性的基礎上增強了影片的商業性。 《懸崖之上》中血肉模糊的張憲臣被用電刑的場景,《風聲》中以藥水、針扎等各種刑罰道具對特工進行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聽風者》中張學寧身上連中五刀,均是通過對刑罰的奇觀化,以更具儀式感的方式,滿足觀眾對刺激感的需求以及獵奇的心理,使影片獲得商業性的特質。 另一方面,對酷刑的極致展現也使觀眾在震撼之余更能體會到英雄們為了革命獻身的堅強意志和大無畏精神,加深對英雄的敬仰之情。 可以說,通過犧牲的集體英雄人物形象,新世紀的諜戰片提升了影片的情感號召力與市場吸引力,為新時代主旋律題材的類型化轉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四、強化影像和情感的表達
除了雙層敘事結構和譜寫英雄集體的這些特征外,新世紀諜戰片更關注對影像與情感的精準表達。 這些影片在把握類型元素的基礎上,注重用詩意化手法,通過烘托氛圍感的鏡頭畫面和訴諸情感表達,營造出獨特的“血色浪漫”,實現諜戰片美學表現上的創新。
作為商業片,諜戰片慣常以驚險、刺激的場景挑動觀眾的視覺神經,這尤其體現在西方的諜戰片中,如《碟中諜》系列、《極限特工》系列等經常出現主人公用各種先進武器與敵廝殺的場面,甚至包括飛機大戰等各種挑戰人類身體極限的打斗場面。 中國諜戰片很少像西方諜戰片那樣表現高難度場景,雖然也存在大量搏斗、爆炸等驚險場面,存在暴力美學與奇觀化,但它們更重視對環境與氛圍的營造,在緊張敘事之外,通過對長鏡頭與空鏡的使用,以留白的手法,打造富于詩意或情感的影像,使自身在商業片的定位上,更多了一層藝術特質。
比如,《懸崖之上》開始用俯拍且不斷推進的雪景鏡頭,為影片營造出濃厚的北國風情。 隨著故事的逐步演進,哈爾濱的皚皚大雪反復出現在張藝謀的鏡頭之中,在張憲臣與小蘭講起自己同兩個孩子分離的往事時,鏡頭中是大雪紛飛的哈爾濱的深夜,雪花簌簌灑落,為英雄流露出的柔情增添了些許悲涼之美,也為這場正義之戰增添了詩意。 《東風雨》使用長鏡頭表達一種詩意追求,以移動長鏡頭逐步展現“孤島”時期上海街頭混亂的景象,鏡頭掠過外國士兵的臉,到大街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再逐漸上移至整個上海街頭的遠景,最后定格至烏云密布、陰雨連綿的上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感便隨著鏡頭流淌到觀眾的認知與情緒之中。 通過影像的詩意化呈現,中國諜戰片為這種商業電影賦予了獨特的美感,增強了藝術感染力,與觀眾形成了更強烈的情感互動。
同時,中國經典諜戰片還擅長以情感作為敘事的推動力。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現代諜戰片由于奉行的是通俗的大眾審美策略,因而在影片情緒基調的塑造上是多元的,尤其會使用與諜戰題材所慣常出現的影片風格差別極大的情緒基調策略[7]。 新世紀中國諜戰片發展出一套特有的敘事選擇,即以人物在亂局中的情感流動為重,而不是過分強調復雜的反轉設定,選擇以親情、愛情、友情等真摯情感叩擊觀眾的心弦,而非故意設定復雜迷局刺激觀眾大腦。 在《懸崖之上》中,當王郁知道丈夫張憲臣被抓且兇多吉少之時,迫于敵人的監視,只能借上廁所之名,在水龍頭的流水聲中坐地痛哭,這一情節準確傳達出她與張憲臣的伉儷情深,使觀眾對英雄背后所承受的犧牲更有認同感,也對王郁這樣有情有義、堅強隱忍的女性人物產生了深厚的敬意。 《秋喜》中特工晏海清與女傭秋喜之間復雜而隱晦的感情、《東風雨》中安明與不同陣營的女友之間的愛情故事,皆使得影片在肅殺的氛圍之外多了一份纏綿悱惻的溫情。 不難看出,新世紀諜戰片的情感處理豐富了人物形象,補充了影片的類型元素,使諜戰片更具有人文關懷的溫度,從而提升了自身的藝術氛圍。
而且,中國諜戰片中的情感描寫并非只為抒情,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劇情的發展。 在《懸崖之上》中,原本殺伐果決的張憲臣在逃脫大批敵人的追捕后,因疑似看到自己失散的兒子而下車,并向附近的修鞋匠詢問情況,也因此耽誤時機導致最終被捕,并牽扯出電影后續的敘事走向。 電影中張憲臣的父愛既打動了觀眾,又推動了敘事的發展。 深沉、質樸的父子親情使張憲臣的行為合理化,引發觀眾的認同之情,使他們在代入自身情感的基礎上,沉浸于電影的后續敘事之中。
可以說,中國諜戰片通過情景融合,最大化地實現了緊張刺激基調下的詩意書寫,在豐富類型元素、追求商業收益的同時,也不斷加強對藝術性的追求,傳達出這個民族的“血色浪漫”。
電影文學論文范例: 科幻電影中的體育元素功能與呈現
結 語
通過對《懸崖之上》及其他經典中國諜戰片的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紀中國諜戰片既表達了政治意識,又在此基礎上不斷加強自身的商業性,既看重市場收益,也不忘努力保持藝術性與思想性,在創新意識之下逐步前行。 這無疑啟示著后來者,只有不斷實現類型創新,保持多種元素的平衡發展,提升自身的市場敏感度與創作責任感,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下去。 對中國諜戰片的類型分析,并不局限于情節結構、時間設定、人物形象塑造和影像/情感的作用這幾個方面,隨著電影美學的嬗變及電影產業的發展,中國諜戰片的未來走向充滿著諸多未知性和可能性,需要我們不斷努力,進行更深一步的思考與探索。
注 釋
[1]徐健民.《風聲》:紅色諜戰影視作品的新標桿[J].電影文學, 2010(6):84-85.
[2]唯一與眾不同的是李安于2007年導演的《色戒》,片中王佳芝因情感沖動放過漢奸易先生,最終導致自身及團隊死亡的故事為諜戰類元素的電影增添了一抹復雜人性的色彩。 但因為其文藝片的定位,故不將其歸置進類型敘事之中進行探討。
[3]陸新.從類型雜糅走向敘事突圍——論當下革命諜戰劇的制作策略[J].南昌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6):135-139.
[4]〔美〕喬治·貝克.戲劇技巧[M].余上沅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207.
[5][6]胡克.新諜戰片的美學傾向與文化分析[J].電影藝術, 2010(1):64-68.
[7]崔丹.當代諜戰片的通俗美學敘事研究[J].社會科學家,2011(8):142-144.
馮俊敏: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學系碩士研究生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