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將軍幕府文學創作與文體成就探論
時間:2021年05月14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昭帝之后,漢代將軍幕府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轉變,具有了輔政治事的大權。為了個人的仕途與發展,士人入幕成風,積極進行文學創作。漢代幕府創作以應用文為主,具有現實時務性、應對性;開拓了邊疆外事與戰爭武功題材;打破了祝、頌等文體的傳統文風或模式,促進了說體文的創作;適應公府特別是幕府言說與書寫需要,奏記、箋等文體應運而生。因幕主與僚屬的關系比較特殊,奏記、箋等呈現出較獨特的文體特征與風格,在漢代文章史上具有一定價值。
關鍵詞:漢代;將軍幕府;文學創作;文體成就;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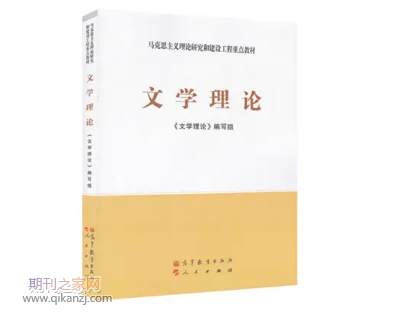
漢代將軍幕府文學是值得注意的文學形態。對此,個別學者雖有涉及,但成果相對偏少。基于此,本文試就漢代將軍幕府文學創作與文體成就進行探討。
一幕府原本具有鮮明的軍事性,是將帥在領軍
與戰爭時處理軍情的場所。在漢昭帝之前,幕府成員大多根據統治者或將軍的要求隨時征調。每次戰事結束,將軍旋即罷遣部隊,上交軍權,其幕府自然也就解散了。這種征調與戰后即罷的體制決定了當時入幕士人應是較少的。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輔政,標志著漢代將軍幕府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轉變。它從單純的軍政場所轉變為軍政與行政兼具的機構,具有了輔政治事的大權,自然也就具有了行政職能。從此之后,士人入幕成為漢代特別是東漢很突出的風氣。對此,《冊府元龜·幕府部》云:“兩漢而下,公府將幕,咸得以辟署賓佐,咨其策畫焉。故士之懷才者,莫不愿伸于知己,而效其所長者矣。”[1]
文學論文范例:外國文學經典重讀與外國文學研究
第8冊8279“中興之后,辟召尤盛,故當時幕府,彬彬然多賢才焉。”[1]第8冊8356據筆者考辨,兩漢比較重要的將軍幕府主要有:西漢霍光幕府,其成員主要有楊敞、蔡義、田延年、丙吉等;王鳳幕府,成員有杜欽、陳咸、陳湯等;王音幕府,成員有谷永、揚雄、杜鄴等;東漢東平王劉蒼幕府,成員有吳良、朱暉、閔仲叔、杜撫等;竇憲幕府,成員有班固、傅毅、崔骃、廉范等;鄧騭幕府,成員有楊震、朱寵、陳禪等;梁商幕府,成員有李固、周舉、馬融、董尚等;梁冀幕府,成員有吳祐、崔寔、趙岐、應奉、馬融、朱穆等;何進幕府,成員有袁紹、邊讓、陳琳、孔融等。
另外,王莽新朝、更始時期,一些將軍也有開府辟署的權力與資格,像莽新更始將軍廉丹,更始尚書仆射、行大將軍事鮑永等。著名的文人馮衍就先后仕進于二人的幕府。就職事而言,幕主辟請著名士人的目的,主要是讓其協助處理各方面軍政事務,為其出謀劃策,“職參謀議”[2]3564,發揮智囊作用;同時,“典文章”[2]819,負責軍政文書事宜,撰寫各類文章。
在此情況下,士子立足于幕主的軍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發揮文學特長,參與文事活動,進行文學創作,自然成為其入幕期間的重要任務。據《漢書》《后漢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統計,目前所能見到且明確屬于幕府作品的,主要有楊敞《奏廢昌邑王》《奏立皇曾孫》、丙吉《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杜延年《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功》《說王鳳》《復說王鳳》《說王鳳重后父》《說王鳳絕罽賓》《說王鳳處置夜郎等國》《說王鳳治河》《復說王鳳起就位》《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戒王鳳》、谷永《說王音》《謝王鳳書》《與王譚書》《與王音書》、揚雄《羽獵賦》、杜鄴《說王音》《說王商》、馮衍《說廉丹》《復說廉丹》《計說鮑永》《遺田邑書》《說鄧禹》《與鄧禹書》《詣鄧禹箋》《與陰就書》《又與陰就書》、班彪《王命論》、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與竇憲箋》《涿邪山祝文》《封燕然山銘(并序)》《竇將軍北征頌》《安豐戴侯頌》、崔骃《大將軍西征賦(并序)》《大將軍臨洛觀賦》《奏記竇憲》《與竇憲箋》《獻書誡竇憲》《北征頌》《仲山父鼎銘》《安豐侯詩》、傅毅《竇將軍北征賦》《西征頌》、朱寵《上疏追訟鄧騭》、龐參《奏記鄧騭》、崔瑗《說長史陳禪》①、李固《奏記梁商》《奏記梁商理王龔》、馬融《廣成頌》《飛章虛誣李固》、朱穆《奏記大將軍梁冀》《復奏記梁冀》《又奏記梁冀》《崇厚論》、崔琦《外戚箴》、應劭《駁韓卓募兵鮮卑議》、袁紹《說何進》《復說何進》②、陳琳《諫何進召外兵》等。
事實上,在當時的歷史文化環境之下,幕府創作要更加豐富。陳湯擔任王鳳幕府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于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3]3023。在竇憲出擊匈奴時,崔骃針對其不法行為,“前后奏記數十,指切長短”[2]1721-1722。梁冀“行多不軌”,其幕府掾屬崔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2]2619。這些史實充分反映了當時幕府文人的創作狀況,僅崔骃就有數十篇奏記,惜因文集佚失或不為典籍所載等原因,絕大部分作品已不可見。
二由于入幕士子的主要職責是發揮智囊作用,獻計獻策,協助幕主進行軍政事務處理,其創作自然多以應用文為主,以解決幕主所面臨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問題為根本目的,具有強烈的現實時務性、應對性。這是幕府文學作為一種文學形態所具有的鮮明特征。這種特征在丙吉、杜欽等人的作品中有充分體現。元平元年(前74),大將軍霍光廢黜昌邑王劉賀之后,迎立新帝成為當時首要問題。為此,長史丙吉作《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該文首先肯定霍光廢除昌邑王之舉,然后直接介紹劉病已(宣帝)的相關情況:“竊伏聽于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
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愿將軍詳大議……”[4]296文章首先提出病已為“遺詔所養”這一要害問題,暗示他具有繼承皇位的合法性、正統性;然后介紹其年齡、經學素養及道德品質,說明他具備為帝的各方面素質。該文以立帝為題,事關重大,對霍光以朝廷重臣身份形成《奏立皇曾孫》一文③,進而迎立宣帝發揮了重要作用。陽朔元年(前24),京兆尹王章在與王鳳的斗爭中被劾奏致死,人們為此對朝廷頗多譏諷。
為補救過失,挽回時論,杜欽作《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該文指出吏民不了解王章之事,多認為他是因直言而死,為打消吏民疑惑,作為輔政者的王鳳應當舉行直言極諫科的選拔。由此可見,此文所具有的政治應對性是很鮮明的。士人為維護幕主的根本利益,往往敢于針對其行事及其缺失、不法之處進行諷諫。
永元元年(89),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骃為掾;出擊匈奴時,又擢其為主薄。“憲擅權驕恣,骃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為主簿,前后奏記數十,指切長短。”[2]1721-1722陽嘉二年(133),楊倫被大將軍梁商辟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2]2565。崔琦在入仕梁冀幕府期間,“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2]2619。士人的這種諷諫意識自然導致了其作品蘊含著強烈的批判性。如,崔骃諷諫竇憲的作品大多不可得見,但由《太平御覽·人事部·諫諍》所載《與竇憲箋》可窺知一二。
據《后漢書》本傳,竇憲本人頗為貪婪,一些趨炎附勢之人自然會貢物求榮,崔文就是針對這種問題而作的。作者首先描述漢陽太守帥吏卒貢獻鷹狗的情景,“云欲上幕府”一句巧妙道出了竇憲的貪婪好異;然后引用“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公侯非兕靡射”等《傳》《禮》之語,批評竇憲所為非法,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資”[5]第5冊,277,直接擺明諷諫態度。桓帝即位后,朱穆曾多次上書幕主梁冀。“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2]1462其《奏記大將軍梁冀》借歷法天象之事,向梁冀進諫:“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6]286這些文句徑陳政治問題,直接批判梁冀競逐私欲,縱容小人,體現出鮮明的直諫精神。
三一般而言,各類傳統文體都有規定性的題材
與表現對象,呈現出較穩定的文體樣式。但在某種情況下,由于承擔了特殊的文學任務與要求,相關文體書寫自然能夠突破傳統題材的拘束,從而蘊入新的內涵;同時,能夠打破既定書寫模式,形成新的文體樣式。其中,竇憲幕府對傳統文體的發展尤其顯著,這充分體現在祝、頌等文體上。永元元年六月,竇憲統率諸部皆會于涿邪山,舉行祝禱儀式。
班固《涿邪山祝文》即是應祝禱需求而作,有鮮明的儀式性。該文今存四句:“晃晃將軍,大漢元輔。”“仗節擁旄,鉦人伐鼓。”[6]259祝文主要是向神明與先祖等進行禱告、以求福佑的一種文體,其文體基本要求是“降神務實,修辭立誠”[8]375,即祝文主要用于降神,因此文風要樸實,寫作態度要真誠敬重。基于這種文體要求,班文應有向天地神靈祈禱以求勝利的內容。
但除此以外,從現存殘句看,該文重在頌贊竇憲的英勇神武與出征盛況,氣勢宏大,其文風絕非樸實所能概括,這反映了班固在祝體上的突破。頌源于《詩經》中的“商頌”“周頌”等,最初主要用于“告神”等祭祀儀式,以歌頌帝王先祖的盛業功德為主,有鮮明的儀式性。摯虞《文章流別論云》:“頌,詩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9]到了漢代,其儀式性逐漸削弱,主要用于歌功頌德。對此,劉師培云:“兩漢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為告神之樂章矣。”[10]
同時,其基于祭祀功能與儀式性質而形成的文句典雅、以四言為主的文體特征,總體上為漢代所繼承。像劉向《高祖頌》、揚雄《趙充國頌》、史岑《出師頌》等均是如此。然而,在文體發展過程中,一旦應用場合、文學任務發生變化,頌體的文體特征、結構模式自然也會隨之而變。班固《竇將軍北征頌》就證明了這一點。
該頌由序引、頌語兩部分組成。序引已成為文章的主體,先敘寫車騎將軍竇憲的德行才干,次寫他精選部隊,率軍出征,再寫他奮力征戰,破敵制勝,最后寫其文武并隆的功勛,鋪陳繁富,文字美瞻。本應為主體的頌語,則寥寥六句:“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濳,眇兮與神參。”[6]252可見,班頌已總體上打破了傳統頌體的文體結構、模式,已經變成以序引為主的散文創作。當然,頌語在形式上還是保持了四言形式,體現出對傳統文體特征的繼承。
箋多用來反映作者與幕主、府郡的日常往來及其所見所感,借以向幕主、府郡等表達個人情懷或認識,有的還有一定的規諷作用,具有鮮明的日常性、私情性特征。如馮衍《詣鄧禹箋》云:“今日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為適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5]第7冊,747據《東觀漢紀》,建武初,馮衍曾辟將軍鄧禹府,“數奏記于禹,陳政言事”[15]。
此文即作于該時期,通過裘蓑之用抒發作者希企重用的情懷。班固《與竇憲箋》為短文數則,如其中一則云:“昨上以寶刀賜臣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以賜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慚。”[6]245這些箋文描寫日常生活中竇憲對他的賞賜,抒發其喜悅心情及對竇憲的感念。自漢武之后,因受崇經意識影響,漢代應用文多追求典雅繁富,而箋體文則因重在反映日常往來及所見所感,故而較為隨意,往往由感而發,舒散自然,形制短小。這種文體風格、特征在漢代文章史上是有價值與意義的。
引用文獻:
[1]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M].周勛初等,校訂.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2]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M].嚴可均,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5]李昉等,撰.太平御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后全漢文[M].嚴可均,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歐陽詢.藝文類聚[M].汪紹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文心雕龍義證[M].詹锳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韋春喜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