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神話比較研究百年回眸
時間:2020年11月12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 要: 蒙古神話比較研究走過百年歷程,前仁學者主要借鑒歷史學、民族學以及比較文學、比較神話學的理論與方法,探討蒙古神話與突厥語族民族神話、佛教神話或古印度、藏族神話以及其他相關民族神話的關系,追尋蒙古神話的產生發展及其多元文化特征,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 今后應當進一步開發利用蒙古神話及其相關民族神話資源,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范圍,力爭比較研究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 蒙古神話; 比較研究; 百年; 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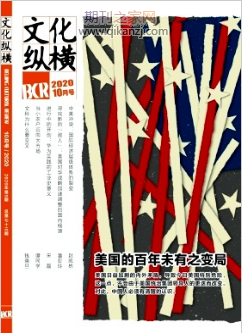
蒙古神話是北方阿爾泰語系諸民族神話的一部分,屬于古老的民族神話。 關于蒙古神話的關注,從布里亞特蒙古學者道爾吉· 班札羅夫所著《黑教或稱蒙古人的薩滿教》(1846年)一文的問世算起,已有173年的歷史; 而蒙古神話的比較研究,從日本學者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發表的《蒙古的古傳說》 (1912年)一文算起,已有107年的歷史,因此蒙古神話比較研究確實是走過了百年歷程。
回顧百年學術歷程,蒙古神話的比較研究是從無到有,從淺入深,在研究方法上由單一性向多樣性轉換。 而比較研究則始終遵循蒙古民族歷史文化的發生、發展以及民族間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蒙古神話與相關民族或國家神話之間比較研究。 首先,蒙古民族與突厥語族諸民族的語言同屬阿爾泰語系,具有天然的族源與語言文化關系,神話文化亦然,兩者很多神話是同源或接近同源。
但是后來諸民族文化發展的脈絡不同,接受宗教文化的不一,諸民族神話之間也發生了諸多差異,學者們根據上述歷史線索,在兩者神話之間進行比較研究,追索其文化的相同與差異,力圖復原其原初面貌。 其次,蒙古民族在歷史上曾經接受數種宗教,這些宗教信仰對其思想觀念產生巨大影響,但其中藏傳佛教對蒙古文化的影響最深,就神話而言,很多古印度神話、西藏神話以及佛教神話均以佛教為媒介傳入蒙古文化領域,與蒙古原有的神話結合,形成新的“神話”,使得蒙古神話成為具有濃厚佛教色彩的神話。
相關學者又關注蒙古民族接受佛教之后其神話發生變化,這一歷史事實,自然而然地選擇蒙古神話與古印度神話、藏族神話以及佛教神話之間的比較研究。 蒙古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也與毗鄰而居的兄弟民族發生諸多文化聯系,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發生諸民族神話文化的交匯和交融,為了驗證民族之間早期文化交流的事實,學術界又選擇了蒙古神話與這些民族神話的比較研究。 蒙古民族也在其最輝煌的時期,即十三世紀,與亞洲和歐洲很多民族發生諸種聯系,也有過文化交流的機遇,在諸民族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神話文化也許受到某種影響。 所以,蒙古與上述民族之間的神話的比較研究也勢在必行。
本文主要依據蒙古民族的歷史發展與其他相關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的脈絡,考察梳理一百多年來蒙古神話比較研究的學術歷程。
一、蒙古神話與突厥語族民族神話的比較研究
神話是人類早期文化的產物,在諸民族先民氏族社會時期已經產生了最初神話,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氏族集團逐漸演化為民族的過程中,諸民族先民將自己“分到”的神話加以“改寫”并傳給后人,最后形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各民族神話。 而這些“改頭換面”的民族神話中多少也能攜帶一些古老神話的要素,神話學家的任務就是將諸民族的神話集中起來進行比較研究,還原其原始形態,建構早期人類神話文化的原初面貌。 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民族和突厥語族民族之間族源及語言文化關系密切,兩者的神話文化關系亦然。 因此,蒙古民族和突厥語族民族神話文化關系早已走進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以及神話學家的視野。
族源神話,又稱族源傳說。 學術界首先關注蒙古民族與突厥語族民族之間存在的族源傳說的關系。 日本歷史學家、民族學家白鳥庫吉于1912年發表《蒙古的古傳說》一文。 論文論述《蒙古秘史》所載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傳說,即所謂“蒼狼白鹿傳說”以及波斯史學家拉施特所著《史集》所載“額爾古涅·昆傳說”,然后與這些族源傳說與《隋書》所載突厥人狼祖傳說進行比較,同時把這些傳說與烏孫、高車等古代突厥語族民族狼祖神話傳說進行比較,指出了蒙古民族和突厥語族民族族源傳說的同源特質。 白鳥庫吉的這篇論文首度關注蒙古和突厥語族民族神話的關系,具有較高的學術創新價值和意義。
1938年白鳥庫吉又發表《突厥及蒙古的狼種傳說》一文,稱“蒙古的狼種傳說實際上胚胎于突厥的建國傳說(即“族源傳說”),蒙古的狼祖傳說是在突厥狼祖傳說的基礎上產生,實為突厥傳說的發展了的形式; 突厥語族民族狼祖傳說中描繪的“西海”,相當于《蒙古秘史》第一節所載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傳說中的“騰汲思”(Tengiz),而高昌國狼祖傳說中的“其國西北洞穴”相當于拉施特《史集》所載“額爾古涅·昆傳說”中的額爾古涅(Ergune Kun)。
1913年,內藤虎次郎(Naito Torajiro)發表《蒙古的建國傳說》一文。 他把蒙古人的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傳說和阿闌豁阿感生傳說與拉施特《史集》所載“額爾古涅·昆傳說”進行比較,認為“狼鹿婚配”傳說與《北史》所載突厥建國傳說和高車狼祖傳說相似。 他引用王充的《論衡·吉驗篇》所載夫余的東明傳說和高句麗的朱蒙傳說,認為感神生子的“阿闌豁阿”故事在塞外民族中不無多見。 這個傳說與夫余、高句麗和百濟的建國傳說更接近。 而蒙古的“狼鹿婚配”傳說則是蒙古接觸突厥之后,襲取其說,僅附加一些其他內容而已。
眾所周知,后世對《蒙古秘史》記載的“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傳說”和拉施特《史集》所記“額爾古涅·昆傳說”與突厥語族民族狼祖族源傳說進行比較研究,尋求兩者族源傳說之間的相同性和差異性,探索這些傳說的同源特色,但是必須關注的是,這些比較研究日本學者一百多年前已經進行,并得出蒙古、突厥傳說同源的結論。 此后日本學者一直沒有停步,他們繼續深入研究蒙古傳說和突厥語族民族傳說,使得這一領域研究步步深入。
1964年,日本學者村上正二(Murakami Syoji)發表長篇大論《蒙古部族的族祖傳承》,文中探討蒙古的“蒼狼白鹿傳說”“阿闌豁阿傳說”和“額爾古涅? 昆傳說”,指出,蒙古古老的傳說“額爾古涅? 昆傳說”反映了由涅古思和乞顏兩個父系外婚集團形成的蒙古部族社會的基本結構。 而且,涅古思和乞顏集團分別以“蒼狼”和“白鹿”為氏族族靈,以此表征兩個外婚氏族的并存。 據此,可認為,以圣獸象征的族靈為外婚集團各自的圖騰。
并且,這些傳說敘說著蒙古民族的發祥和遷徙,同時,民族的“滅絕”和“再生”是得力于薩滿的“鍛冶部族”而實現的。 而這些傳說的母題與東南亞一帶傳承的民族發祥傳說母題同屬一個類型,不盡如此,這些傳說還和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的“鍛冶部族”創世故事相關聯。
村上正二在當時已經提出“額爾古涅? 昆傳說”中的涅古思和乞顏兩氏族集團分別以“蒼狼”和“白鹿”為族靈。 他的這一觀點,比中國學者提前了半個世紀。 從表面上看,村上正二未能對蒙古的族源傳說與突厥語族民族族源傳說進行比較,但他最后提出的“鍛冶部族”創世故事指的是古突厥阿史那氏的狼祖傳說,所以他的上述研究仍然基于蒙古和突厥的同源神話傳說。
在國內最早關注蒙古、突厥族源傳說及其兩者關系的是韓儒林先生。 1940年他發表《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以各種文獻記載為依據,首先探討烏孫、突厥、高車等突厥語族民族狼祖傳說并與蒙古蒼狼白鹿傳說比較,然后畏吾兒和蒙古感光生子傳說進行比較,最后探討蒙古接受伊斯蘭教和佛教之后其族源傳說的演繹改變等。 韓儒林的這篇論文是國內首度比較全面深入研究突厥和蒙古族源傳說的學術成果,為后來的研究打造堅實的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呼日勒沙研究蒙古族源傳說,并與突厥語民族族源傳說進行比較。 他發表《圖騰理論與孛兒帖赤那和豁埃馬闌勒》《貓頭鷹崇拜與氏族起源傳說》等系列學術論文。 他的論文涉及蒙古、突厥語族民族族源傳說,將這一研究引入蒙古神話傳說比較研究的領域。 滿都呼教授的《蒙古語族與突厥語族民族族源傳說比較凡說》,是蒙古、突厥族源傳說比較研究力作。
該論文吸收借鑒神話學、圖騰理論以及歷史學、語言學等學科理論與方法,比較蒙古、突厥語族民族族源傳說,探討兩者的共性與差異性。 其中蒙古、突厥語族民族族源傳說中的烏鴉圖騰族源傳說、天鵝圖騰族源傳說以及樹木圖騰族源傳說進行比較,認為蒙古、突厥各民族族源傳說中的動物圖騰或植物圖騰是相同的,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氏族部落擁有相同的圖騰,證明這些氏族可能是同源的。 在上述民族族源傳說中氏族的圖騰動物或圖騰植物相同,以此推斷,阿爾泰語系蒙古民族和突厥語族民族先民擁有相同的祖先。
那木吉拉的學術論文《“符離之窟”與“額爾古涅·昆”——阿爾泰語系突厥、蒙古語族民族先民“先祖之窟”信仰及神話傳說探討》一文也論及蒙古、突厥語族民族神話傳說的相通性,提出漢籍所載突厥語族民族狼圖騰神話中的“符離之窟”(“狼之窟”)與蒙古源傳說中的“額爾古涅·昆”存在相通性,它們均為神話傳說中的幻想境界,是蒙古、突厥先民“先祖之窟”的象征,它的原型取自大自然的山穴。 這些山穴作為原始部族的生活場所,后來人類將其神圣化,成為古人頂禮膜拜的對象,并在神話傳說中作為圣地頻繁登場。 論文還指出,“先祖之窟”信仰習俗及其神話傳說在亞洲北部諸民族中廣泛傳承,是北方少數民族信仰習俗文化的一部分。
除上述之外,學術界也從蒙古、突厥語族民族之間語言文化密切關系為基礎,頻繁比較分析兩者的神話傳說,試圖解釋兩者早期文化的相似度。 那木吉拉《〈蘇勒哈爾乃傳〉及其常青植物神話母題——蒙古、突厥語民族常青植物神話比較研究》《突厥語族和蒙古語族民族常青植物神話比較研究》等學術論文中將蒙古的常青植物神話和蒙古文《蘇勒哈爾乃傳》所載神話、古亞歷山大大帝傳說中的常青植物神話母題以及印度故事、哈薩克長命泉神話進行比較,試圖追溯蒙古、突厥語族民族常青植物神話原初形態。
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阿爾泰(Altaians)族與蒙古族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語言文化關系,兩者的神話也有很多相通之處,尤其是阿爾泰族與相鄰而居的布里亞特蒙古之間的文化交流很密切。 陳崗龍根據上述民族之間的文化關系,發表《蒙古薩滿神話與阿爾泰神話的比較研究》一文,論文首先討論布里亞特蒙古、蒙古最初薩滿來歷的神話、蒙古薩滿神話中的鳥與薩滿關系以及最初薩滿與熊之間的相互轉換關系,然后蒙古薩滿神話與阿爾泰族神話進行比較,指出阿爾泰語系蒙古民族神話和阿爾泰族神話中,薩滿的職能相同,即從天上來到人間拯救被魔鬼奪走人類靈魂的薩滿職能相同。
綜上所述,一百多年來學術界一直關注蒙古神話傳說和突厥語族民族神話傳說的關系,尤其是注重族源傳說的關系,其研究從膚淺到深入,從狹窄到寬闊,從研究學科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單一性到多樣性,從歷史學、傳說學以及民族學等早期傳統的學科理論研究發展到現在的比較神話學、比較故事學以及當下流行的母題、類型學方法進行研究,取得令人振奮的成就。 但是蒙古、突厥語族民族神話傳說的比較研究仍然有著較大的空間,如進一步挖掘活態的民族語神話傳說資料,并翻譯利用; 擴大比較研究范圍,加強比較研究力度等。
二、蒙古神話與佛教神話及印藏神話的比較研究
從古匈奴時期佛教傳播于北方阿爾泰語系諸民族,在思想觀念上影響了北方民族先民,但是蒙古民族真正意義上的接受佛教,是十三世紀。 在元代,蒙古上層社會普遍接受藏傳佛教,其思想觀念極大地影響了蒙古上層社會,有元一代,佛教成為“國教”。 十六世紀藏傳佛教再度弘通蒙古地區,在數百年間幾乎所有蒙古諸部無一不接受佛教,佛教的思想觀念極大地影響了蒙古民眾。
古印度和藏族神話以及佛教神話主要以佛教為媒介,與蒙古神話碰撞,最終使得蒙古神話發生變化。 在蒙古神話中產生了移植的具有古印度佛教色彩的神話和藏族神話,蒙古原有的神話也受到古印度或具有佛教色彩的神話影響,部分藏族神話也進入蒙古文化的領域,影響蒙古神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現象。 學術界根據蒙古神話與佛教神話、印藏神話之間的這種關系,闡釋兩者之間的關系之由來、文化交流之后發生的變化。
蒙古國學者S·杜力瑪《蒙古神話形象》一書中說,蒙古后世文人的神話文化的知識大都來自古印度文獻《吠陀》、史詩以及佛教神話。 蒙古的喇嘛學者們為古印度和藏文典籍作注時,也要利用印度和藏族的神話。 而他們把起源于印度和藏族的神話與蒙古本土的生活習俗和蒙古人的思維方式結合起來,將其改編為蒙古民眾容易接受的方式。
前蘇聯學者С? Ю? 涅克柳多夫在《關于蒙古神話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很難將佛教神話從西藏—蒙古共同文化寶庫中分離出去,而且佛教神話對于蒙古精神文化來說,也很難斷定將佛教神話視為“舶來品”的觀念是正確的。 佛的形象、象征以及情結已經深深滲透到蒙古人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成為蒙古文學、藝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色巴圖和寶力高所著《傳播于蒙古的佛教神話功能》一文主要探討傳播于蒙古的佛教神話的兩個功能,之后論述蒙古神話中的佛教神話影響之深刻。
有關蒙古神話與佛教文化影響的討論,時至今日仍在繼續,扎拉嘎夫于2018年在《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蒙古文版)上發表的《蒙古神話的佛教影響探析》一文中從神話與宗教、神話人物與宗教人物的關系來解析神話與宗教的密不可分的關系。 并用蒙古神話中大量存在的佛教教義戒律以及形象、情節的介入來闡釋蒙古神話的佛教影響。
由于蒙古神話與古印度神話、佛教神話、藏族神話之間的這種“不可分割”的關系,學術界從不同角度研究兩者的關系,他們往往采用比較的方法。 那木吉拉著《蒙古神話比較研究》一書中作者借鑒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和比較故事學的母題、類型研究方法,考察蒙古創世神話、人類起源神話、騰格里(天神)神話、日月星辰神話和動植物神話與印、藏神話、佛教神話的關系,探討蒙古神話如何以佛教為媒介,接受佛教神話和信仰佛教的古印度、藏族等民族或國家神話影響以及蒙古神話接受影響之后發生的發展變化。 該學術專著在蒙古民間文學及神話研究領域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得到有關專家學者的首肯。
“攪拌乳海神話”系古印度神話,隨佛教傳遍整個亞洲乃至世界很多地方的著名神話。 蒙古族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該神話。 該神話文本不僅在蒙古文宗教經典和歷史文獻當中有所記載,在蒙古民間也流傳各種口頭變體。 陳崗龍著《蒙古攪拌乳海神話的比較研究》,一文將蒙古與印度攪拌乳海神話進行比較,追溯其神話原型,進一步分析蒙古攪拌乳海神話諸母題、情節,并與相關神話、史詩中的神話母題、情節進行比較,試圖闡釋蒙古攪拌乳海神話與相關國家或民族神話之間的關系以及蒙古神話自身固有的特征。
古印度“攪拌乳海神話”進入蒙古文化圈,在其影響下蒙古民間產生獨具特色的日蝕月蝕神話。 那木吉拉著《蒙古神話和英雄史詩中的印度日蝕月蝕神話影響》一文也借鑒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探討古印度“攪拌乳海神話”對蒙古神話和英雄史詩的影響及其途經。 論文首先討論蒙古古文獻所載古印度“攪拌乳海神話”文本,然后探討該神話對蒙古神話的影響,在蒙古民間口頭產生的日蝕月蝕神話及其變體。
那木吉拉著《蒙古族北斗七星神話比較研究》一文也是蒙古神話與印藏神話比較研究之作,論文首先對蒙古北斗七星神話與《五卷書》《尸語故事》中相關故事進行比較,然后對蒙古北斗七星神話與藏族北斗七星神話進行比較,得出相應的結論:蒙古族北斗七星神話的核心母題產生于蒙古人信仰佛教之前。 而蒙古各部普遍接受佛教觀念的過程中,印度和藏族離奇故事和藏族北斗七星神話影響蒙古神話,其情節母題替代或充實了蒙古神話主人公的經歷,使之成為尤為完美無缺的神奇形象。 蒙古神話雖然接受印藏神話故事的影響,但其主題內容及其附件依然保留下來,仍不失為是蒙古固有神話。
那木吉拉著《蒙古創世神話的佛教文化影響》一文專門探討佛教文化對蒙古創世神話的影響。 論文評介相關學者們對蒙古神話與佛教神話和信仰佛教的印度、藏族等民族和國家神話對蒙古創世神話的影響,探討了蒙古神話接受佛教神話以及相關民族或國家神話影響之后發生的變化。
巴雅爾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用蒙古文撰寫了《蒙漢創世神話比較》一文,該文運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方法,探討蒙漢創世神話的關系。 首先肯定此前有些學者提出的漢族創世神話接受影響于印度創世神話的觀點,然后認為漢族創世神話又以佛教為媒介,影響蒙古創世神話。 我國漢族“盤古開天辟地”神話是否接受印度同類神話影響,這是學界至今爭論的學術話題。 同樣,蒙古創世神話是否通過佛教媒介,接受漢族創世神話影響,也是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
總之,蒙古神話與佛教神話或與佛教相關的民族或國家神話關系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這一學術研究還在進行當中,相信今后該領域的研究在更加寬廣的領域內行進,相信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
三、蒙古神話的多角度多層次比較研究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相關學者關注蒙古神話和跟蒙古民族無“實事聯系”民族神話之間的關系,同時在與蒙古民族毗鄰的或相距甚遠,但有“實事聯系”的民族神話之間的關系,通過比較探討蒙古神話的特點及其產生、發展的軌跡。
1938年播磨酋吉(Harima Yukichi)發表《布里亞特人的世界創造說》一文,介紹最高神創造大地和人類、狗發毛的來歷、洪水神話等。 關于布里亞特人的口承,他說布里亞特蒙古在二、三百年間與俄羅斯人雜居,接受了俄羅斯文化的巨大影響,從而布里亞特蒙古的固有神話傳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影響。 布里亞特人的創世傳說也接受《圣經》的影響,又受到薩滿教和佛教的感化。
播磨酋吉的論文《布里亞特人的世界創造說》發表63年之后,陳崗龍發表《蒙古洪水神話的基督教因素》一文,同樣探討布里亞特蒙古神話的基督教影響,認為布里亞特蒙古創世神話有兩個系統:一種是保留原始薩滿教信仰的神話,這類神話主要反映布里亞特蒙古先民的氏族社會狀況; 另一種則是滲透基督教觀念的較晚近的神話。 這一類神話在表面上也采用了《圣經》所載造人神話和洪水神話母題情節。 該文還認為,布里亞特創世神話中隱喻了薩滿教同基督教的斗爭,其洪水神話中的滔天洪水象征著基督教文化的大洗禮。
潛水神話(earth-diver myth)為創世神話的一個重要類型,潛水神話稱,神命其助手神潛入海底撈出泥土創造了世界。 陳崗龍著《蒙古潛水神話的比較研究》一文將蒙古潛水神話置于該神話類型所分布的諸民族大文化圈內,進行比較分析,追尋蒙古潛水神話的發生、演異的軌跡,剖析蒙古潛水神話的多元特征和多層次特征。
1974年日本學者田中克彥(Tanaka katsuhiko)發表《蒙古神話和日本神話》一文。 該長篇論文以序言、蒙古神話的資料特質、布里雅特口頭傳承的意義、高天原和“天降”、地界里的誕生—從神到英雄、雅庫特“天降”二類型、“記紀神話”和其他類似點、北方系神話里的南方要素等部分構成。
序言里主要論述了日本與蒙古以及整個阿爾泰語系民族神話的比較研究的緣起。 論文的其余部分中主要以論述蒙古及布里亞特神話資料的特點,并以《格斯爾傳》中的神話故事為例,與日本的相關神話故事比較,得出如下結論:蒙古及近鄰民族傳承和日本神話之間存在不少的相通要素。 這些共通要素中,即有來自蒙古或者是阿爾泰語系固有起源的成分,也有印度、中國西藏、伊朗以及其他民族成分。 所有這些都是從南方,與日本不同的途經得到的共同的文化遺產。
那木吉拉還發表了《中亞地區狼和烏鴉信仰習俗及神話傳說比較研究——以阿爾泰語系烏孫、蒙古事例為中心》一文。 該文借鑒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和影響研究的方法,探討阿爾泰語系蒙古、突厥語族民族的狼和烏鴉雙重信仰及其神話傳說,并與古羅馬的狼和啄木鳥信仰以及相關人物傳說進行比較,追尋阿爾泰語系蒙古、突厥語族民族先民的狼和烏鴉雙重信仰及其神話傳說及其產生發展的脈絡,該論文的英語譯文發表于《亞洲民族學研究》。
那木吉拉著《蒙古洪水神話比較研究——以〈天上人間〉和〈獵人海力布〉為中心》一文,以蒙古洪水神話《天上人間》和《獵人海力布》為研究對象,與滿族和鄂倫春族洪水神話、古印度洪水神話、漢族洪故事進行比較,探討蒙古洪水神話與上述民族同類神話異同及其特征。
最后,蒙古民族與滿族在歷史上不僅居地相連,而且兩者語言同屬阿爾泰語系,語言及文化關系密切,神話也諸多相同之處。 因此學術界又關注蒙古族與滿族神話的關系。 包哈斯完成博士學位論文《蒙古族和滿族神話的比較研究》,這是國內外第一部滿蒙神話比較研究成果。 包哈斯又發表《天神大戰—蒙古族和滿族的天神神話比較研究》一文。 論文指出,蒙古族和滿族的天神神話均有鮮明的特點和有趣的形象,雖然不像希臘神話那樣有完整的體系和故事情節,但在兩個民族的神話中天神神話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如蒙古族神話“天神之戰”和滿族神話“天宮大戰”,都通過講述天神之間發生的戰爭,體現了這個世界開初的模樣和秩序,構建宇宙模式,表現了初民對宇宙、人類本質的理解和認識。 本文比較兩者的異同,欲追根溯源,旨在展示滿蒙兩個民族先民遠古文化某些相同特征和殊異特征及其產生的原因原委。
文學方向論文范例: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價值觀的建構
綜上所述,蒙古神話比較研究走過百年歷程,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至本世紀一十年代初為蒙古神話比較研究的黃金時期,蒙古神話的比較研究在上述三個領域內如火如荼地進行,在研究方法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采用歷史學、民族學以及民間文藝學的方法,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主要借鑒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學、比較神話學的方法以及母題、類型研究方法,以追尋蒙古神話發生、發展軌跡及其多元文化特色和文化內涵。
總體上看,經過幾代學術同仁的共同努力,蒙古神話的比較研究取得不菲的成就,但是該領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還需要走很長的路。 今后的蒙古神話比較研究,要進一步挖掘利用蒙古神話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神話及其語境資料; 及時更新研究理論與方法; 擴展比較研究領域,力爭比較研究向縱深發展。
作者簡介:那木吉拉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