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ߵķ����cĪ���ČW(xu��)�ij�����W(xu��)
�r(sh��)�g��2020��03��02�� ����ČW(xu��)Փ�� �Δ�(sh��)��
����Ī���ČW(xu��)�ij��Ʒ���ںܴ�̶���Դ�����c�Ї�(gu��)�vʷ���F(xi��n)��(sh��)֮�g���ڵĽY(ji��)��(g��u)���P(gu��n)(li��n)����(du��)�Ї�(gu��)�vʷ���F(xi��n)��(sh��)�ĸ�֪����(g��u)��Ī��ʷԊ(sh��)�Գ�����W(xu��)����˼�|(zh��)�أ��Z�Z���ҵĚvʷ�\(y��n)��(d��ng)���o���K�ҵ����ζ���(zh��ng)��ȫ��ʽ�^��ҕҰ���c�vʷ�o�ܼm�p���UҰ����������Ȼ����־����������Ī�Ի��p�`���صض�������ͿĨ������ɢ�l(f��)����ʎ���ۜ����Ž��ij�ߚ��|(zh��)��
������(y��ng)ԓ���������ČW(xu��)�г���“��(qi��ng)��”“�(y��ng)��”һ�}��(du��)Ī���ČW(xu��)��Ӱ푣����(y��ng)�����W(xu��)�y�Ժ��wĪ�Գ�����W(xu��)��ȫ������1980��������Ժ�“��˼����”��“�����”���Ļ��Շ��У�Ī�������c��“��˼”ȡ��ĺ���(y��ng)��������ͨ�^��ȡ����Ѹ������ij�����}���γ��������“��Գ��”���|(zh��)��Ī���ČW(xu��)Ҳ�ͳ����(y��ng)��������W(xu��)�c��Գ�����W(xu��)���p��׃�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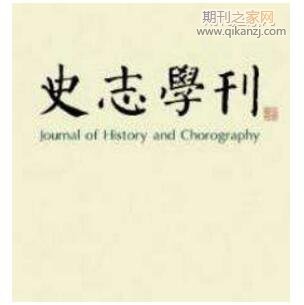
�����ČW(xu��)Փ��Ͷ�忯���ʷ־�W(xu��)����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p�¿�)���ÿ�����ɽ���ط�־;��ɣ��1993�ꄓ(chu��ng)�����Z�N�����ģ��_������16�_������أ�ɽ��ʡ̫ԭ�У��]�l(f��)��̖(h��o)��22-72����ʷ־�W(xu��)�����njW(xu��)�g(sh��)���ע�،W(xu��)�g(sh��)�о����Ǽ��vʷ�W(xu��)����־�W(xu��)������W(xu��)��һ�w�ČW(xu��)�g(sh��)�о����
����һ��“��Գ��”��Ī�Գ�����W(xu��)����Ҫ����
����Ī�ԹP�µ����������������(qi��ng)����������ռ�������Pɏ(���t�������塷)���O��(gu��)��(��˾���Ů�ˡ�)��˾�R��(k��)��˾�R�Z(���S����Ρ�)���O��(��̴���̡�)���ڏ�(qi��ng)������(hu��)����ͼ�ʎ�Ěvʷ�����У�Ҳ����(f��)��(j��ng)�������W(xu��)��Ӣ�۵����ԡ����@Щ“��Ӣ��”��Ӣ�����죬ǡǡ�w�F(xi��n)��Ī��“�����”�ij�����W(xu��)�����S����Ī�ԹP�µ��@Щ����Q��Ӣ�۵�“��Ӣ�ۻ�”���������Ī�Խ���“��Ӣ��”��Ӣ�۠I(y��ng)��(g��u)������W(xu��)���P�³���������У�����ĺ���b���c�������\(y��n)������������ϵ���������Y(ji��)���������(sh��)���K���A�a������Ӣ��֮�¿���̓��(g��u)��Ӣ��֮��֮�ԅs�o�����Ρ�Ī�����R�пյ����������������h(yu��n)�ĸ��������������@�����_�Q�������Ƴ��ļ��О�ȪԴ���Ķ���Խ�˚vʷ���x�܌W(xu��)���Ļ�������b����
��������Ҫ���ǣ�Ī����չ�����ČW(xu��)���L(zh��ng)�ڱ���(j��ng)�������W(xu��)�ų�͉��ֵ�“��Գ��”����������������������P�µ�ĸȸ�����U�f“��Գ��”������һֻ���˾S�o(h��)��ȸ����(du��)�C���M(j��n)��һ�δΛ_��������������ĸȸ���ϣ����������w��С�ߓ��еľ�����������J(r��n)���@�ǿ��w֮�����ߵ�ԭ��ĸ�ԵĐۺ��⣬ʹ�w�B(t��i)��С��ĸȸ���������ಫ����������δ�S�����ӵ��^���У������˳�ߡ��ۺ��☋(g��u)�ɳ��֮“�|(zh��)”��“һ�δ�”չʾ�˳��֮“��”�����������f��“СС����ȸ���^��������ij�ߣ����������n�ʹij�ߡ�Ȼ���@���Ƿ����Ĵ��㌎�f�������Ĵ����@�N��r���һ�N���������Ĵ�
����Ԋ(sh��)�ƣ�‘�۵���������������ȫ������ʹ����ʹ�x�_�ı��ܡ�’”��Ӣ���������ף���ţ��Ԋ(sh��)�W(xu��)�v�ݼ������D(zhu��n)���ԏ��������������W(xu��)�c�Ļ�������122-123�(y��)��������������W(xu��)�����磬1994���_�h��(���t�������塷)���ں�(�����ļt�}����)��С��(���ݺӡ�)��ů(������ǧ�ܡ�)�������źͰ��w��(����·��)������(��������֮�衷)���Ϲ�����(���S����Ρ�)��ü��(��̴���̡�)���{(l��n)Ę(������ƣ�ڡ�)�ȣ����������߅���������������ߡ���Ĭ�ğo�����ڡ�����������v��ؚ���������wҲ��ȱ��ȫ����Ҳǡǡ���@Щ�������ϳ�����ĸȸ��Đۡ��ƺ��⡣
�����_�h���O�������(gu��)�����߶����ܚ������P���������иЄ�(d��ng)���ĵĵ���������ͬ�r(sh��)�־������ܿ���ʹ��ľ���������“������”(���t�������塷)�ָŭ�R��(sh��)�ղ��^���@ʾ��һ�N“����”�ij�ߡ�����ֵ��ע����ǣ�С�f��(du��)��аħ���w���pʬ߀������eֹ�ı��F(xi��n)�������ĉ�?z��i)�������������ʾ��݅��ָ�c(di��n)��;��ʹ“��”�@��һ�N�������Ĕ������c��Ѹ������Ů���O������——“����(f��)���Եģ��Ȅe��һ�й������������(qi��ng)�Ĺ���”����Ѹ����Ů����������Ѹȫ������6������614�(y��)�������������ČW(xu��)�����磬1981��
�������ؿֲ���ȼ���������Ĉ�(zh��)���ͷ�����������“������”Ҳ��“�ʺ�ڰ��ĵ�ĸ”����Ѹ�������L(zh��ng)�c��ɽ����(j��ng)����������Ѹȫ������2������248�(y��)�������������ČW(xu��)�����磬1981���������R�r(sh��)���������������������ڣ��@���`��İ�Ϣ��“������”ԭ����һ��(g��)���ߣ������������һ�δΈ�(ji��n)�g��(qi��ng)���e��(d��ng)���s������һ�ɻ���������־�đ�ŭ����������(f��)��ď�(qi��ng)��������
����������ƣ�ڡ��е����T�[����ҕ��“������”������m(x��)���͏�(qi��ng)����һ��(g��)�ڄڰl(f��)�ҵ������f���ˣ��s����Ī��е������������Үa(ch��n)�����غ�Ů�˱��Ϸִ��M���@��(g��)���vʷ�l(f��)��֮�H����vʷ���µ����꣬�đ�Ī��ԩ�����Qԩ��ꎲܵظ������ܿ��̶�������־������݆������������ԩ���yѩ�����q���^����һ����̴�֮���������V���o��֮�vʷ�c���W�o��֮��������ұ�����ѠT���µij�����W(xu��)���졣�{(l��n)Ę�����vʷ�����ˣ�����ͬ���x������“��”��������“����”�����r(n��ng)�I(y��)��������“�ĸ�”���@��(g��)ȫ��(gu��)Ψһ�Ćθɑ���“���c(di��n)”��һֱ�DZ�����(zh��ng)�������е�“���”��
�����r(sh��)���ĸ��_�ţ�Ӳ�����θ���30����{(l��n)Ę���K��Ҳ������̫�(y��ng)���·N���ˣ������s��Ȼ��(x��)�T������ҹ��“�θ�”��ֱ������ҹ�������Ծ�ĉ�?z��i)�����ȥ���cһ�����ֵ��ϳ��a(ch��n)�ļZʳͬ�w�������{(l��n)Ę�����T�[����Щ����ƨ�ɡ�ֻ��һ���t�Ƕ��������ӵľ��`����(g��u)������ʎ�ڸ��ܖ|���l(xi��ng)����ҹ���꣬����ʎ�Ěvʷ��־�(q��)��Ĺ��ꡣһ��(g��)�����Qԩ�ą�����һ��(g��)�K����Ĭ���λ꣬Ī�Խ����@�ɂ�(g��)“����”——�vʷ�����ߵķ�����ʹС�f�ڌ�(du��)�(y��ng)��������W(xu��)�ăA����“�ɞ������������־�������[��”����ɣ���“����”�c“��”——������ƣ�ڡ��Pӛ���������ČW(xu��)���q������89�(y��)�����������ҳ����磬2009��һ��(g��)��(g��u)����Գ�����W(xu��)�Ŀ��w���ı���
�������������U����������P�µ�ĸȸ��“�����ː۵��(q��)ʹ�^�����Ҫ�īCȮ����ȳ�����С�r����С����ȸ���ѽ�(j��ng)�܄�(d��ng)�˵��C�����е���——һ�аl(f��)�Ը��F���擴����е��О����——�͔�(sh��)�����w�����o���P(gu��n)ϵ�ˡ�”����ᷣ���Փ��ߡ�������������u(p��ng)�ļ�������111�(y��)���麣���麣�����磬1998���Ϲ����ϱ����@��һֻ������“���F���擴�����”��ĸȸ���@λ�c�������Ը��Į���Ů�ԣ��sͬ�����w�F(xi��n)��Գ�ߵ����
�����Ϲ����ϼ��Ǐ�(qi��ng)��vʷ�еı������ߣ����ǚvʷ�ķ����ߡ����ǚvʷ��Ű�����y�ߺͬF(xi��n)��(sh��)���y�ijГ�(d��n)�ߣ��s�����B��(qi��ng)��������������������ֳ���ͳ�M��ķ������О飬ͻ�Ƃ��y(t��ng)Ҏ(gu��)Ӗ(x��n)�������Ժ��������������ϣ����ذ���������еIJ��������x�c���ҡ�Ī�������@λ������ӵ���ͨ�DŮ���@λ���������v���^����ʹ����?j��n)_��ĸ�H���@λ���������ϴ����ښvʷ�����(hu��)�д��K�����^�����_�����ڽ��Ќ������`��Ó���`����o(h��)���v��ͻ���˶����I(l��ng)����]�i�c���d——����/˽���I(l��ng)���������������Ҏ(gu��)���ļ�ͥ�I(l��ng)��ͳʐ���څ��(sh��)�����(hu��)�vʷ�������@ʾ����(du��)���ӷ��µ����ƙ�(qu��n)��������x��
�����҂����ԏ���һ�Ƕȿ���ĸ�H������Գ������ĺ����ԡ���������ԃɷ������������U����c��❓�������IJ������������������ɯ“���`���ص�Ц”���������[�F(xi��n)�Ŀ~���U(xi��n)����Ⱥ�����ɜy(c��)���İ���Ѩ���z���Ļꡣ���������͡��е�Ү�dҲ������❓�J(r��n)���“���ο�냺�Ĵ�ĸ”���෴��“�Ǻ�(ji��n)ֱ�Ǐ����c�ȱ�������ü���ʹ������]��ʧ����Ҳ�]�б�����ֻ��һƬ�����Č�?k��)o����(y��n)�C�Ĝ��ᣬ��(y��n)�C�ЙM������������Ĵ����c������������¶��һ�����۲��ϵij��㣬һ�Ɍ�Ҫؓ(f��)�dȫ�����ěQ���c����”��
�����c���_�����_��“���������”“����Д��c��ǵ�¶”��ͬ���_(d��)·���残����“����ֻ���讋�ױ��棬��Ⱦ����”������“����ֻ�ǘ�(g��u)˼�����ܣ��·���֔(j��n)��(y��n)……�P�P���������”�����^�������������������۶����m�������@�����ܣ�“Ψһ�m��(d��ng)?sh��)����ۣ�����ֻ��Divine(����)��Sublime(���)��”���ڢ�����ᷣ���Փ��ߡ�������������u(p��ng)�ļ�������104-105��106��110�(y��)���麣���麣�����磬1998��
������(d��ng)�vʷ��(z��i)�y�c����IJ����缲�L(f��ng)�E����u��r(sh��)���Ϲ����ς���δ�Լ��ҵķ�ʽ���V�vʷ����(du��)����(z��i)�y����������������־�ͳ��Ʒ�Բ�δ�ʬF(xi��n)�����������������(qi��ng)�����(y��ng)��֮�⡣�����ij�ߣ������ԏ�(qi��ng)����������˲�g�Űl(f��)����ӿ�����������“�Ҡ���”“������”�ǰ���m(x��)��(j��ng)���(y��ng)�����|(zh��)�������c“������”���������“���”Ҳ��ͬ�������c��Ű�ď�(qi��ng)�ȡ��vʷ���L(zh��ng)�Ș�(g��u)�Ƀ�(n��i)�ڵČ�(du��)Ԓ�c���ա�
�������������ij��“���O�ˣ��ͳ��O�ˣ������m(x��)�m(x��)�ģ��c(di��n)�c(di��n)�εεģ����L(zh��ng)�@������������͚��߳��ض����t�IJ�����������(ji��n)ֱ��o����ű��ϵ�ˮ©һ�ӣ�һ��һ�εصε����Ŀ���̎������һ�N�������֎���ʥ�Ŀֲ������飬���nj���Ҧ����֮���^‘�’��ˇ�g(sh��)��;Ȼ��Sublimeѽ!������ʧ���Sublime��ˇ�g(sh��)ѽ!”��ƽ�͡���?k��)o�������c����֮�����������ķ�픣������`����������ĕ�(hu��)�������@�@���������䐂����֮���ߣ�“��(du��)��һ�w���B(y��ng)���أ�������˼���`�꣬�nj�?k��)o�����䣬�����ľ����(hu��)�͛�ӿ���϶룬�c�ڰ�һ���܉�����������c����;����������(hu��)���@���߸��־ã������ˌ�ζ����?y��n)錎�(k��)o�Ǿ��������۶�����(d��ng)�Ǿ�������;��?y��n)��ɽ�ǿɜy(c��)���Ķ���Y�s�o��;��?y��n)�����Ⱥڰ������أ�����������߀Ҫ��(f��)�s׃��һ��”��
�����c�����ļt�}����ͬ��l(f��)���ġ����L(f��ng)��Ҳ��һ������w�F(xi��n)Ī��“��Գ��”���W(xu��)�ľ��¶�ƪ��С�f��(ji��n)������(d��ng)���讋Ұ���L(f��ng)���������(n��i)�ģ���Ȼ볚��һ�ɳ�ߚ���“����”��һ��(g��)�O����ͨ���r(n��ng)�����ڸ�ݕr(sh��)������(j��ng)�ĵغ߳������{(di��o)���澏���Ѷ��n����ͯ���“��”���ܵ�һ�N“������ܻ̻�……���Ҹ��ֺ�ʹ��”����w�����L(f��ng)�E����“����”�������L(f��ng)�����u��“܇��߀ͦ�ںӵ��ϣ�܇�Ӻ�߅�Ǡ����������p��߬��܇�ѣ�����������һ�����������p�������һ����ڵ��ϣ����ϵļ�������һ�ӗl�l�����������”
����Ī�ԣ������L(f��ng)����������ǧ�ܡ�����155�(y��)���Ϻ����Ϻ���ˇ�����磬2005���ڏ�(qi��ng)�����Ȼ֮����ǰ���˟o����һ��(g��)���ߡ�����“����”�n�ϸ��ݵ����|��(n��i)�s���N(y��n)���������������һ��������“����”������ľ���۾�ãȻ����“ãȻ���۾����g”߀�Ѓɂ�(g��)�O��“�е���ů”��“�����Ĺ��c(di��n)”���@���c(di��n)�DZ������ľ��⣬�������ڿ�M�ֱ��в��ܱ������ʹ������c��������һ̎��(x��)��(ji��)ͬ���Ǻ������ǵij�߸е��⻯�����L(f��ng)�^���f�ڻ֏�(f��)ԭ�“������һ�����~����һ�ӱ������������˄�(sh��)”��܇�ϵIJݱ�ϯ��һ�գ�Ψ��һ������ͨ���^����é��“�A��܇����龿p��”���@��ݣ�����ʥ�����Ǹ������~��ʣ���R���~�Ǽܣ�����CȻ�cƽ�o�������������ⲿ�M���ă�(n��i)��������
����������Ĭ�����ߣ���������Ī�Գ�����W(xu��)���������d
��������f��ĸȸ����һ���������o(h��)�rȸ�ĉ��e�Ы@���˳�ߣ���ô����ĸȸ����С���rȸ��?��(d��ng)ʧȥĸ�H�ı��o(h��)���rȸ�������������w�Ƿ������cĸ�Hͬ�ӵ�����?
����Ī��С�f�ĺ��ӷ·�“�rȸ”���������_(d��)��Ī�Եă�(n��i)���挍(sh��)�����M(j��n)���������W(xu��)�����ͨ�����@���f��“����”����ָ��ͯҕ�ǻ���δ��������ʽ�����`��(d��ng)�r�������������������Ī��С�f����ʎ�ڬF(xi��n)��(sh��)߅����“��Ĭ������”��ͨ�^��������Щ���vʷ֮��尾�����F(xi��n)��(sh��)֮�m��������������“���”�������ČW(xu��)�ر��F(xi��n)��
����80������vʷ��e������ʷԊ(sh��)�ΑB(t��i)���t����ҵ��r(n��ng)��Ѿ��D(zhu��n)�Q��ĺ�������“�����L(f��ng)��”�������ļt�}�����Ĺ��¾����@“�L(f��ng)��”��չ�_���������l(xi��ng)��F(xi��n)��(sh��)�е��˂����������mؚ�F�T���sҲ�g����һ�棬�������l(xi��ng)�傐��(�ں�һ�ҵĠ�r)���ИI(y��)Ҏ(gu��)�t(С�F�������F����ͽ����)���������(Сʯ����С�F���;��ӹ�������)�����˹��ں����w���ݣ����M���ۣ��·����x���l(xi��ng)��F(xi��n)��(sh��)�����c���جF(xi��n)��(sh��)֮�g̎��“�ڶ�������”�Ġ�B(t��i)��“���x”�����һ��(g��)��M�殐 �X��ҕ�X���|�X�ұ˴��g��������ͨ��؞ͨ��“�ں�����”���@��Ī�Ԍ�(du��)“����”�����°l(f��)�F(xi��n)��Ҳ��Ī���ČW(xu��)���猦(du��)��Ҋ“���y����”�ķ��ܡ�
����Ī����Մ���@ƪС�f�����W(xu��)��“�ڈ�(ji��n)Ӳ�ġ�������خ������ɷ���߅��ʩ����̓�õġ���ů�ĸ��X�ğ��F���Ƿ���ʹС�f�@��ij�N��ζ��?�����h(yu��n)�h(yu��n)�ض��M(j��n)�����F���ܷ�@��ij�N����ı��F(xi��n)������?”Ī�ԣ��������L(zh��ng)���t�}����������ˇ��(b��o)��1985��7��6�ա����߲����ر�������“��(y��n)��”��“��(ji��n)Ӳ�ġ�������خ������ɷ�”��������“�������{(di��o)”��“̓�õġ���ů�ĸ��X”������̎�����I(y��ng)���һ�N���x���`���h���`��(d��ng)����£����H�ṩ��һ�N�µ�“����”���£�Ҳ���m(x��)���Ї�(gu��)�ŵ����W(xu��)���y(t��ng)������Ҫ���ǣ���ʼ�K����ʾ����Ⱦ��һ�N��(ji��n)Ӳ�ġ��Կ��y���ɫ�ĬF(xi��n)��(sh��)��(ch��ng)����“�F(xi��n)��(sh��)����”�c“���X����”�ɴ˘�(g��u)��������ֵČ�(du��)λ���[��������/�F(xi��n)��(sh��)����(g��)�w/�vʷ����(y��n)��/��������(ji��n)Ӳ/̓�á�����/��ů֮�g�ĽY(ji��)��(g��u)��ì������
������(j��ng)����Ԓ�Z����(d��o)�Ŀ��y���W(xu��)��ע�،����y���¼{�����w�Ԕ������������w�Ԛvʷ�^�����Ϻͽ^��(du��)��־���x�����ܣ����y����������Լ�(x��)��(ji��)�͈�(ch��ng)��������s�p�����ڼȶ����x���a(ch��n)��ϫ@��һ��(g��)ָ��λ�ã�����ָ����λ���ϣ��Wҫ�����Թ�â���@�N���y�w�F(xi��n)��“���W(xu��)�ij��”�����¡����£����Д������С��¾�����100�(y��)���ڰ��A�g���������̄�(w��)ӡ���^��1964����һ�N�����Ե����x���a(ch��n)���c֮��ȣ�Ī�Ե�“���y”ʼ�K�P(gu��n)(li��n)�������������w�Ĉ�(zh��)���ڈ�(ch��ng)�����y�]����������A�M(j��n)��һ��(g��)���w���������ɞ��@һ����ľS�����c�����ˡ�����ֱ���J(r��n)�飺“����Ҫ�ܽ^�Լ����^ȥ�����B(y��ng)�����^ȥ��������^ȥ�����Ծܽ^����һ���ѽ�(j��ng)�������ġ����x�����x�Ė|�������ص@�����峺��ԭʼ���۾������꿴���IJ��������е�ʲô�|�����������������籾���Įa(ch��n)����������κν�(j��ng)�(y��n)��ۙӰ���vʷ�����϶��]�С����е�һ�ж����Q�����ǘӵ��r�ۣ��ȴ��������^�p���A ���|����”���ա�����ֱ�ӣ������ǵ��L(f��ng)��——�x��ʮ����Ї�(gu��)�ČW(xu��)������182�(y��)���ν����g�������������ČW(xu��)�����磬2001���ں���(du��)���(hu��)�ԬF(xi��n)��(sh��)�ľܽ^���[��Ī�Ԍ�(du��)�������x����ķ�˼������Ҫ�����ǣ��ںں�����Dz��Ǜ]��“�κν�(j��ng)�(y��n)��ۙӰ���vʷ������”?�ں��ԛQ�^�ij�Ĭ�ܽ^“��(j��ng)�(y��n)”��“�vʷ”����“��(j��ng)�(y��n)”��“�vʷ”���H�]�Џ���������ʧ������Ҳ��δ�ŗ���(du��)���IJ�������?c��)�С�f��ֵĬF(xi��n)����ֱ�ӌ�(d��o)���˺ں�������(m��ng)�õ��Ɯ硣�挦(du��)�F(xi��n)��(sh��)��(du��)��(m��ng)�õĴֱ����룬�����ں����x“�vʷ”����“��Ȼ”�Ы@���������ڵ������С����x�vʷ�������������ī@�ú͌�(du��)ԭ������Ȼ�Ĉ�(zh��)�ء�����f����һ��(���ǡ�������)�����������������裬�M(j��n)�������������_��һ��韴���������֮������ôĪ�Ԅt�ĺں����Ͼ�l(f��)��һ�N��Խ�Ļ����y(t��ng)����Ԓ���ԭ�����������cԪ?d��)�?/p>
�����ͺں����ƣ���Ĵָ�����еİ��xҲ�ǼҾ�ؚ���ij�Ĭ�ĺ��ӡ����ڞ�ĸ�H�Iˎ�Ěw;�У���һ��(du��)���ص�İ����Ů�ñ����Ĵָ���D��Ĺ��һ���ɘ��ϣ��ҴҶ��^���r(n��ng)�ˌ�(du��)���x�������ͺ��������������ĵ�“��ƤŮ��”�����r(n��ng)�D��(du��)��ʩ��δ�����@ƪС�f��Ѹ��Ϣ��������������ˎ�����T�����Ě��|(zh��)�������鹝(ji��)��“��/����”�ĽY(ji��)��(g��u)�ό�(du��)��ˎ���M(j��n)���˽��b�c“�،�”����֮ͬ̎���ڣ���������(gu��)�����\(y��n)�����ߣ�����Ʒ���������͠����Ы@�ã������x�t����ر����ҏ�ؚ���Ă�(g��)�w������(n��i)����l(f��)����Խ���y��������
�����ژO�ȵĽ^���У����x���n���߿��Ĺª�(d��)�質���(d��ng)�����¸ҵ�ҧ�����Լ��ăɸ�Ĵָ�������r���¹�䁾͵Ĵ������K�s�Ե��ڱ�����·�档�@�r(sh��)��������һ��(g��)���tɫ��С���������w���@�������p�`�����¹�����Ӿ�������¹�����𱻱�������һ�ر���ˮ�������ˎ���w�ܻؼң�Ͷ�M(j��n)ĸ�H�đѱ������h(yu��n)�n���ĸ����p��]�����¹⡢�����Ļ��㡢�����c�¹�䁳ɵĴ����ĸ�H�đѱ�……ƽ�o����ů������I(y��ng)���ͯԒ���Ԋ(sh��)�⣬�mֻ��С�f���һ��(ji��)���F(xi��n)����ռƪ���OС�����������ṩ�ľ�������Ȼʹ���ӛ_�������Ľ^�����_(d��)�������Լ���ĸ�H�����ĘO����
����С�f�Ѓ��͵���Ȯ���s�݅����ĵ�·���ɭ��Ĺ�ء��Dס���ӵ�İ���ˣ��·��������o����ܡ��o����Ó��������Ҋ�����ȵ��ˣ���ͬ�ӈ�(ji��n)Ӳ�ĺ��ĬF(xi��n)��(sh��)����������ľ���ʣ��õ������ӱ��������ĵĽY(ji��)�֣��@Ҳ�·����Ɛ��Ј�(b��o)�������������Ǐı����������h��ĸ質�������ӵ������⼤�l(f��)�����������¹⡢�r�������tɫ�ĺ��ӡ�ĸ�H��������“��”“Ԋ(sh��)��”��ͨ���⺭�������Č�?k��)o����������ů�����ۣ�����һ�N��(n��i)�ڵ����ߵij�ߣ�����������f��“һ��ֲڵ��`�����Ą������J(r��n)��Sublime��һƪ��������������Ȼ��������һ��ˇ�g(sh��)Ʒ���Ƿ���O�ĕr(sh��)��һ�ӿ���ʹ�҂��@�@��ʹ�҂��CȻ��ʹ�҂�������������һ���Ա�֮��ʹ�҂����ߵ��X��”����ᷣ���Փ��ߡ�������������u(p��ng)�ļ�������110�(y��)���麣���麣�����磬1998��
�������ݺӡ�����һƪ�P���c�⾳��������Ѹ����Ʒ��С�f����Ĵָ�����л\������������ɫ�ʵ������Ԉ�(ch��ng)�������خ�(d��ng)���Ї�(gu��)�l(xi��ng)�����ν�(j��ng)��(j��)�Y(ji��)��(g��u)���ճ������龳���^֮��Ĵָ�����Ŀ������ݣ����ݺӡ��ȿ�Ҋ��Ī�Ԍ�(du��)�l(xi��ng)�傐���c�l(xi��ng)�����ν�(j��ng)��(j��)��m�p���Č���(sh��)������Ҋ�����Ե�ī������Į�����ƽ��(ji��n)���������c������������|(zh��)���γ���Č�(du��)��(y��ng)����Į��ľ����Ⱥ���Bͬ��ؚ���͙�(qu��n)��Ϩ���˜�?z��)��H���ߣ��ں��ӿ�ʹ����ŭ���Q�^�ď�(f��)���У��CȻ����һ�ݳ��s����ij�ߡ�
����С�f��һ��(g��)��Ĭ�ĺ���С�������˴��h֧����ӛ��Ů�������ϸߴ�İח�䣬�s���҉��䵽Ů�����ϣ���(d��o)���������������l(f��)����С����������εġ���δ���^����ĸ�H�Ě���;���Hͬ�����ƙ�(qu��n)����־�o�ζ���(ji��n)���Ĉ�(zh��)���ߣ������ݵؑ��PС�����@�Ǹ�ĸ����米�Ѻ��ӵĹ��£�Ҳ��һ��(g��)���߷����c��(f��)��Ĺ��¡�С�����H����(n��i)�Ļě��Ĵ����x�����������H���ѣ���(qi��ng)�M�o���ĉ��֣��߄�(d��ng)����С�ĺ��Ӯa(ch��n)����“һ�N�fԒ”��������С��“ ���Լ�˻���ߵغ�����‘��ʺ!’”Ī�ԣ����ݺӡ��������g����������360�(y��)�����(y��ng)�����L(f��ng)��ˇ�����磬2004��“��ʺ”�Ǻ����f�^��Ψһ��Ԓ���@�����ߵ��������V�����ڸɿݺӵ�������������o����o����Q�^����ʽ������ˌ�(du��)�H��������ĸ�H��“��(f��)��”��
����80���ǰ���ǽ�(j��ng)�������W(xu��)�����x�͕r(sh��)�����ڴ˕r(sh��)�Ěvʷ�����У������������鮔(d��ng)��ʷ��“���y��”���F(xi��n)�������ɱM�ٲ����ԬF(xi��n)����Ԓ�Z������(j��)���������ښvʷ�еı������\(y��n)���A��vʷ���w�ď�(qi��ng)������־��“����”“��˼”“�ĸ�”“֪��”���ČW(xu��)˼���еij��Ʒ��ཨ�����˵����xԒ�Z�c��������Ԓ�Z��ͬ�ĬF(xi��n)��������“����С�f”�Č����Ԓ�Z�Ľ���(g��u)·�����γ���һ�N�e�ӵij�ߕ��������ǵ�“����”ͨ�^�c�����vʷ���µą^(q��)�������Ѓ�(n��i)�ڵ��L(f��ng)���c�f��(y��n)��Ī�Գ�����W(xu��)�c������֮ͨ̎���ڣ������˹����ǚvʷ�е����vʷ�����“߅����”�����Ǻ��ӻ��红�Ӱ㼃�����棬ͬ�r(sh��)������Ҳ�DZ��p����“��(qi��ng)��”�������������^ĸ��Ű������(j��ng)���܇��˵��{(di��o)�o��Ū;�����صؽ��d;�����ܼ������R������Į��Ⱥ���^�������ȟo����o���˄�(d��ng)�vʷ�����vʷ�sҲ��(du��)��������“��(n��i)����”�o���κΡ�“����”�ij��Դ�Ԍ�(du��)��������“��(n��i)����”�Ĉ�(ji��n)�֣���С���α����T����������ƫƫ���c�vʷ�������гʬF(xi��n)�����˲�Ŀ�ij�ߡ�
��������Ī���ČW(xu��)��“����”����vʷ�S��
����Ī���ČW(xu��)�е�ԭ��������������Ԋ(sh��)�⣬��ζ��һ�N���_(d��)“����”�ĕ�����������ڷ�˼��❓“���”Փ���Ļ��A(ch��)�ϣ����½��f��“���”��ᘌ�(du��)�����Կ��W(xu��)�f������(j��)����sublime��grace�քe�g��“�ۂ�”��“����”���Ԍ�(du��)��(y��ng)�Ї�(gu��)�Ą�?c��)����?y��ng)�f�����������˲�ͬ���������J(r��n)�����^sublime(���)�cgrace(��������)���Dz����ݣ��(y��ng)�����ƫ���������|(zh��)����sublime(���)�cgrace(��������)ƫ������Ʒ�����������ĸȸ֮�ɞ����ߣ�ԭ��������Ʒ��“‘���’ֻ�����Ľ^�����ஔ(d��ng)���҇�(gu��)��ˇ���u(p��ng)���õ�‘��’�ֻ�‘�^’��;���@‘�^’�֣��c���fָ��(du��)���������ƣ������fָ�҂���(n��i)������ĸ��X”����ˣ�“��ߵ�һ��(g��)�����c���f��‘���ɜy(c��)����’(immeasurable)��‘δ��(j��ng)�y(c��)����’(immeasured)�������f��‘������’��‘������’”��
������ԭ��������������Ԋ(sh��)�⣬ʹĪ���ČW(xu��)��(n��i)�ڵ�����һ�N�����������ͻ�����Ī�Խ�˾ܽ^���ڵ����x�O(sh��)��������“����”�����O(sh��)���x��
����Ī���ČW(xu��)�������{(di��o)�����֡�������ʽ�������d�£��s����“����”�Ĉ�(zh��)��;����ӵ������ԣ��s���V�T�ǷN������(zh��)�ֵĄ�(chu��ng)ʹ�У����ٳ��صđn�����R(sh��);���������Ű�����y��Ҳ����ر��ǷN��ʹ�ൽ��Ϣ�ij��ظС����ָС�֮������ˣ��������Ҍ�(du��)����“�g��”“��ů”“Ԋ(sh��)��”һ����w�J(r��n);�������ҵ���Ĭ���Ժ�Ц�o�ž�;�������“���g”“��g”��ˇ�Ć�ʾ����ij�N���x�ϣ�Ī���ČW(xu��)������������������w�����F(xi��n)�ı��F(xi��n)����䁏�����(f��)�������c���o���nj�(du��)���w�T��(���I)�c���`�T��(�ª�(d��))�������Դ������w�@���^�c(di��n)���п��죺“Ī�Բ��]�о��������ĸ��X������ħ�á���Ó��Щ�����̦����ë��‘���X’����l(f��)�F(xi��n)��������‘�¼�’�ĘO�F(xi��n)��(sh��)�����|(zh��)��”
������
����Ԋ(sh��)��������ĸ��X�Ϳ�����o���������Kʹ�Ą�(chu��ng)��ӛ���������ǬF(xi��n)��(sh��)����Ҳ�������vʷ�Ĺ��꣺���t�������塷���л�֮����������ƣ�ڡ��������ԩ֮�������Ƈ�(gu��)�����(q��)��֮�������ܡ���Ի�����֮�������S����Ρ��鰲��֮����Ī���ČW(xu��)�y�ښvʷ��ѡ��O�����ԣ�“��Ѹ�ڷ����f�����r(sh��)��������ǿ����Լ����ϵĹ�⡣���ԕ����������g���Кvʷ���L(zh��ng)Ӱ��Ī���@һ����������ʳ�đK�ұ��µĖ|���ÓQ�ˡ��vʷ�����L(zh��ng)�ȳ��^���ҿ������L(zh��ng)�ȣ������d�^�c(di��n)�������l(xi��ng)�����(hu��)�����u�̎̎�@ʾ�ˆμ��Ļֺ�͜�����Ă���”
������
��������֮��Ī��̎���ČW(xu��)�c�vʷ֮�P(gu��n)ϵ�����س�֮̎�����vʷ/�F(xi��n)��(sh��)�{�낀(g��)�w/�����^(q��)��ʹ֮������w�������������������(ji��n)Ӳ�����|(zh��)�ԣ������“���x�O(sh��)��”������֮�Խ���(r��n)�����w˼����`�Ե������c��ʽ�����o��
������(d��ng)����߷���ʥ�ɞ����Еr(sh��)�Еr(sh��)���ČW(xu��)��͑׃?y��u)龫��̓�o���Α��ČW(xu��)�������ӣ����@���g������(hu��)��?sh��)��Ԙ����?hu��)�㐺��������(hu��)�����[������Ҳ��(hu��)��“��Ĭ”�o�ؾܽ^�Ϳ��h���ČW(xu��)�o����׃��(ji��n)Ӳ��(qi��ng)��ĬF(xi��n)��(sh��)�������ṩ�ˁ��Ԅeһ���硢�eһҕ�c(di��n)���^�պ͌�ҕ�����ӟo�����@������������(qi��ng)�w���Ą�������I(xi��n)����Ąڄ�(d��ng)�ɹ������@��(g��)��������������е�ÿһ��(g��)�˶��ǻ����Ǻ��ӣ����ǻ����dz�Ĭ�����[�����ߡ�“С�f��С�f��С��֮�ZҲ����Щ��С�f�f�ɸ��С�����֮��ˣ��o���ǽ�̧���I(y��)��̧���Լ�������”��
��������Ī�������(g��)�w�������ǽ^��(du��)�����ߣ��ČW(xu��)�����ǣ��������鏊(qi��ng)����Ĭ����������“����”���@���棬�ČW(xu��)�P(gu��n)���������x������ʥ���C�^����߱��☋(g��u)֮�r(sh��)���������ČW(xu��)�c“����”һ�𣬔y�����M(j��n)�����c����֮�أ��ن���ʥ��
- �����I(l��ng)���Z�����ֆ��}���팦(du��)�߷���
- Փ�����Ļ��r(ji��)ֵ�������ı���Ϣ����
- ��Ό�(du��)�׃��_չ?ji��)h�Z���ČW(xu��)����
- �w�(y��n)ʽ��������x�̌W(xu��)�Ļ������c(di��n)
- �x��ˇ�g(sh��)Ʒ���Q���Z���Ļ��о�
- �W(w��ng)�j(lu��)�Z�Ԍ�(du��)�ڝh�Z���ČW(xu��)�l(f��)չ�к�Ӱ�
- ���B(y��ng)�h�Z���ČW(xu��)���I(y��)��(y��ng)�����˲ŵ����P(gu��n)��ʩ
- �Z�����֑�(y��ng)���Z������ڿ�Ŀ�
- ���Z�c���Z�̌W(xu��)�Z���ČW(xu��)
SCI�ڿ�Ŀ�
���T�����ڿ�Ŀ�
SCIՓ��
- 2025-01-254��������ԃr(ji��)��SCI�ڿ����]��
- 2025-01-23�Ԅ�(d��ng)���c����ϵ�y(t��ng)4�^(q��)�ڿ�IMA J M
- 2025-01-23��SCI�ܸ��������Щ������
SSCIՓ��
- 2025-01-25ͨ�^�ʸ�!���]6�����ðl(f��)��ˇ�g(sh��)SS
- 2025-01-22�Z�Ԍ��I(y��)�о����m��Ͷ�������ڿ�
- 2024-12-24�����ssci�ڿ���ȫ����������ss
EIՓ��
- 2025-01-24�������eiՓ��ˮƽ
- 2024-12-282024.11��EI�ڿ�Ŀ䛣�����18��
- 2024-12-262025�꼴���e�k���t(y��)�W(xu��)��(gu��)�H��(hu��)�h
SCOPUS
- 2025-01-24scopus�l(f��)�����¸�ʽ��ָ��
- 2024-11-19Scopus��䛵Ľ���������ڿ�
- 2024-05-29scopus�����Щ������ڿ�
���g��(r��n)ɫ
- 2024-11-22��(gu��)�H�����ڿ��l(f��)��Փ�đ�(y��ng)ԓ��ʲô
- 2024-11-22��(gu��)�H���Ľ̎����ڇ�(gu��)�H�����ڿ��l(f��)
- 2024-11-22��(gu��)�H�����ڿ��u(p��ng)�Q���J(r��n)��
�ڿ�֪�R(sh��)
- 2025-01-24�ڿ��κˡ��p����ʲô��˼
- 2025-01-23���н�ͨ�l(f��)չ���P(gu��n)�����m��Ͷ����
- 2025-01-21�������w�W(xu��)�����ڿ��ϼ�
�l(f��)��ָ��(d��o)
- 2025-01-25Փ��Ͷ��ǰҪ�z����Щ��(n��i)��?
- 2025-01-24�t(y��)�W(xu��)�о����Į��I(y��)Փ���x�}�v��
- 2025-01-23�����Ļ������Փ���īI(xi��n)39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