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紀錄片創作中拍與被拍的關系
時間:2020年02月07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在紀錄片創作中,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備受爭議的話題,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至關重要。本文以大量的紀錄片為案例展開分析,旨在探討紀錄片創作中拍與被拍的關系。筆者認為,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可以建立平等和信任的關系、合作關系“、分享”的關系,這種方式一方面可以拍攝到真實、自然的影像,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現道德爭議。
關鍵詞:紀錄片;平等;信任;合作;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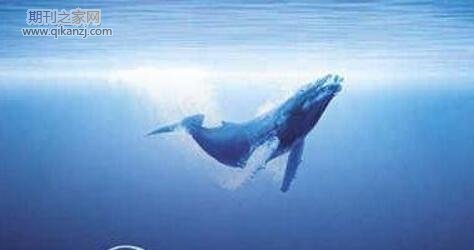
相關論文范文:數字影像技術在行業博物館的應用
摘要:專業特色鮮明的行業博物館在建設過程中,線下實體場館和線上虛擬展館綜合應用以靜態圖片、動態圖像和虛擬影像等主要數字影像技術,可以有效提升其記錄、研究和傳播行業歷史文化的效率。但目前該領域相關應用發展不夠均衡、方式簡單陳舊、移動互聯網推廣乏力。行業博物館自身應當加強相關課題研究和綜合投入,探索與社會合作開發數字影像應用模式。行業主管和政府綜合管理部門要加強頂層設計,在資金支持、平臺建設和激勵引導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隨著攝像設備的普及,紀錄片創作的門檻降低,紀錄片成為我們關注社會、表達自我的一種新的方式和途徑。很多文字工作者開始轉變創作方式,用影像,甚至很多農民都開始用攝像機、手機記錄自己和周邊人的生活。近年來,紀錄片的數量比以往增加了很多,但是很多問題也隨之而來,其中受爭議最大的就是道德問題。那么,紀錄片導演在記錄影像時該如何處理與被拍攝者的關系?拍與被拍到底應該是怎樣的關系呢?
一、平等和信任的關系
首先,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拍攝者既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俯視、歧視甚至歪曲對方的生活,也不能仰視、夸大其詞,而是從平視的角度客觀地審視被拍攝者。其次,拍攝者要尊重被拍攝者,在尊重的基礎上被拍攝者才會對拍攝者產生信任,進而消除戒備心理,在鏡頭前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吳文光導演的《江湖》記錄的是一個大棚演出團的生活,為了拍攝到被拍攝者最真實的一面,他選擇與他們在非常簡陋的環境中一起生活。徐童在拍攝《算命》時,搬到燕郊與被拍攝者做了很長時間的鄰居,充分地了解他們的生活。雅克·貝漢在拍攝《鳥的遷徙》時,為了讓鳥不抵觸拍攝團隊,他們花了半年多的時間與鳥共同生活。
為了和被拍攝者建立起平等、信任的關系,很多導演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不斷地進行探索和嘗試。有了這些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我們才能看到紀錄片中非常震撼人心的、真實的畫面。例如,周浩的《書記》中,縣委書記在鏡頭前正常地辦公,絲毫不受攝像機的干擾;徐童的《老唐頭》中,被拍攝者對著鏡頭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的經歷,非常自然;吳文光發起的村民影像計劃的作品《我的村子》中,拍攝者王偉拿著DV在村子里到處溜達,拍攝村民們的日常生活,村民們在鏡頭前都非常放松。所以,要想拍到被拍攝者最真實的一面,拍攝者必須設法讓自己融入到被拍攝者的生活中,從他(她)的視角出發進行觀察和思考。
二、合作關系
很多紀錄片導演認為,在創作結束后他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聯系就中斷了,獲得的一些獎項只屬于他一個人,他覺得他是在利用被拍攝者。周浩的《龍哥》的另一個片名是《利用》,寓意他和被拍攝者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但是片中的被拍攝者是很樂意被拍攝的,龍哥行蹤不定,拍攝曾中斷過幾次,每次都是他主動聯系周浩,我們在該片中看到的是他們之間平等的關系。導演或許想表達的是龍哥在鏡頭前有表演的成分,他的很多言行不一定是完全真實的。利用與被利用這個問題也困擾了吳文光導演很多年,近年來他將鏡頭由外向內轉向自己,拍攝自己的生活,改變了創作方式。但是從客觀的角度講,只要拍攝紀錄片,就會存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系,這是不可避免的。而對紀錄片來說,它是有多重屬性的,例如,歷史題材的紀錄片和記錄人類文化的人類學紀錄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很多反映社會問題的紀錄片能夠形成積極的作用、推進社會進程。
比如,1938年,導演伊文思冒著生命危險記錄我國抗日戰爭的真實經歷,后來這部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在法國和美國放映,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的抗日戰爭得到了全世界的聲援,這些寶貴的鏡頭也成為反映我國抗戰史的重要資料。周浩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也多是關注當下的很多社會問題的,《日子》記錄的是鄉村留守老人的現狀,《厚街》關注進城打工人員的生活境遇,《急診室》記錄急診室醫生的日常工作,反映中國的醫療現狀,這些問題只要被提出來才會引起關注。
“紀錄片能讓你更好地觀察這個世界,平和地去看待事情的發展,這對促進人和人之間的了解,減少相互的摩擦,都是有幫助的……比如說,《急診》講急救室的故事,有的觀眾會說,他們之前非常極端地看待醫患關系,但其實醫生非常不易。如果他能坐下來看90分鐘片子,如果他能得出這么一個結論,這就夠了,那我的片子就發揮了某種作用。”①因此,只要被拍攝者了解拍攝的意圖、同意拍攝,同時雙方是平等的關系,就不存在利用與被利用,而拍與被拍應該是合作關系,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一種責任。比如,克勞德·朗茲曼的紀錄片《浩劫》反映的是二戰中猶太人被屠殺的史實,導演找到了幸存下來的當年在集中營當理發師的猶太人維巴,維巴在回憶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時講到一半就痛苦得不能自已,拒絕再講下去,但是導演要求他必須講下去,“對于《浩劫》這個作品來說責任大于人情”②。導演認為維巴有義務把真相說出來,因為這對猶太人非常重要,他不講出來這段歷史就會被遺忘。
三、“分享”的關系
1999年,張麗玲的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播出后在社會上深受好評,但是沒多久該導演就被《角落里的人》這集中的主角之一史國強以侵犯名譽權等理由告上法庭。據史國強稱,他曾要求張麗玲在影片上映前給他看素材,并要求導演在后期制作時遮擋他的臉部,但這些要求都沒有被滿足。2008年,徐童的《麥收》在一些高校和電影節上放映后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片中的女主角妞妞(化名)是個在北京打工的發廊女,片中出現了妞妞家庭的詳細地址,導演跟隨妞妞去她家拍攝時,她的父母稱呼的是她真實的名字——牛紅苗,這就等于妞妞的個人隱私完全被暴露了。在該片放映后,妞妞和她身邊的姐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是要求徐童停止播放本片。但是幾年后,筆者發現在一些網站上竟然能下載該片。在自媒體如此發達的當下,試想一下,如果認識妞妞還有片中其他發廊女的人看到了這部紀錄片,后果會怎樣?會對她們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紀錄片的隱私問題一直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如何保護被拍攝者的隱私權一直沒有定論,很多學者認為這個尺度的把握要靠拍攝者的良知。
筆者認為,與被拍攝者分享影像是一個可行性很強的辦法。1954年,人類學家讓·魯什在制作紀錄片時將拍攝的影像放給片中的主人公看,他們在觀看后對影片發表了意見。讓·魯什覺得他們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是以往的紀錄片創作中沒有出現過的,于是他提出了“分享”的理念。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很多國家在創作一般紀錄片時開始使用分享人類學方法,其目的是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實,透過現象看到一種文化的本質。除了實現人類學意義上的真實,分享素材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被拍攝者,對于被拍攝者來說,他(她)在回看素材后有權力決定保留或者刪除哪些素材,而這種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侵權問題。
四、結語
隨著自媒體的普及和手機攝像功能的不斷升級,紀錄片創作不再是精英行為,來自民間的影像記錄會越來越多,但是拍與被拍是一種無法改變的關系,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只有處理好拍與被拍的關系,才能從根本上規避道德甚至法律問題,才能拍出真實的、鮮活的影像。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