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安全視域下南海漁業糾紛探析
時間:2019年04月03日 分類:農業論文 次數:
[內容提要]南海周邊國家經濟發展依賴海洋資源,地緣政治深受海洋影響,漁業糾紛往往成為海洋資源爭奪的重點。由漁業糾紛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沖突、國家對立,已成為關乎南海海域安全與穩定的突出議題。資源匱乏、民族情緒、領海爭議等原因,推動南海相關國家對漁業糾紛進行安全化操作,激化南海漁業糾紛。在此背景下,協商建立漁業合作機制為南海資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臺。漁業合作機制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將會不斷彌補國家間的信任赤字、推動國家利益的聚合、加快非傳統安全治理的進程,而漁業合作機制也將成為綜合安全治理的著力點。
[關鍵詞]南海,漁業糾紛,資源安全,安全化,安全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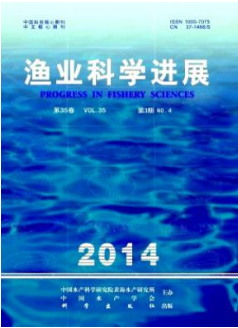
近年來,隨著亞洲各國海洋權益觀念的空前提高,各國對于海洋資源爭奪愈演愈烈。尤其是海底石油資源、漁業資源等海洋資源關系國計民生,成為國家間利益爭奪的主戰場,海上資源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東南亞國家大多是沿海國家,地理位置依傍海洋,漁業捕撈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方面倚重海洋漁業資源。
因此,南海漁業糾紛成為海洋資源爭奪的核心議題,由漁業糾紛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沖突、國家對立,業已成為關乎東南亞安全與穩定的突出議題。由于爭議方大多是世界上的漁業經濟大國或區域實力強國,因而漁業資源爭奪更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在當前的資源安全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對資源安全研究的對象大多是對國家主權和軍事安全有重要影響的水資源、石油、天然氣等,或將其與國家治理失靈聯系起來,或探討因為資源爭奪而爆發的國家間戰爭,或者是將資源安全與資源沖突結合起來進行分析。①
對于漁業沖突的研究,既有學術研究從不同角度提供了分析問題的框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研究梳理,但較少有研究從安全化的角度對南海漁業糾紛進行詳細的分析以及梳理其升級過程。②因此,從安全化的角度對南海漁業糾紛進行探究,在中國同東盟國家積極推行“南海行為準則”案文磋商的背景下具有現實意義。③
一、資源安全對地區安全再定義
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安全”的定義一直不很成熟,然而即使這種不成熟的“安全概念”也長期被現實主義“國家安全”話語所主導。④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超級大國之間逐步實現核平衡,經濟與環境威脅日益受到關注,安全的初始定義得以擴展,國際安全研究議程開始向軍事—政治之外擴展。⑤1983年,國際關系學者理查德·烏爾曼率先提出了“非傳統安全”概念,將貧窮、疾病、資源沖突等內涵均納入安全的范疇之中,強調非軍事威脅在未來安全議題中的重要性。①
隨后,兩極格局的瓦解以及世界范圍內全球化的擴展,使“安全”的定義有所更新。包括恐怖主義、種族危機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斷凸顯并形成傳統安全領域外的新安全挑戰。與傳統安全相較,非傳統安全因其豐富的議題以及模糊的邊界而更加難以定義。但總的來說,仍然可以勾勒出其與傳統安全之間的界限與區別:第一,傳統安全主要研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安全互動或安全問題,而非傳統安全研究主要指向“跨國家”的安全互動,以及國家內部產生的安全威脅;第二,傳統安全研究的是“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安全互動,并把國家視為主要威脅,非傳統安全著重研究“非國家行為體”所帶來的安全挑戰;第三,傳統安全側重安全議題中的軍事安全,非傳統安全則研究的是“非軍事安全”對國家和國際安全造成的影響;第四,傳統安全更傾向于將“國家”視為安全主體,而非傳統安全則將“人”視為安全主體和實現安全的目的。②
非傳統安全研究對傳統安全研究的核心突破之一,在于從水平層次上將安全議題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等新的安全領域。因資源沖突而引發的安全議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成為非傳統安全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理查德·烏爾曼在其《重新定義安全》中預言:“在未來幾十年,因為領土而爆發的沖突會減少,但由某些基本商品需求的增加而出現的供給不足可能會導致資源沖突更加激烈,這種沖突往往以公開的軍事力量對抗為表現形式。”③1982年以來,資源對國家內部沖突以及國家間沖突的爆發、延續和沖突烈度產生了戲劇性的影響。④
而漁業資源更是因其對于沿海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作用而成為海洋資源沖突的根源之一。因此,本文首先指出漁業資源在資源安全問題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進而以東南亞漁業糾紛為切入點,采用領域和層次相結合的綜合分析法,對由漁業資源爭奪而引起的沖突如何升級成為影響地區穩定的“存在性威脅”進行詳細論述,進而說明資源安全已經成為一個影響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核心因素。
(一)資源安全:更新安全的定義
資源是指一切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東西。⑤具體而言,“資源是指由人發現的、有用途和有價值的、出于自然或未被加工的狀態的物質及其能量,人類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能產生經濟價值,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的福利”①。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正在面臨迅速枯竭的風險,部分資源枯竭的速度已經超過了人類可以承受的程度。對于關鍵性資源的供給爭奪,在冷戰結束后取代了意識形態沖突,成為國家之間進行斗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于獲取資源的居安思危,使得“資源安全”概念成為非傳統安全研究新的關注點。資源安全被定義為“以可承受的價格供應自然資源的能力”②。資源短缺和資源過剩之間的矛盾,是引起全球資源沖突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而對資源安全的研究大多關注與國家安全、地區沖突之間的密切關系石油資源、礦產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等。
有史以來,因為資源利用相關的沖突甚至戰爭是人類社會的重要命題。隨著冷戰的結束,美蘇及其陣營下進行的意識形態競爭幾乎完全消失,各國不再以東西方的對立為主要關注點,追逐和保護稀缺資源成為國家的安全功能之一,這對于資源安全問題的中心化發展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由于資源的供給枯竭,政府則會設法最大程度地謀取有爭議地區和近海的資源儲藏,國家間由此而產生的沖突也如影隨形。
尤其是當資源的儲存地被兩個或更多的國家分享、或資源位于有爭議的邊界地區以及近海經濟區時,為爭奪資源而發生沖突的危險也會隨之增加。③這種資源沖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資源在沖突中占絕對主導地位;另一種盡管資源不是主導原因,但是在沖突中起到了催化作用。④當矛盾無法調和,資源沖突會以國家對有爭議的邊境地區或專屬經濟區的領土爭端的形式出現,并上升為地區性權力斗爭。如1994年挪威和冰島之間的“鱈魚大戰”,而俄羅斯和日本之間的漁事摩擦的直接后果就是俄海軍軍艦幾次向日本漁船開火并導致了兩國間的外交抗議。⑤
從經濟、資源和社會角度而言,漁業資源對南海周邊國家至關重要。漁業資源是南海周邊國家經濟收入以及國民生計的重要來源之一。豐富的漁業資源大部分集中在世界糧農組織所劃定的世界主要漁區第36區以及37區的范圍之內。①每年南海地區的捕魚產量超過全球捕魚量的10%②,南海海域潛在漁獲量為6.5×106噸至7×106噸。其中,水深500米以內淺海陸架區(含北部灣)水域內漁業資源最為豐富,潛在捕魚量為5×105噸,占整個南海漁獲量的80%以上。③
而該地區也是中國、越南等周邊國家漁業沖突與合作進行最為密切的地區。1970年后,隨著各個國家逐漸建立起海洋專屬經濟區,南海漁業資源被人為分割,漁業糾紛開始變得更加頻繁,暴力沖突也不斷升級④,漁業資源分配與資源安全治理成為南海周邊國家共同面對的海洋治理議題。
(二)漁業糾紛:發展面臨的困境
漁業沖突被定義為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基于各自的經濟和社會動機,在相同海域內對漁業資源的分配與獲取產生的矛盾與糾紛。⑤安東尼·查爾斯(AnthonyT.Charles)將復雜的漁業沖突分為四種相互聯系的類型:漁業管轄范圍糾紛、管理機制問題、內部分配問題以及外部分配問題。在這些不同類型沖突的背后,是各種漁業行為體所追求的具有差異性的目標。分別以“資源保護”、“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為目標的行為構成了三種不同的范式。這三種相互沖突的范式共同組成了分析漁業糾紛議題的三角框架。⑥
隨后,伊麗莎白·班尼特等學者在此基礎上引入了外界行為體在漁業糾紛中的作用,將漁業沖突更新為五種類型:第一種沖突指向“誰擁有漁業資源”,也就是指向在固定海域漁業資源的捕撈權;第二種沖突指向“漁業資源如何被控制”,也就是指向在資源管理機制中出現的沖突與糾紛,包括漁業資源分配問題以及漁業資源合作問題;第三種沖突指向“漁業資源使用者的關系”,例如手工業個體漁民與工業化捕魚企業的關系;第四類沖突指向“同一生態環境中漁民與其他資源使用者之間的聯系”,通常發生在漁民與同樣依靠水資源而生存的從業者之間,由資源沖突而爆發的爭端;第五類沖突指向“漁民與非漁業議題之間聯系”,主要是指由于經濟、政治變化等因素引起的沖突。①
南海漁業沖突已經成為南海沖突中的核心安全威脅之一。非法捕魚頻頻發生,遠洋捕撈與海盜問題相聯系,周邊國家海上民兵政策的推動都使得漁民的遠洋捕魚行動被賦予了更多政治性含義,而發生在爭議海域的漁業沖突更是成為南海問題相關國家宣示海上主權、展示國家實力的角斗場。以爭奪漁業資源為本質的漁業糾紛被安全化為一場政治博弈,推動著地緣政治環境的不斷惡化,甚至成為大國戰略對弈的新熱點。②
二、多方驅動的漁業糾紛成因
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南亞海上漁業糾紛逐漸增多,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重大隱患。其中的原因,既包括資源衰退而引起的供求矛盾,也包括領海爭議所引起的執法權沖突,而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也不斷激化漁業糾紛。漁業資源對于東南亞國家的重要作用,使之成為東南亞國家在海洋權益爭奪中的重要利益訴求,而合作機制的不完善使得地區合作難以有效進行。
對于大部分東南亞國家而言,漁業經濟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關乎國計民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海洋漁業資源的日益稀缺,使得東南亞國家已經將其視為本國海上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在國家目標的驅動下,國家行為體更加傾向于采取有利于增加捕魚產量和漁業收入的發展方式,這就造就了在資源相對有限海域中大量漁船被允許出海捕撈,漁業糾紛的發生不足為奇。③
(一)難以平衡的供求矛盾
盡管漁業糾紛頻發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共同構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南海周邊國家漁業需求的大幅增長與漁業資源衰減之間的矛盾。漁業產品是世界食品領域貿易程度最高的領域之一,預計有78%的海產品進入國際貿易競爭,而南海海域所在的西部太平洋地區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漁業產品出口地區。中國、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漁業生產國。根據東南亞漁業開發中心的數據統計,東南亞國家的漁業總產量已經達到了4222萬噸,其中遠洋捕魚量為1665萬噸,占整個東南亞漁業產量的40%,世界海洋捕魚總量的20%,其中南海海域的捕魚總量占據半壁江山。
與此同時,相較于水產養殖和內陸漁業捕撈而言,遠洋捕魚帶來了更大的經濟效益,海洋捕撈帶來的經濟效益占漁業捕撈產值的50%來自于遠洋捕撈。①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以及海洋捕撈技術的不斷發展,海洋漁業資源面臨著嚴重枯竭的危機。沿海各國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思維,在進行海洋漁業捕撈的過程中往往優先考慮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資源的可持續性發展。在過去的15年中,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捕魚總量增長了將近60%,預計到2050年,東盟國家的漁業消費總量將達到4710萬噸。②
而長期的過度捕撈使得南海地區漁業資源產量逐漸減少。南海地區14%的魚類種群被估計為按生物學不可持續的方式捕撈以及86%的魚類種群被完全捕撈或低度捕撈。③目前,除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附近部分漁場及部分海域還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外,東南亞其余海域傳統漁場的漁業資源數量和質量相較20世紀中葉都呈現大幅度下降狀態,南海近海海域幾乎無魚可捕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三、結語
漁業資源既是國家沖突的誘發因素,同時也有可能推動地區資源安全合作。如果不能妥善地處理資源引起的糾紛和爭端,地區安全極有可能陷入一個混亂的局面當中。如何在當前的國際社會的框架下對國家間發生的資源沖突做出相應的去安全化努力,越來越考驗各國的外交應對能力。但漁業資源的合作、海上資源安全的治理道路漫長,不可能一蹴而就。漁業糾紛是近年來資源沖突的一個突出體現。
因漁業資源而引發的沖突甚至戰爭已經成為地區安全需要面對的新議題。審視世界各地的漁業合作,也是一個在利益競爭中不斷磋商、在談判中互相妥協的過程。因此,應對南海漁業糾紛,應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逐漸建立沖突應對機制和協商治理機制,為推動資源安全治理和地區和平穩定邁出堅實一步。
相關期刊推薦:漁業科學進展(雙月刊)是由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和中國水產學會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