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與有機農業財稅扶持政策研究
時間:2017年06月15日 分類:農業論文 次數:
這篇農業工程學報投稿論文介紹了社會福利與有機農業財稅扶持政策研究,論文力圖從理論上分析這一問題,為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找到更為合理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論依據。論文分析了政府扶持政策,認證費用補貼應該采取局部補貼,同時對有機農業實行免稅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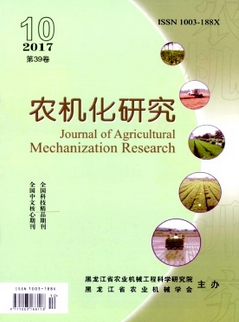
關鍵詞:農業工程學報投稿,有機農業,社會福利,財稅扶持
有機農業是在“化學農業”“石油農業”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的背景下于20世紀70年代產生的,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獲得了較快發展。根據瑞士有機農業研究所(FIBL)和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合會(IFOAM)發布的研究報告,全球有機農業用地從1999年的1100萬hm2增長到2014年的4370萬hm2,有機市場規模從152億美元增長到800億美元[1]。這期間,發達國家普遍加大了對有機農業扶持的力度。美國2002年以來,陸續實施了資助有機農業研究、分攤有機認證成本與有機轉型成本等政策,以擴大有機產品供給[2]。歐盟有復雜的補貼標準,包括有機農業轉換期補貼、維持補貼、認證補貼、農業環境補貼等[3]。
其他如澳大利亞[4]、日本[5]、德國[6]和瑞典[7]均有扶持政策。農業補貼是世界各國比較常見的產業扶持政策,其理論依據來源于農業的非均衡理論、農業的弱質性、多功能性等[8]。政府對有機農業進行扶持,除了常規的農業補貼理論外,主要有兩方面的理論,一是新興產業理論,對新興產業進行扶持是產業結構政策一個重要內容;二是基于有機農業外部性,外部性帶來了市場機制失靈,因此需要發揮政府的干預作用,其核心是矯正市場機制的失靈。謝玉梅等認為歐盟長期以來對有機農業生產發展的直接補貼及配套服務措施有效地解決了有機農業發展的外部性問題[9];尚長風等認為有機農業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現在土壤養護、水資源保護、大氣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農產品的安全等[10];政府基于外部性對有機農業進行財稅扶持帶來的社會福利變化、政策效果差異的研究相對缺乏。
一、有機農業外部性與社會福利損失
按照有機農業的一般定義,即“按照有機農業的生產標準,選擇優良生態環境的基地,在生產過程中不使用或基本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肥料、農藥、生長調節劑、畜禽飼料添加劑等物質,不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獲得的生物及其產物,防治工業“三廢”的污染,實施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技術的農業生產體系”[11]。顯然,有機農業是具有“外部之外,還存在“社會收益”。“一件產品的私人邊際收益(MPB)是用它提供給購買者額外的滿意程度來衡量的,社會邊際收益(MSB)是社會從生產單位的產品中得到的額外滿意程度”[13]。
因此,有機農業存在邊際社會收益大于私人邊際收益的現象。這樣單純依靠市場配置資源會導致產出水性”的產業,“外部性”是福利經濟學一個重要概念。從理論上看,發展有機農業將面臨由于“外部性”帶來的市場機制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問題。“外部性”是指“生產和消費行為可能會強加給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外的人以成本或收益”[12]。由于不使用或者基本不使用化肥與農藥從事生產,有機農業生產過程顯然可以減少對大氣、水、土壤的污染,可以減少碳排放。
相應的有機農業提供的產品除了“私人收益”平低于最優水平,從而社會福利不能實現最大化。如圖1[13]私人邊際收益、邊際外部收益、社會收益、私人成本分別為MPB、MEB、MSB、MSC,如果單純依靠市場,均衡產量為Q0,但考慮正的外部收益,社會最優產量為Q1,在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后社會福利損失為三角形ABC的面積。
二、政府扶持政策分析
由于有機農業正的外部性,這為政府對該產業進行政策扶持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對有機農業產業進行扶持逐漸成為一種共識,同時產品要能按照有機產品標準進行銷售必須經過認證,這構成了有機產品成本的一部分。這樣政府對有機農業進行扶持有這樣幾種方式,一是財政補貼,即政府直接補助廠商使得產品能夠實現相對較低的價格;二是稅收優惠,即政府通過低稅率或者零稅率支持有機農業;三是認證費用補貼,即政府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認證費用;四是技術創新支持,即政府通過各種形式支持技術創新,甚至直接提供一些通用技術研發經費。為了說明問題的簡化,假定有機農業的邊際成本保持不變(邊際成本遞增情況不影響本文的分析結論,另外邊際外部收益MEB的大小不影響本文的分析結論),于是有:
(一)財政補貼
假定生產者按照不變的邊際成本MC=P1提供產品,在Q1產量水平時,全社會經濟福利=梯形A′CBP1的面積,如果產量增加到Q2,政府需對每一單位產品實施補貼為P1P2,此時產品價格降低為P2,政府補貼數量為P1B′DP2,消費者剩余增加額=P1B’DP2+CB′B面積,生產者剩余減少額=P1B′DP2,因此社會福利凈增加為三角形CB′B的面積,這樣通過政府干預克服了外部性帶來的效率損失從而實現了社會福利最大化;如果采用部分補貼,政府需對每一單位產品實施補貼為P1P3,產量增加到Q2′,同理社會福利凈增加為四邊形CBFE的面積,顯然,政府補貼的效果呈現出邊際遞減現象(圖2)。
(二)征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如圖3,由私人邊際收益MPB決定的均衡產量為Q1,考慮到外部性,則全社會經濟福利=梯形P1DEA′的面積,現在政府對產品征稅,假定每一單位產品的稅額為P1P2,征稅后產品的供給價格提高到P2,政府獲得的稅收為P1P2BC,如果不考慮外部性,社會福利損失為三角形BCD的面積,如果考慮外部性,征稅之前全社會經濟福利為A′EDP1,征稅后全社會經濟福利為梯形P1CFA′面積,考慮到政府獲得了稅收,社會福利損失為梯形CDEF面積,大于不考慮外部性情況下的社會福利損失,考慮外部性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損失增加了四邊形BDEF面積,這說明因為外部正效應,征稅后的社會福利凈損失遠遠沒有外部性情況,如果對有機農業征稅將帶來較大的社會福利凈損失。
(三)認證費用補貼分析
假定初始均衡的產量為Q1,如果考慮認證費用,則供給線上升為P2=MC+CC,產量下降為Q2,如果政府補貼全部認證費用,產量又恢復到Q1,此時認證補貼為矩形P1P2FG的面積。顯然,如果不考慮外部性,此時將會帶來三角形EGF的凈福利損失,如果考慮外部性,則會增加梯形BDFE的凈社會福利;如果政府補貼部分認證費用,則供給價格上升到P2′,此時社會福利凈增加BCHE。顯然,政府補貼認證費用的對社會福利增加的邊際效果是遞減的(圖4)。不僅如此,政府對認證費用進行全額補貼有可能會帶來社會凈福利的減少。在圖5中,假定MSB、MPB的位置保持不變,MC+CC位置保持不變,MC+CC與MSB相交于I,過I點做一橫軸的垂線與MPB相交于K,則政府對認證費用的補貼的上限為矩形P2IKP0的面積。顯然,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產品的邊際成本為MC,如果政府對有機產品的認證費用進行全額補貼,即矩形P2MRP3的面積。則均衡產量固然可以擴大到Q3,但帶來了三角形IMN社會凈福利的損失。
(四)技術支持政策
有機農業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生產成本高,如果通過技術進步降低了生產成本,則有機農業的市場需求潛力將會大大增大,社會福利也會大大增加。顯然,如果政府支持技術進步降低了生產成本,邊際成本從MC降低到MC′,產量從Q增加到Q′,因為技術進步是一次性投入,這樣在不考慮技術研發投入的情況下,社會凈福利的增加為梯形PBB′P′面積,顯然政府降低生產成本的技術進步可以較好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圖6)。不僅如此,有機面臨比常規農業更高的技術難度。例如由于不使用或者基本不使用農藥,因此對病蟲害防治的難度大,這均決定了有機農業技術研發投入遠遠高于常規農業,通常企業很難承擔;加之技術進步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外部正效應,這決定了有機農業技術進步要更多依靠政府投入來實現。這在一些發達國家得到證實。美國重點扶持研究項目,2014年農業法案對有機農業研究補貼支出達到1億美元,是2002年的67倍。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將有機產品的市場擴大到社會福利最大的水平,需要較高的持續性的財政資金投入,且社會凈福利的增加十分有限,因為外部性對有機產品征稅會扭曲市場機制帶來較大的社會福利凈損失。
顯然,有機農業的正外部性為政府補貼有機認證費用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從效率角度看,政府對認證費用的補助不一定是全額的,即使政府補助可以增加社會福利,但其邊際效果是遞減的。因此,在財政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對認證費用的補貼可采用部分補貼的方式;政府支持有機農業更為有效的辦法是對企業技術進步提供支持,尤其是重點支持企業降低生產成本。
從我國當前情況看,發揮財稅手段對有機農業的支持不能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發達地區的做法,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建議財政支持主要用于支持有機農業的技術研發,政府可以支持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對有機農業生產的一些通用關鍵技術進行攻關,例如有機肥料技術、利用生物多樣性控制作物病蟲害等,同時對有機農業企業進行生產技術攻關提供補助。其次應該制定對認證費用補助的實施辦法,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建議實行認證費用部分補助;政府財政對農業的貼息貸款支出也要重點支出企業的技術創新;從稅收角度看,建議對有機農業企業實行免稅政策。
作者:康丕菊 彭志遠 單位:云南財經大學 國際語言文化學院 云南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推薦閱讀:《農機化研究》近年來,本刊曾多次受到國家農業行政管理部門和國家有關學術組織的表彰與獎勵,曾獲1994年、1996年、1998年、2000年全國優秀農機科技期刊獎和2002年全國農機優秀科技期刊一等獎;并自1988年起,連續5屆被國家權威部門確認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