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惰性的沉迷與優雅的破碎中尋找絕美
時間:2021年08月04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景象奇觀”“游蕩中窺視”和“反情節”,是索倫蒂諾在電影《絕美之城》中對羅馬城幾種核心的表達策略.索倫蒂諾對21世紀羅馬上流社會形形色色的描繪鑲嵌于羅馬這座“永恒之城”,形成了獨特的歷史和現實交融與制約的奇景,在費里尼之后再次點燃了對“美和虛無”的探討.索倫蒂諾在影片中一邊流露出對貝盧斯科尼時代的意大利當代文化中大行其道的聲色犬馬和頹廢墮落的自我反思,一邊卻又對“何為絕美”仰之彌高求之不得而迷茫.
關鍵詞:羅馬文明;保羅·索倫蒂諾;奇觀;懷舊;審美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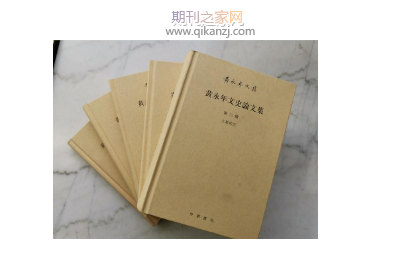
1永恒的羅馬和陰影中的羅馬人
狂歡艷舞的男男女女當中主人公杰普緩緩步出人群,“我注定是多愁善感的,我注定是一個作家,我注定是杰普·甘巴德拉.”杰普緩緩地點上一根煙如此說道.在眾人的麻木當中,也許只有尋找到一個多愁善感的、因年齡而需要去思考死亡的主人公,才能去發現當代生活的本質.
《絕美之城》中的杰普作為向導,帶領觀眾去探尋、窺視并領略當代羅馬社會的荒淫無度和虛偽潰爛.羅馬意味著什么,羅馬走向何方,是索倫蒂諾始終懸置在影片所有場景之上的感嘆.杰普不僅僅是向導,他本身就是羅馬當代生活的縮影,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杰普就是羅馬.杰普是一位年少成名的作家,24歲那年就憑借一部中篇小說《人體器官》享譽意大利乃至歐洲文壇.
在之后的40多年當中他再也沒有創作一部小說,而是以花花公子的生活揮霍自己的才華和時光,沉溺于過量的、無休止的聚會狂歡之中.20多歲的時候杰普從那不勒斯來到了羅馬,憑借自己的才華躍進上流社會,很早就成了他年輕時所期望的“社交名流之王”.但杰普畢竟是“多愁善感”的羅馬知識分子,在步入老年的時候他毫無頭緒地陷入了身份危機和價值危機當中.他能言會道、言辭犀利、憤世嫉俗又四通八達,但在65歲之后決定不再多做任何自己無法認同的事,他決定要解決困擾自己四十多年的問題:尋找絕美.
導演借絕美的概念不僅僅是為了追求一個形而上的答案,更多的是為了反襯當代人的精神上的空洞、凋零乃至困惑.羅馬往日的輝煌和現在生活在羅馬的人們的空虛和無度,成了電影的核心矛盾之一.索倫蒂諾的視角化身為杰普,用一種悲觀的態度去表現當代城市的精神生活和娛樂文化的巨大的幻滅,采用了極為復雜雕琢的影像風格來描繪羅馬城和羅馬人,從內容和形式上達到了統一.
開場的兩場戲是用極為經典的對比手法來烘托出羅馬的兩個世界的共生.影片第一個鏡頭鳴放禮炮處理的極有創造力,鏡頭從炮口位置后退,同時在鳴放時刻突然采用了升格鏡頭,第一幕就奠定了全片夢幻與現實融通變奏的節奏基調.在羅馬的帕歐拉噴泉,老漢用池水洗漱,老嫗坐在公園椅子上,手里拿著報紙寫著羅馬最著名的足球明星托蒂,背后是復興時期(意大利統一運動)的英雄雕像.街頭人跡稀少,到處都是空蕩蕩的.攝影機鏡頭左右飛翔,迎著朝陽游曳在壯麗的建筑和隱秘的小花園當中.
帕歐拉噴泉的建筑內一群著裝現代的女郎在吟唱格里高利圣詠的優美旋律.拿著手機談生意的人步出大巴車,一群亞洲游客在羅馬當地導游的帶領下誠心領略著羅馬的華麗壯美.一位游客拿相機拍攝俯瞰的整個羅馬城,突然心臟病發作暈倒在地,人們圍過來救他,遠處的歌詠沒有停歇.人跡稀少和美輪美奐的建筑在電影當中反復出現,在主人公白天和夜晚巡游在羅馬大街小巷的時候更是如此,一種濃郁的被拋棄和被遺忘的情緒,結合繁華的絢爛的美完成了奇怪的組合.
當地人每日生活的習以為常和不以為然,和亞洲游客的虔誠膜拜乃至暈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羅馬城就像一本厚重的書,不斷地書寫新的篇章,舊的篇章又隨處可見,老讀者不屑一顧,新讀者趨之若鶩.緊接著一場戲就是樓頂的狂歡派對,杰普的65歲生日宴會.隨著相貌奇怪的女人一聲刺耳的怪叫,人群簇擁之下縱情歌舞.現代社會放縱的狂野濫交,毫無顧忌的聲色犬馬,伴隨著節奏感極強的電子音樂立刻呈現處了羅馬人的當代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索倫蒂諾對這場奢靡放蕩的宴會加入了極為“費里尼”的元素作為一種“不和諧”的調配,如墨西哥馬里亞奇樂隊演奏混入人群,以及玻璃房中的脫衣舞女在突然切換的極為輕快柔和旋律中呼呼舞動,幾乎像動物一樣被人觀賞,另一個丑陋的女人并無前因后果的高喊“我的手機丟了”.這些鏡頭分散地穿插在狂野喧鬧的歌舞狂歡之中,作為視覺和聽覺信息超量過載的某種喘息調和其中,為觀眾提供了一種張力極強的壓迫感的同時又加入了不適感.值得一提的是,杰普的雜志主編侏儒達蒂娜在這場戲當中有著驚人的作用.當鶯歌燕舞的女郎們相互簇擁起舞的時刻,鏡頭從裸露的大腿叢林當中找到空隙當中的達蒂娜.
當天色漸明、曲終人散之際,達蒂娜酒醒,闖入了剛才高挑的脫衣女郎的玻璃房當中.這兩次達蒂娜的出現,都是利用了侏儒和其他人的體型的巨大落差,配合當代生活當中的物欲和性欲制造出了某種扭曲的荒誕感,這種視覺奇觀足以令觀眾拍手稱奇.不僅如此,宴會當中的美與丑的相貌妝容伴隨著電子樂的強力節奏快速地交替涌現,粗俗的語言和狂放的軀干目不暇接,貼面式的近景充滿了各種表情,配合不時的呻吟,給觀眾用一種感官過載的方式,完全飽和地展示了羅馬上流社會的紙迷金醉.
這種類似于巴洛克式的影像風格最典型的美學特征就是用視覺上的或感官上的誘惑式的語言,配合極為壯觀的場面,讓觀眾完全沉浸在一種美學欣賞的休克當中.而羅馬作為兩千多年的歷史遺跡遍布之地,隨之完成了自我的走向商品化和功能化的蛻變.整部影片的第一個高潮也由此提前到來:達蒂娜歪歪斜斜的站立在一片狼藉的屋頂,背景是虛化的行將黎明的羅馬城,馬蒂尼酒的巨大霓虹燈管商標隨著搖臂鏡頭的移動緩緩升起.這兩場戲表現的兩個世界,一方面是在白天充滿好奇甚至是具有窺陰癖的游客,帶著尋找的心境去欣賞羅馬城市建筑的視覺美景,另一方面是在夜晚生活在羅馬的人在現代建筑的屋頂上恣意狂歡.人們不禁要問:當代的羅馬人是否還值得永恒之城的美?
2惰性的沉迷與優雅的殘破
杰普直到65歲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他已經沒有時間去浪費在自己不認同的事上了.他生活圈中的人清楚地體現了如他所說的“殘破的生活”:杰普曾經是一個作家,40年不務正業沉迷于燈紅酒綠;初戀女友的現任丈夫同杰普訴說衷情依依不舍,卻在妻子離世后迅速另結新歡;上了年齡的脫衣舞女伴還在賣力的工作來為治療自己的重病買單;郁郁不得志的劇作家朋友來到羅馬40年依然在無助的追求藝術,又陷入了不值得的感情困擾當中;口若懸河的玩具商人到處吹捧夫妻和睦,卻見縫插針,四處風流;左派女知識分子夸夸其談國家大義和社會責任,卻掩蓋自己學術的虛偽、家庭的失責和婚姻的破裂.索倫蒂諾的人物設置滲透著他對現代性的責難和對上流文化圈自命不凡、自甘墮落的嗟嘆.
從復興運動英雄加里波第、加富爾的雕塑,到65歲揮霍自己的時光和才華的杰普,尋找了40年藝術之路的劇作家老友最終放棄離開,脫衣舞女伴最終病逝,再到好友的兒子因無法忍受世間的荒謬和無意義而自殺,杰普困惑茫然,求助于教廷.不愿為世人解惑,只愛研究做菜的主教卻在數次接觸中讓杰普明白了他和這群上流社會追求膚淺的人沒有區別,教廷如T臺走秀一般的宗教儀式表演讓杰普冷眼旁觀.
這一系列的變化讓杰普幾乎心灰意冷,無力追問絕美在何處,他請求在卡拉卡拉浴場表演讓長頸鹿消失的魔術師把自己變消失.對年輕、容貌的癡迷正是意大利90年代之后貝盧斯科尼式的文化風尚,而年輕和容貌在生命中注定的短暫和流逝在羅馬的永恒式的美面前更加的脆弱和不值一提.
意大利以一種其引以為傲的豐富內涵和格調在優雅的下降,人們寧愿去逃避這一事實而去追求毫無意義的繁華和虛榮,靠著毒品、性和夸夸其談提供慰濟.偉大藝術成了他們口中借來肆意炫耀賣弄的裝飾,人人都在張口閉口談論莎士比亞、普魯斯特、福樓拜、尼可羅·阿曼尼提和皮蘭德婁,不求甚解地把他們當成文化標簽來消費,卻無人關心真實的社會.整個意大利的社會問題似乎完全遠離了意大利的上流社會人群,債務問題、移民問題、犯罪問題、南北差異似乎完全隔絕在這群討論文學、藝術的名流群體的泡泡之外.
真正的羅馬人放棄自己的責任,不愿直面對城市之美的照料義務.杰普甚至聲稱“羅馬最好的人是游客”.盡管索倫蒂諾有所否認,但這種缺席和隔絕正是他所埋下的對整個羅馬的視聽注腳:正是因為談論政治的缺席,因為共同價值的破滅,羅馬的文化在衰敗,在墮落,在腐蝕,變得褻瀆神圣、粗鄙和空心.
在恢弘燦爛的羅馬所承載的歷史面前,居住于此的當代羅馬人是如此的淺薄和卑微,逃避主義是貫穿在所有人物當中的隱含態度,可能只有維奧拉的兒子安德烈在追問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杰普花花公子的態度,取悅女人的輕浮態度,依靠美容術延緩衰老的事實,使他本身就投射著羅馬優雅的衰敗.讓他于他的朋友們唯一的差別可能也只在于一種感知上的自我覺察和誠懇.杰普當然也在尋找,但他卻輕易的以一種輕描淡寫的浮皮潦草的犬儒主義觀點去勸解安德烈,去藐視他人,或許這正是杰普的一種自我防御的機制:逼著自己去解構所有的崇高和深遠.然而索倫蒂諾并未將電影以一種憂郁的感傷當中結束.
半截入土的老修女瑪麗亞以一句“根最重要”讓杰普幡然醒悟.在羅馬的晚霞中,老修女的經紀人把她當成明星一樣經營,似乎要讓她成為另一個像紅衣大主教一樣被諷刺的對象.但索倫蒂諾將電影中罕有的本真賦予了瑪麗亞修女.她能叫出每一個火烈鳥的教名,鳥群靜靜地停在杰普家的陽臺上,又豁然離去.如同神跡一般的場景令杰普若有所悟.老修女瑪麗亞拖著衰老的軀體艱難地攀爬圣階,而杰普去接受雜志的任務俯瞰“科斯塔·康科迪亞”號沉船,再次回憶起了四十多年前在這片海域遇到的初戀女子艾莉莎,最終平靜的接受了“美已逝去”,“為人所必然的困窘”和“小說只是戲法”的事實.一切諷刺的、解構的、虛無的都被消解掉了.杰普終于又開始寫作了.所有的破碎最后都沉寂于破碎.
3懷舊的感傷與回歸的期望
“懷舊有什么錯?這是對未來不抱希望的人唯一的消遣.”杰普的朋友羅曼諾在劇場中說到.懷舊是《絕美之城》最核心的主題.所有的反現代性最終歸于了對年輕時代,對更早的傳統的訣別式的珍視.索倫蒂諾對華麗的衰敗有著執著的敏感性,他利用豐滿絢爛的巴洛克式的影像風格去描繪充斥巴洛克美學風格的羅馬.杰普就是觀眾的向導.
索倫蒂諾鏡頭中的杰普始終在行走,游蕩中窺視,杰普閑庭信步中帶著敏感的觸覺去觀察花園中嬉戲打鬧的孩子,醉酒在大街上喧嘩的食客,替人遛狗的外來勞工,在餐廳帶著黑色面罩沉默不語的阿拉伯太太,杰普在感受現代意大利的多元生活.他游蕩在羅馬的大街小巷,穿梭于古老和現代之中.這種行走鏡頭并非是有明確的視角指向,杰普在視角中是自由的,他可以突然迎面出現,也可以在畫面中橫向移動,并非如泰倫斯·馬力克一般將視角鎖定在主人公背后,借主人公去看.
索倫蒂諾的行走鏡頭是松散的,重要的并不是讓觀眾去感受杰普所感受到的見聞,而是要將杰普的感受放置在環境中形成帶有作者性的審視.《絕美之城》對藝術美學的展示精彩絕倫,索倫蒂諾利用各種滑軌、斯坦尼康和搖臂將古羅馬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到反宗教改革運動時期,再到復興時期的古典建筑拍攝的富麗堂皇.由于羅馬的特殊性,歷史遺跡和城市完全交融為一體,索倫蒂諾展示的羅馬正是懷舊思潮最適合的載體.影片對羅馬建筑的表達極為宏大和壯麗.
太陽光和燭光投射進宮殿和雕像上的鏡頭都經過了對光影的精心雕琢,這些偉大的建筑似乎是一點一點被剝開供人觀賞.到處都是明信片取景地的城市廣場噴泉,遍布市區的古建筑設施和雕塑,包括杰普的高級公寓窗臺之外的宏偉的羅馬斗獸場.他們似乎具有生命力一般,都和杰普一樣,作為同一個群體毫無希望的陷入對過往光輝的不舍當中,不得不接受的是這樣的事實,曾經的羅馬再也回不來了.
對藝術美學的懷舊集中體現為對當代藝術的否定性的看法上.渡槽公園的古羅馬阿皮亞水渠下,經典油畫般的取景,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巴恩斯的詩歌“我的心在高地”響起,吉普賽女藝術家赤身裸體、聲嘶力竭地撞向拱柱,進行著滑稽、空洞的行為藝術表演.這種場景和行為的撕裂感比之前所提到的羅馬的兩個世界更加直觀和強烈.索倫蒂諾借杰普之口,在之后的訪談中對吉普賽行為藝術家咄咄逼人的追問,正是導演對當代藝術空洞賣弄,回避本質,逃避真實情感的辛辣諷刺.隨后的小女孩在悲傷中用身體在巨大的畫布上作畫的場景,后現代主義藝術當中“人在何處”的缺陷暴露無遺.
影片中的懷舊還體現在對現代科技的無視的態度上.與《甜蜜的生活》當中的馬切羅不同,杰普從未出現在汽車或其他現代交通工具當中;手持攝像機鎂光燈的媒體同樣也從未在《絕美之城》中出現;當與自己的粉絲富家女纏綿之后,杰普選擇在富家女試圖拿起筆記本電腦向他展示臉書頁面的時候決然離去;同樣,手機完全缺席了杰普的生活.如果說費里尼去表現的還是意大利戰后黃金時代的資本主義騰飛之下的荒誕,那索倫蒂諾則完全將經濟科技發展帶來的生活變化統統棄之如無物.
時代的“進步性”在索倫蒂諾看來不僅是可疑的,甚至是膚淺的、不值一提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索倫蒂諾對羅馬的新古典主義、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巴洛克美學毫不吝嗇的贊嘆和崇敬.杰普和女伴執手夜游馬耳他宮和美第奇宮,在古典雕塑和繪畫面前流連忘返.杰普對絕美的回憶,正是對青春時光的懷舊.他的初戀情人艾莉莎40年前在海灘的礁石群中向他袒露玉體,年輕的杰普在黑暗中被燈塔的光芒勾勒出明暗交替的臉龐,那一刻艾莉莎的形象仿佛古希臘柯尼多斯的阿弗洛狄蒂的雕像一般純真、端莊、美麗.杰普心中的絕美是關于過往的,古典的,在此刻顯露無遺。
可最終杰普還是不得不得出結論:生命就是關于時間的.在所有的城市游歷中,有三場戲杰普流下了熱淚.除了得知初戀女友病故的消息時痛哭之外,一場是在埃特魯利亞國家博物館的一個人的肖像展當中,當面對藝術家四十年每天的自拍,杰普看到了時光在一個男孩臉上雕刻的所有痕跡,人近晚年的他不得不感同身受,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被自己揮霍的人生.另一場是在好友維奧拉兒子安德烈的葬禮上.
杰普在之前剛剛賣弄人情干練的經驗給女伴拉蒙娜講解如何在葬禮上完成社交王者的風范,卻在葬禮現場無法自控崩潰在淚水中.杰普不是在哭安德烈,而是安德烈如此年輕卻對生命意義的不妥協和自己的放任自流讓他無法面對自我的良知.電影在剛開場引用了塞林納的《長夜行》的詩句為開場,“旅行是有用的:它激發你的想象力.其他的一切都是失望和麻煩.我們的旅程完全是想象的,這也是它的力量所在”.結尾則用了完全契合詩中內容的行舟臺伯河的長鏡頭作為旅行的終點,堪稱本片的華彩篇章.杰普直到直面死亡,終于平靜地接受了絕美的不可得,而“只有化為碎片的美去撫慰人以無常和微妙、真實和虛假的結合,一切的浮華之上就是生而為人的困窘”.美就在此。
作者:孫地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