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視閾下的遼代箭儀
時間:2021年08月04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 要:箭儀是遼代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遼史》《金史》《契丹國志》中記載的遼代箭儀有瑟瑟儀、射鬼箭、勘箭儀、正旦驚鬼、上巳節、重九節以及再生儀七種禮儀,遼墓中也出土了大量與箭儀相關的文物,包括箭鏃、箭、箭囊、箭筒等實物及相關壁畫。遼代的箭儀既有契丹本民族的特點,又融入中原文化因素,是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關鍵詞:考古學;遼代箭儀;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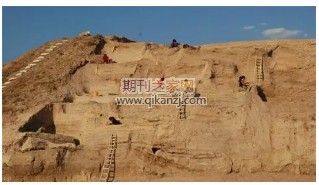
契丹建國以前,由于長期過著氏族生活,只有一些簡單的風俗。《遼史》中記載:“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尚有質之風,遙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1]遼太祖阿保機即位以后,為了加強皇權,于太祖七年(913年)“定吉兇儀”[2]。從此遼朝開始施行禮制。
一、遼代箭儀略說
箭是遼朝禮儀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禮器之一,與之相關的有瑟瑟儀、射鬼箭、勘箭儀、正旦驚鬼、上巳節、重九節以及再生儀七種禮儀。箭儀作為一種長期的文化積累,凝聚了契丹民族深刻的人文理念和思維方式。
據《遼史》《金史》記載,瑟瑟儀有如下程序:按照等級,皇帝射兩次,親王、宰相及臣僚射一次;用手帕標志要射的柳枝,離地幾寸的地方要削去樹皮露出白地,先是一人馳馬前導,后一人馳馬用無羽橫鏃射之;如果射斷柳枝,以手接住,并飛馳而去者為優勝者,給與冠服;瑟瑟儀第二天植樹,前段為祈雨,后段仍然是射柳[3]。
據《遼史》記載,射鬼箭大多是在秋冬月份舉行。祭祀是射鬼箭的重要內容,皇帝出師前要先告廟,祭拜“三神主”,要殺青牛白馬祭祀天地。祭時,常依托于一棵獨樹。將出征時,牝牡麃各一獻祭。戰勝敵人后,以白、黑羊祭天地。遼帝每次親征在出師、行軍途中、班師時都必須進行射鬼箭之儀。射殺的對象為死囚、俘虜等。太祖初年,射鬼箭已經成為一種極刑被確立下來,與梟磔、生瘞、炮擲、支解并列[4]。
據《遼史》記載,勘箭儀整個儀式由受箭、呈箭、勘箭等活動組成。將箭作為勘合的對象,說明箭在契丹社會中不僅是一種重要的遠程武器,同時也是軍事權力的象征,皇帝巡幸歸來須內外勘同后開門,也示留守之慎之意[5]。
據《遼史》記載,正旦驚鬼整個儀式中,先擲丸,根據擲出帳外的數量不同,舉行不同的儀式。若所得數量為奇數則為不祥,巫人會執箭繞帳高呼,在帳內進行燒地拍鼠之儀,以示消除不祥之意[6]。
據《遼史》記載,上巳射兔是上巳節當日要射木頭刻成的兔子,然后騎馬比賽,先射中兔子即為獲勝,輸的一方要下馬跪著向獲勝的一方敬酒,獲勝方則騎在馬上將酒一飲而盡[7]。
據《契丹國志》記載,重九射虎是,重陽節當天,天子率領群臣部族射虎,射不獲或者射得少的人,被判輸,要罰他們請“重九”宴[8]。
據《遼史》記載,遼朝只有皇帝、太后、太子和部族首長可以舉行再生儀[9]。契丹皇帝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行再生禮。先在禁門北,準備好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并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在舉行儀式這天,皇帝要脫衣服、光腳進入再生室,三次從岐木下過,并臥在木邊,老者擊箭袋說“生男孩兒了”,太巫用巾蓋上皇帝頭,皇帝起來,群臣稱賀,再拜。事先選好的七位老人每人把為皇帝起的名字系在采緞上,進獻皇帝,皇帝選好一個名字后,賜給老人物品。群臣則進獻小嬰兒的包被,彩結等物。皇帝祭拜先帝后再宴請群臣[10]。
二、考古學視閾下的遼代箭儀
據《易經·繋辭下傳》記載,弓箭最原始的形態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11]。之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用木頭、竹子、動物的筋和膠等合制成弓,稱為“復合弓”。箭是搭在弓上發射的武器,主要由鏃、桿、羽、栝四個部分構成。在內蒙古、遼寧、河北、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發掘的遼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遼代鐵箭鏃實物,筆者將其分為七類,分別為甲類A型、B型、C型,乙類,丙類,丁類,戊類A型、戊類B型,己類,庚類(見表1)。
在遼代史籍中記載,“箭削樺為簳”[35]“紅錦袋皂雕翎羱角骲頭箭十,青黃雕翎箭十八……”[36]在遼墓也出土了箭桿實物。赤峰大營子遼墓中出土鐵桿鏃,鋌細長,鋒作柳葉形,存長15.5厘米,刃寬0.9厘米[37]。在內蒙古霍林郭勒遼墓中出土木桿鏃,鐵鏃為四棱尖刀狀,長5厘米,寬1.8厘米,厚1.6厘米,尾部有一圓銎,可安裝箭桿。箭桿長70厘米,直徑0.5-0.7厘米之間。箭桿細端纏上薄薄的樺樹皮,插進鐵鏃圓銎里,從而使箭桿安裝牢固。箭桿尾端刻一個“凹”字形槽,槽搭弦上,彎弓射出。箭通長75厘米。箭桿為硬質富有彈性的木條[38]。分析可知,遼代鐵箭鏃的種類較多,箭桿木質,箭羽以雕翎為主。
遼墓中也出土有盛箭的器物。在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巴彥庫仁遼代墓葬中出土一件箭囊,其為縫制,筒形,口窄底寬,口部一側邊向內斜收,端部有根殘斷的皮條,兩件“八”字形銅飾件鉚在斜邊上,另一側邊略外敞。口下部正中位置挖空一塊,呈橫向圓角長方形。兩側邊中部略內弧,底部為圓邊。口部及一側邊以明線縫合,另一側邊是在兩張皮革的側邊斜向內暗線相縫,表面無縫線,長57.3厘米,口寬22.8厘米,底寬31.8厘米[39]。在內蒙古霍林郭勒遼墓中也出土一件箭囊,其為樺樹皮縫制,出土時保存完好。
半圓形長筒,筒長70厘米,寬18厘米,厚8厘米。囊底為1厘米厚的木板[40]。在遼墓壁畫中也有相關內容,《鷹軍圖》[41]中,6個騎馬者排列成兩排三隊,均身披鎧甲,頭戴盔,腰挎箭囊。《廳堂圖》[42]中,在紅色幾案左側懸掛有箭筒,側開式筒蓋翻垂。《獵虎圖》[43]中,射獵者腰間掛有箭箙。《騎獵圖》[44]中,有一契丹獵人正拉弓射箭,左腋下掛有箭囊。在慶陵東陵前室北甬道西壁左側人物畫像,其右肋之下懸掛一個箭筒,箭筒里盛有箭束[45]。分析可知遼代盛箭用的器物大致存在兩種形制,即縫制的箭囊、用樺樹皮制成的箭筒,在狩獵的過程中一般放置在獵人腰部。
據《金史》載,瑟瑟儀中“以無羽橫鏃箭射之”[46]。通過考古材料發現,所謂橫鏃箭可能箭鏃鋒部扁平,刃部較寬,與甲類箭鏃類似,亦有可能包括戍類箭鏃。遼代軍事上所用的箭鏃為矛式鏃、三翼鏃、菱形鏃、柳葉形鏃[47]。射鬼箭儀式中,均以人為射殺對象。此種類型的箭可能箭鏃鋒部尖銳,接觸點小,與乙類、丙類、丁類、己類箭鏃類似。在上巳射兔儀中,所射的對象是“以木為兔”,可能與射鬼箭所用箭鏃相同,利于集中力量射擊目標。
勘箭儀中,東上閣門使執雄箭,勘箭官執雌箭,所執的雌雄箭可能為木箭[48]。因史料記載有限,正旦驚鬼儀式中巫人所執弓箭亦可能為木箭。契丹民族用于狩獵的為寬刃箭鏃[49],即重九射虎儀中所用箭鏃可能與甲類、戍類相似。再生儀中包含老者擊箭袋說“生男孩兒了”這一活動。箭袋的形制可能為縫制的箭囊或用樺樹皮制成的箭筒。
三、小結
遼代箭儀內容豐富,儀式莊重,是契丹文化與漢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遼代箭儀既有契丹本民族特色的瑟瑟儀、射鬼箭、勘箭儀、正旦驚鬼、再生儀,又有中原文化特點的上巳節、重九節。《新唐書》記載:“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50]唐代射兔也是一種射箭活動,人們用木頭雕刻成兔子,然后騎馬比賽,看誰先射中兔子即為獲勝,輸的一方要下馬跪著向獲勝的一方敬酒。九月九日重九日,中原漢族歷來有賞菊、飲酒、登高、插茱萸等習俗。契丹族的上巳節、重九節很可能來自中原漢族地區,同時也反映出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
參考文獻:
〔1〕〔2〕〔3〕〔4〕〔5〕〔6〕〔7〕〔9〕〔10〕[元]脫脫,等.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833,8,835,845,848,1542, 877,1542,878,1537,879-880.
〔3〕〔46〕[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826,826.
〔8〕〔35〕〔36〕[宋]葉隆禮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4.283-284,252, 225.
〔11〕常萬里.易經[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 519.
〔12〕〔17〕〔24〕〔27〕〔30〕敖漢旗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敖漢旗沙子溝、大橫溝遼墓[J].考古,1987(10):889-904.
〔13〕〔28〕李宇峰,韓寶興,郭添剛,張春宇,王慶宇.彰武朝陽溝遼代墓葬[A].遼寧考古文集[C].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83.
〔14〕〔18〕〔2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順義縣文物管理所.北京順義安辛莊遼墓發掘簡報[J].考古,1992(06):17.
〔15〕劉謙.遼寧錦州市張扛村遼墓發掘報告[J].考古,1984(11):990.
〔16〕彰武縣文物管理所.遼寧彰武縣東平村遼墓發掘簡報[J].北方文物,1999(01):31-34.
〔19〕崔福來,辛建.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長崗遼墓清理簡報[J].北方文物,1993(01):43.
〔20〕齊小光,王建國,從艷雙.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6(01):4.
〔21〕張漢英.河北豐寧五道溝門遼墓[J].文物春秋,1996(02):18.
〔22〕〔33〕張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J].文物,1983(09):18.
〔23〕柳嵐,邵春華.吉林雙遼縣高力戈遼墓群[J].考古,1986(02):138.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