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希納《沃伊采克》的多維批判意蘊及其劇場呈現
時間:2020年09月10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內容摘要: 批判精神是畢希納劇作《沃伊采克》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現代藝術表征,但劇本結 構的開放性和語義的復雜性決定其批判意蘊向多個維度延伸。該劇的社會政治批判是最顯在的一個意義層面,它批判了社會對底層無產者無情的壓迫。其次是內涵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批判,包括對“文明”社會人倫價值的深切懷疑和對現代精神病癥問題的揭示。最終作者把觀眾引向了對生命意義、個體存在境遇的哲學批判。從當代在中外上演的三個劇場 案例,可見其批判意蘊在劇場實踐中的具體呈現。
關 鍵 詞: 畢希納 沃伊采克 批判精神 劇場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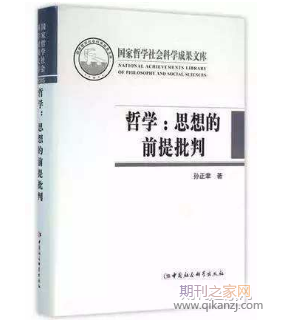
《沃伊采克》是畢希納最后一部①、也是他“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品②。它醞釀 了現代德語戲劇藝術風格的多種源頭,批判精神是其突出的表征。正如畢希納本人的個 體存在是政治、哲學、科學、熱血和詩情的結合一樣,《沃伊采克》的批判意蘊也是多維 的。作家對他所在時代的社會、文化、個體生存,以及人類即將面臨的困境和從未擺脫的 苦難進行了綜合的反思。本文試從政治、文化和哲學三個層面,結合劇場案例進行闡釋。
哲學方向論文范例:從《人性論》談休謨的哲學研究方法
一、社會政治批判
社會政治批判是劇本最顯在的一個意義層面,也是國內學術界比較主流的解讀。③ 從情節主線來看,作者通過沃伊采克這個社會底層人物的悲劇命運,揭示了階級社會中 無產者所遭遇的貧困處境和殘酷的不公。但沃伊采克作為該劇最主要的悲劇人物是一 個殺人者而不是被殺者。
所以,畢希納在情節構思過程中有意突出了主角的殺人行為的 被動性。在第一手稿中,沃伊采克就經常有一種幻覺,有人要他去殺人,暗示殺人者的殺 人行為是受某種神秘力量驅使的,并不完全自主。④ 第二手稿中,踐踏他人格的上尉和 做人體實驗的醫生這兩個施虐者角色的出現,使沃伊采克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欺凌和壓 迫的事實有了更直接的原因和明確的表現,更加凸顯了社會外因的影響,將悲劇的重心, 從“殺人”轉移到殺人者被各種社會力量以“合理”的方式虐待的過程上來。這樣,殺人 者成了被虐者,殺人行為成了悲劇性的反抗。
于是,反抗壓迫和剝削的社會批判主題就 顯現出來了。這種將犯罪的責任歸咎于社會而非罪犯的做法,后來成為歐美批判現實主 義的文學和戲劇作品中常見的模式,而畢希納是歐洲戲劇史上較早提出這個批判視角的 作家。 然而,畢希納的政治批判并不止步于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和對壓迫者的憎惡。隨著民 主革命的失利和退潮,他對社會革命有著比同時代人更深刻和清醒的認識。
⑤ 和“青年德意志派”①不同的是,畢希納認為僅僅依靠知識分子,通過知識啟蒙和文藝宣傳,從觀 念上來引領廣大無產者進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對無產者來說,貧窮和饑餓是根本的革命 動機,也是他們的軟肋。知識階層可以借助貧困鼓動廣大無產者起來革命,統治者同樣 可以用物質輕易收買無產者,瓦解革命。② 劇中沃伊采克和瑪麗同樣都是社會最底層的 貧民。如果說他們的結合象征著無產者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中艱難求生而形成的相互依 賴的關系,那么他們之間的背叛和殘殺就象征了這種聯合關系的瓦解。
而瓦解的主要原 因是“物質”: 瑪麗厭棄貧窮的沃伊采克,被富有而健壯的鼓手長吸引,一塊懷表就可以 引誘她投懷送抱,用背叛情人和出賣肉體換來的一副金耳環可以令她喜不自勝。她慨嘆 自己雖“有一張紅唇”,卻不能像闊太們那樣有大鏡子照好衣服穿,有“漂亮的先生”的親 吻。③ 她對富人的反感僅僅是出于物質上的羨慕,并不曾對這個社會制度固有的剝削本 質有半點認識! 同樣,當時的知識分子階層也不可能引領革命。在“教授的院子”一場中,畢希納對 知識分子的虛偽做作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教授”站在高高的頂樓,自比以色列王大衛。 這象征著知識分子遠離民眾,居高臨下,自命不凡。可是,他眼中看到的卻是女生的內 衣,腦海中想象的是大衛王強占人妻的不倫之事,說明他人品猥瑣,趣味低下。他滿口云 山霧罩的德國唯心論哲學的專業術語,將貓從窗口拋出,來證明“神性有機體”和宇宙空 間的各種關系。④ 這個從目的到手段都荒誕無聊的實驗,卻被“教授”當作探求真理的莊 嚴舉動。
“教授”只關心貓騰空的狀態,“醫生”只關心貓虱的新品種和沃伊采克的病理 癥狀,他們都毫不在乎沃伊采克的痛苦和屈辱。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盲目追求科學和真 理,罔顧現實社會和人類的生存福祉。 唯一一絲渺茫的革命希望以絕望的方式啟示在沃伊采克身上: 他在醉醒之間對苦難 有清醒的認識,他用自我毀滅反抗,用窮人的鮮血叩問社會。畢希納認為民眾的覺醒是 社會改革最重要的前提。他曾希望在民眾中塑造出一種“新的精神生活”,建立一種人 人都認可的“絕對的法律原則”,成為人們行動的根本依據⑤。
這有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影 子,亦有馬克思社會革命論的先兆,可惜他短暫的生命沒有給他充足的時間展開政治 理想。 作品用科學紀實的態度進行社會批判,不僅取材于真實的社會事件,而且很多情節 和臺詞也直接源于生活現實或文獻資料。這種方法具有強烈的真實性和社會話題度,使 批判更為可信、有力、精確。同時加入怪誕的元素,“批判性地將科學的觀察方法交由滑稽的東西來擺布”,把質樸的事實轉化為生動的敘事,將科學向社會問題開放,開啟了一 種新的文學表述方式。
① 1995 年孟京輝和德國留學生安琪·布德聯合執導的話劇《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 克》就是運用紀實和諷刺的技法,圍繞原作社會批判主題展開的劇場案例。② 該劇把《沃 伊采克》和中國上世紀 30 年代鼓舞國人抗日救亡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并置為上下 兩場的雙題劇,作為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紀念演出。選題本身 就寓意著貧窮、壓迫和反抗是跨越國界和時代的普遍的社會問題。
郭濤在劇中飾演 《放》劇中的青年工人和《沃》劇中的沃伊采克,是兩個在不同時代和文化語境中的被壓 迫者和覺悟了的反抗者。演出的形式非常突出原作的紀實性特征。上半場的《放下你的 鞭子》在劇場室外的空地上演出,試圖還原街頭劇的環境效果,演員對話有民謠、流行歌 曲、武術雜耍、電影對白等多元素拼接。《沃伊采克》隨后在室內小劇場上演。劇場環境 封閉、幽暗、觀眾擁擠,正好與上半場的室外演出形成強烈對比,臺上臺下的觀眾和演員 一起進入焦慮、壓抑、郁悶的情緒體驗,場內空調低沉的轟鳴,“不斷加強著一種不祥”和 “撕裂人心的躁狂”。
③ 舞臺占劇場的三分之一,中央放一只矮箱,天花板上懸下許多粗 麻繩,中間吊著一個搖籃,一束橘色的燈光灑下,用來表現沃伊采克窮困潦倒的家。④ 這 個本已破敗的家最后隨著男女主人公的死亡而毀滅,直至劇終時舞臺上的搖籃仍空懸 著,象征著貧窮和壓迫的陰影仍然籠罩世間。 該劇還把握了原作諷刺和黑色幽默的風格,除了沃伊采克和瑪麗以外,其他的角色 均以喜劇方式演繹,還特別加入了小丑不時進行插科打諢,和上半場的花式雜耍一起形 成了全劇嬉笑怒罵的諷刺基調。表演風格是表現主義的,刪去了許多生活真實細節的表 達,注重精神和激情的表現。
沃伊采克“被繩子纏、被摔、冷水澆頭”⑤,郭濤用奔跑、抽 搐、戰栗、神經質等大幅度的動作來表現角色身心受虐的痛苦和半瘋半醒的精神狀態,用 激情串起全劇碎片化的結構。演員“將自己的血肉與角色的血肉熔鑄為一”,撞擊觀眾 心靈。⑥ 為了達到批判性啟迪的目的,該劇在開頭就上演了殺人的結局,后又用不同的 方式多次表現沃伊采克殺死瑪麗的情景,甚至有小丑直接發問: 誰是真正的兇手,誰能真 正思考這個案件? 劇場墻上有兩面老式的鏡子,配合場上演出的種種間離處理,不斷提 醒觀眾思考、反觀自身。評論認為,孟京輝“將反抗情緒與荒誕形象注入其中,從而表達 了一種新的意趣和精神傾向。”⑦
二、文化批判
對革命活動的反思和質疑,必然使畢希納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超出“壓迫/反抗”這樣 簡單的政治批判邏輯,進入更深的層面尋找問題根源。事實上,作品由政治批判這個顯 在的故事結構引申出更為廣泛的文化批判的意義,即站在人文主義的立場,超越一時一 地的政治矛盾,用更普遍的眼光揭示啟蒙時代以來,人們深陷其中卻不自知的文化困境。
1. 對“文明”社會人倫價值的深切懷疑
畢希納受盧梭反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全劇貫穿著一個突出的意義線索———自然與 文明的沖突,通過一系列對立的意義結構使這個主題得到反復表現。 一是鄉野和城市的對立。全劇場景發生的空間分為鄉野和城市兩類,沃伊采克在這 兩類空間中的狀態截然不同。如他在曠野里割荊條,產生幻覺,看到遠處城市里有天火 雷動的世界末日的景象; 而當他躲入叢林時,世界又陷入了死寂①。“曠野”象征自然, “城市”象征文明社會,暗示了城市和鄉野所代表的兩種文化形態的尖銳對立。沃伊采 克曾在曠野里動念殺人,也是在野外殺人、棄刀的②。
此外的場景基本都發生在城市。 處在野外的沃伊采克有力、亢奮、神經質,他所見所感所為都出于內心的自然意志的驅 使; 而城市的場景都在人為的文明規范下發生,人們做著無聊、荒誕、自以為是的舉動,沃 伊采克則顯得木訥、孤獨、軟弱、壓抑。鄉野和城市兩類場景中人物能量的對比,為作者 揭示文明對人的自由本性和生命沖動的閹割做了整體性的烘托。
二是人和動物的對照。畢希納在劇中巧妙地設置了一明一暗兩個反向平行的意 象———動物的人化和人的動物化。③ 人和動物相互影射,以此來表現文明與自然的對立 和錯位。畢希納用極為諷刺和怪誕的手法,在劇中設計了兩場雜耍篷的戲,集中表現了 “動物的人化”,用動物的馴化諷刺人的教化,質疑了“啟蒙主義”所宣揚的理性和教化的 價值。④ 招徠者先是向圍觀的人介紹即將進行雜耍演出的馬、金絲雀和猴子有像人一樣 的本領。他不斷地拿這些動物和人來比較,說他們經過教育后有了擁有“禽獸的理性” ( viehische Vernunft) 或“理智的獸性”( vernünftige Viehigkeit) ,這使它們不再像多數人類 那樣只是“禽獸般愚蠢的個體”( viehdummes Individuum) 。
⑤ 這顯然是用動物來影射人類的自以為是。教化的人類無非是掌握了一些無聊的技能,他的動物性本能被膚淺的理 智所包裹,他的理智從未脫離過動物的本性。招徠者又向觀眾介紹一匹具有“雙重理 智”的馬,它能聽懂人話,因而兼具動物和人的理智,但他又不能說話,說明理智有限,沒 有完全擺脫動物性。它是“一個獸性的人”,又“確實是一頭畜牲”①,這暗喻人是理智和 自然的雙重結合體,人不必因為教化獲得的能力而沾沾自喜。畢希納認為,理智“只是我 們精神本質的一個極小的側面,教育只不過是這種本質的一個很偶然的形式”。② 如果 人因為這一小點教化的成就就忽視自然本性的話,只會使自己的自然本性“腐敗變 質”。③
2. 對現代人精神病癥問題的揭示 另一個沉重的文化批判主題是現代人的精神病癥。畢希納敏銳地洞察到了現代社 會人們難以逃脫的被精神折磨的厄運。⑦ 劇本取材于三起殺人案,它們的共同之處除了 殺人犯的貧民身份和情殺動機之外,他們都被懷疑精神有問題,但最終卻被判定為正常 行為人而獲刑⑧。這些素材被濃縮到了劇中的沃伊采克身上,劇本展現了精神錯亂癥使 他備受折磨直至走向崩潰的過程。畢希納早于弗洛伊德半個世紀,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來 看待精神病。他真切地描繪了沃伊采克復雜的心理感受和恐怖的幻覺,展現了精神病人 乖戾的行為背后隱藏的非理性的思維。
三、哲學批判
劇本的離散性結構促使人們“從他自己的心靈感受中拿出東西來添加到這部劇中, 同時將想象力的血液和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混合起來”②,最終引向了對生命和存在的哲 學思考。 畢希納為我們展現了一幅人與人之間存在之疏離的荒涼圖景。沃伊采克無論在什 么場合,和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地溝通。“醫生”從不在乎他的病痛,甚至感到興奮; “上 尉”享受著沃伊采克為他修面的服務,卻在談論著時間和天氣,對他進行道德指責; 安德列斯是沃伊采克最親近的戰友,劇中有五場戲是他們兩人單獨在一起的,但是沒有一次 對話是真正的溝通; 沃伊采克和瑪麗之間的對話從來沒有情感的交流,甚至還要隔著窗 講話①。
沃伊采克在公眾場合總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眾人喧鬧狂歡,而他則沉浸在自己 幻覺和現實交織的痛苦之中。劇中其他角色之間也普遍存在著冷漠的疏離: 瑪麗和女鄰 居瑪格麗特之間的相互咒罵,“醫生”和“上尉”之間的相互嘲諷,瑪麗和鼓手張之間如野 獸般征服與被征服的情欲的宣泄……因為要表現這種人際間的交流障礙,劇中人物的臺 詞顯出一種特有的生澀感,形成了全劇的荒誕意境,不知不覺把觀眾帶入了生之孤獨的 體驗之中。
或許畢希納“并不是在向我們展示一個社會的離群者如何自然主義地、逐漸 被疏離的過程,而是啟發我們進入身處疏離的感覺”。② 這種疏離感是對現代社會人的 孤立狀態的揭示。總之,多維批判意蘊交織而成的《沃伊采克》是一部集紀實、象征、諷刺、幽默、思辨 和啟示為一體的風格獨特的劇作。它的意義和價值能夠隨著時代、民族、文化的變遷不 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章文穎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