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學經典的跨媒介閱讀模式探究
時間:2019年12月16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 要:圖像時代下,面對文學經典閱讀的日漸式微,本文著力構建一套跨媒介閱讀模式,激活文學經典在新時代下“數字 受眾”中的傳播通道。
關鍵詞:文學經典;跨媒介閱讀;圖;像;表;閱讀平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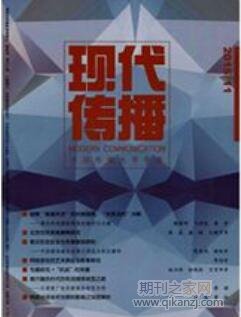
今天已然進入數字圖像時代,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2017 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數字時代的兒童》指 出,全世界上網人口中,18 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占據了 三分之一。推算一下,截至 2018 年,2000 年后出生的這一 批從小浸泡于互聯網中的孩子恰好進入高校,這一批孩子被 認為是第一批擁有“數字童年”的青少年,面對信息獲取模 式數字化的受眾,文學教育工作的出路成為擺在每一個文學 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問題。
因循守舊、固守成規肯定是死 路一條,不管紙媒的“書卷味”如何沁人心脾,都無力阻擋 “嶄新的數字化新媒介時代”的來臨。教育部頒布的 2017 年 版《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其中“跨媒介閱讀和交流”成 為語文教學的任務群之一,由此說明數字閱讀已然成為閱讀 趨向。因此作為承繼中學教育的大學語文教育,更是應該一 以貫之地執行“跨媒介閱讀”模式,這也是對終身學習和數 字化時代的一種呼應。當然數字閱讀由于其媒介特有的物質 結構肯定帶有有偏向性。
碎片化、娛樂化、淺層次化都是我 們不容忽視的缺陷。文學閱讀在與媒介資源聯手協作時,我們 應該充分發揮教師這一引導者的作用,有效規避閱讀風險,使 得傳統閱讀與新型數字閱讀模式相得益彰,最終為讀者構建豐 富、完善的閱讀體驗和效果。
本文是作者在歷時 4 年,對 520 名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外國文學》的同學問卷調查,24 名 同學深度訪談的基礎上構建的“跨媒體閱讀”模式。之所以選 擇語言文學學習者作為調研對象,一方面是因為筆者多年從事 文學教育,對于受眾的學習閱讀情況有能力從歷時的比對中 加以把控和分析。另一方面,外國文學作品由于異域文化背 景,更成為學生經典學習中束之高閣的重災區。下面即筆者 從閱讀主體和閱讀資源建立的新型閱讀模式。
一、閱讀主體——教師引導、學生“悅讀”
將教師這一群體納入閱讀主體,是因為歷來教學相長, 況且在數字化時代,教師的知識權威地位早已被顛覆。從事 文學教育的教師應該及時了解并使用新型閱讀媒介,分析媒 介自身的偏向性。做好引路員和掌舵者的工作。因為經典大 多具備一個優質的故事內核,更是成為多種媒介平臺爭先恐 后加以改編的資源。因此學習經典的渠道多樣化。
比如莎 士比亞的戲劇,除卻舞臺演出,更是成為影視導演的寵兒,幾乎西歐各國都有電影改編,比如《王子復仇記》,兒童動 畫版的《獅子王》。就連我國新世紀以來就有馮小剛執導的 《夜宴》、胡雪樺執導的具有西藏風情的《喜馬拉雅王子》。 今天人們利用電子設備在互聯網上甚至可以欣賞到現場價值 不菲的英國國家劇院版的《哈姆雷特》。陳忠實的《白鹿原》 自獲得茅盾文學獎以來,更是被改編為同名秦腔、同名連環 畫、單行本同名話劇、同名電影、同名電視劇。
有些改編是 在充分理解原著的基礎上對經典的互文性解讀,但有一些純 粹是以名著為噱頭,本身毫無藝術價值,甚至對于讀者都會 引起一種誤讀。面對這種情況,今天的教師的職責不能依舊 局限于知識的傳播,而要轉向為做媒介資源的偵查員。剔除 有害媒介,推介有效媒介,同學生提供優質的閱讀視聽平臺。 另外目前高校所采用的文學史教材基本還是清一色的文 字性著作。
面對閱讀環境的變化,教師需要編定圖文并茂、 融合視聽資源為一體的教材。這一方面,應向國內兒童讀物 和中小學教材學習。在《外國文學》教材編訂中,暨南大學 的張世君教授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她注意學科交叉,在跨學 科平臺上整合外國文學史知識體系。探討了外國文學作品與 電影、歌劇、美術作品的互文性,拓展和深化了外國文學史 教學,改變了外國文學史的資源和知識結構。
在體例上,該 教材每章、每節結束都有圖表總結,思維導圖。但由于內容 只講到馬克吐溫,該教材在高校教學中的普及度不高,輻射 面不廣,沒有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在教材編寫的道路上, 教學一線的工作者依舊任重而道遠。 真正完成閱讀依然要靠學生自身。
數字一代對于識別和 使用新型媒介具有天然的嗅覺優勢。閱讀內容的跨媒介生產 已是必然趨勢,從二維到三維、從文字到圖像、從平面到立 體,豐富的經典世界正在建構。讀者除了利用成熟的媒介平 臺外,還可以鼓勵學生利用自媒體平臺傳播經典。比如鼓勵 學生在課程微信群里閱讀打卡,在朋友圈里曬閱讀進度等, 都可以讓學生愛上經典,并自身承擔起經典傳承的重任。
二、閱讀資源——圖文并茂、聲像一體
1. 思維導圖
思維導圖“表現思維過程、發現不同知識間聯系和沖突 的重要工具。”在教學設計中,教師可以首先安排學生從閱讀后的簡單的人物關系圖畫起,接著給出自己對于某一問題 導向下的思維框架,讓學生補充圖示的詳細信息。
之后讓學 生自行通過互文性媒介資源的比對繪制小論文思維導圖,以 此培養學生的邏輯能力和知識遷移能力。最好通過思維導圖 在群中的共享,讓參與者相互提問,解決潛在的問題,使得 思維導圖下的論述趨向嚴謹。教師也可在學生思維導圖的共 享中也會得到啟發,教學相長、教學互促的目的將得到真正 的實現。
2. 文學地圖
《外國文學》課程是一門涵蓋除卻中國文學之外的世界 所有國家文學的課程。它時間跨度大、地域覆蓋廣、內容異 常豐富。為了讓學生不畏懼該門課程,繪制世界文學地圖是 很有意義的。在某一時段文學史或者某一地域的文學史學習 完成后邀請學生繪制文學地圖。比如要求學生繪制文藝復興 時期歐洲文學地圖,大多數學生完成地圖之后就會發現莎士 比亞和塞萬提斯這兩位巨匠的共同之處,也會在地球的另一 端發現中國的戲劇大師湯顯祖。
3. 表格
比起生動感性的“圖”,表格自有它清晰理性的優勢。 在文學經典的教學和閱讀中,表格的引入更是如虎添翼。閱 讀本身就是為了信息的獲取,當文字不利于快速、便捷、客 觀的輸送信息時,將其轉換成表格就成為一種正向選擇。在 大數據時代,對于某一個作家的學術研究趨勢的分析,圖表 是最好的呈現方式。比如法國作家福樓拜,“學習通”平臺 不僅提供了近三十年各類型學術發展趨勢曲線,還有各頻道 檢索量統計表,相關學者統計表,學者機構統計表,核心期 刊統計表、基金項目統計表等,在表格的視覺沖擊下,讀者 對于是否將其作為閱讀對象將會做出更為理性的選擇。
三、結語
菲德勒認為,“一切形式的傳播媒介都在一個擴大的、 復雜的自適應系統以內共同相處和共同演進。每當一種新形 式出現并發展起來,它就會程度不同地影響其他每一種現存 形式的發展。”因此,跨媒介閱讀是大勢所趨。紙質閱讀和 數字閱讀并不截然對立,“傳統閱讀以文化為基礎,講求思 想的深邃和思維的別致,數字閱讀以技術為基礎,講求信息 的海量和鏈接的快捷。
”讀者應根據需求自由選擇適合的閱 讀方式,樹立一種多元閱讀媒介理念,引領健康有效的閱讀 行為。媒介技術只是一種工具,抵制對技術決定論的夸大, 相信經典文學閱讀在與媒介資源聯手協作中,經典的受眾群 體無論是數量還是階層都會有所改善。
參考文獻:
[1]匡文波.紙質媒介還有明天嗎[J].現代傳播,2008(4).
[2]蔣中云.思維導圖在計算機實驗教學中的應用[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3 (8).
[3]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認識新媒介[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4]朱尉.跨媒體傳播與國民閱讀方式變革[J].編輯之友,2010(9).
相關論文投稿刊物:《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月刊)曾用刊名:(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79年創刊,是新聞傳播類專業學術雙月刊。辦刊宗旨在反映廣播電視理論研究與改革的最新成果,促進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