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通志》的創(chuàng)新度探討
時間:2021年05月29日 分類:農(nóng)業(yè)論文 次數(shù):
【摘要】鄭樵的《通志》中有諸多不同于前代史學著作的創(chuàng)新之處,其中《昆蟲草木略》就能夠很好地反映出這個特點。《昆蟲草木略》第一次將動植物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編入史書之中,詳細記載了多種物類的名稱、性狀、用途等;它在具體內(nèi)容上與經(jīng)籍結(jié)合,從經(jīng)學的角度探索了動植物學的重要性,并超前性地意識到環(huán)境對于生物的影響;行文中還體現(xiàn)了鄭樵的會通思想、實學學風以及科學精神,對前人觀點批判繼承并不斷創(chuàng)新。基于以上幾個原因,《昆蟲草木略》在史學著作中具有獨特的理性意識,并在學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達到了一定高度。
【關(guān)鍵詞】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創(chuàng)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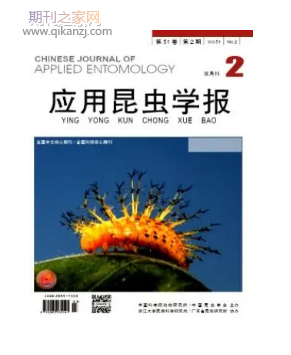
南宋鄭樵的《通志》作為一部紀傳體通史歷來褒貶不一,有人評價此書博而不精,疏漏頗多,而也有人認為其卓見明理,獨樹一幟。但不論評價如何,《通志》的創(chuàng)新性隨著后世研究地不斷深入確已逐漸被學界認可。其中最能體現(xiàn)這一特點的即為書中的二十略部分。該部分不但內(nèi)容廣括政治、經(jīng)濟、禮、樂、文字、音韻、圖譜、典籍、天文、地理、動物、植物等諸多領(lǐng)域,而且還在分類學、校讎學、博物學等方面存在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但由于長期以來學界對于《通志》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多停留在整體概括方面,而對局部的分析實屬欠缺,所以本文將從二十略中的《昆蟲草木略》入手,對《通志》中生物學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進行專門研究。
一、較之前代的創(chuàng)新
據(jù)史料所載,我國古代學者對于動植物學早有涉及,但論述主要寓于醫(yī)藥、農(nóng)業(yè)和方志等類型的著作中,而像三國時期陸機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南北朝時期的《竹譜》等生物學著作僅為鳳毛麟角。進入宋代以后,這種情況才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的生物學著作更多,涉及的生物層面更為廣泛,內(nèi)容也更加深刻,如北宋學者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記》就是現(xiàn)存關(guān)于我國西南動植物的第一本專書,全書按草木、藥、鳥獸、蟲魚分類編排,共記述動植物65種,較之前代有著更高的生物學價值。不過,如果說北宋學者刻意撰寫生物專門著作僅是有營造一門學問的傾向的話,南宋鄭樵《昆蟲草木略》的出現(xiàn),就清晰地提出了創(chuàng)立“鳥獸草木之學”的理論說明。鄭樵敏銳地意識到了古代學者對于動植物學的不屑一顧,即便是那些對生物學有所涉及的學者也“只務說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其真。
遇天文,則日此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水名;遇草木則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名,此魚名;遇鳥獸,則日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魚、何鳥、何獸也,縱有言者,亦不過引《爾雅》以為據(jù)耳,其實未曾識也”①,不求甚解,也不能跳脫前代著作的框架。于是鄭樵便有志于改變這一狀況,即通過實踐和親身觀察對動植物學進行系統(tǒng)考察。
為此,他便在夾漈山中定居,與山間野老往來,與飛禽走獸共處,將植物5類311種,動物3類142種,共計8類453種收錄在冊,區(qū)分為草類、蔬類、稻粱類、木類、果類、蟲魚類、禽類和獸類,詳細列舉出動植物的名稱、別稱、性狀、用途、價值等內(nèi)容,“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參之載籍,明其品匯”②,構(gòu)建了前所未有的系統(tǒng)完整的動植物學體系,體現(xiàn)了對動植物學前所未有的重視,并第一次將動植物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編入史書之中,在中國自然科學發(fā)展進程中起到了首創(chuàng)作用。
二、具體內(nèi)容的創(chuàng)新
《昆蟲草木略》作為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傳統(tǒng)動植物學著作,在具體內(nèi)容上的創(chuàng)新不可謂不多。它雖然繼承發(fā)展了諸如《埤雅》《爾雅》《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新修本草》等前代著作中的內(nèi)容,但也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大膽創(chuàng)新。
(一)與經(jīng)籍相結(jié)合
《昆蟲草木略》不同于前代動植物學專著專事實用與生產(chǎn),而從經(jīng)學的角度探索了動植物學的重要性。鄭樵將無涉于史學的動植物學納入二十略,其用意在于貫通生物學、《雅》學、《詩》學、《樂》學等諸多門類,構(gòu)建一個以名物之學注《爾雅》,再以《爾雅》傳《詩》,以《詩》明《樂》的治學路徑,即以實證的自然研究的經(jīng)驗和知識來重新解釋儒家經(jīng)典,繼而從治學的角度對動植物學進行深刻的探索。鄭樵認為《詩經(jīng)》的難處就在于對動植物學的認識和掌握。以《關(guān)雎》為例,他指出,“若曰‘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guān)關(guān)之聲乎?”③另外,他也敏銳地意識到,許多儒生雖然讀遍詩書,卻對田間之事一竅不通;而農(nóng)人雖熟于耕作,卻又多數(shù)不能領(lǐng)會詩書之旨。
這種知識與實踐的不對等造成了經(jīng)學與動植物學兩者的分裂,既影響了治學之人對經(jīng)籍內(nèi)容的理解與進一步詮釋,又造成歷來動植物學囿于田舍醫(yī)藥的局限。因此他主張在解讀明經(jīng)之時參考具體的動植物學知識,而《昆蟲草木略》的編寫也正反映了他這個具有革新意識的觀點:“已得草木鳥獸之真,然后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后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為之會同……夫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④可見《昆蟲草木略》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會通了動植物學與傳統(tǒng)經(jīng)學,使每一個研究領(lǐng)域的意義都不囿于既定概念,這是前代學者所未能達到的。
(二)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對生物的影響
《昆蟲草木略》中除了對動植物性狀價用進行分析之外,鄭樵還通過親身實踐和仔細觀察還得出了相當具有超前性的認識。比如他已經(jīng)意識到,環(huán)境的變化能夠?qū)ξ锓N產(chǎn)生變異的影響。比如,他在介紹“垣衣”時談道:“垣衣曰昔邪,曰鳥韭……有數(shù)種生于屋上,曰‘屋游’;生于屋陰,曰‘垣衣’。在井中者謂之‘井中苔’,在墻上抽起茸茸者,謂之‘土馬’……”⑤這就明確地區(qū)分了垣衣生在不同的環(huán)境與位置之下性狀的差異,而不是單純記錄垣衣的普遍性狀,或者忽略環(huán)境影響直接將垣衣的不同形態(tài)歸為植物的不同種類。這不禁讓筆者聯(lián)想到進化論的奠基者達爾文和他震動當時學術(shù)界的《物種起源》。
達爾文通過環(huán)球考察,搜集大量有關(guān)動植物演變和發(fā)展的科學資料,提出了生物進化的主導力量是自然選擇的觀點。生物經(jīng)常所發(fā)生的微細的不定變異會通過累代的選擇作用。適者能夠生存,并逐漸累積有利的變異發(fā)展成新種;而不適于外界環(huán)境條件的則會被淘汰。鄭樵在達爾文得出結(jié)論之前700年就已經(jīng)對這方面有所覺察,實屬難能可貴。
三、思想精神的創(chuàng)新
《昆蟲草木略》之所以具備相當突出的創(chuàng)新性,不僅得益于宋代較為寬松的學術(shù)氛圍,更取決于鄭樵獨特的會通思想、實學學風以及科學精神。遍觀《通志》可知,“會通”這一思想可以說貫穿全冊。 而這一觀念在二十略中更是得到了高度體現(xiàn)。鄭樵曾自豪地說:“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shù)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⑥事實也的確如此,二十略包括了學術(shù)的各個領(lǐng)域,雖不乏對前人學術(shù)成果的繼承,但也其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富有創(chuàng)新性的論斷。
他不但將這些不同領(lǐng)域的內(nèi)容分門別類地編入《通志》,還創(chuàng)造性地將其融合交織,互相印證或輔助理解。除了前文提到的編《昆蟲草木略》以明《詩經(jīng)》之外,鄭樵還在《圖譜略》中對昆蟲草木學進行了完善。因其較前人更注重在圖像記錄方面開展動植物學研究,所以更便于讀者直觀地認識那些較為生澀抽象的自然之理。這樣的認識在宋代重辭章、講義理的時代背景之下,有著相當罕見與大膽的創(chuàng)造性。求實思想在鄭樵的著作中也有著相當重要的體現(xiàn)。
在他生活的時代“學者操窮理盡性之說,以虛無為宗,實學置而不問”⑦,空疏學風盛行于世。鄭樵就十分反對這種虛無不切實際的學風。他尖銳地指出:“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采。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
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于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⑧并將義理之學、辭章之學相對立的求實學風提出來,主張不要對書本所言輕易迷信。他認為書中的內(nèi)容帶有作者較強的主觀性,難免與事實有所偏差,如果不通過實踐檢驗便不足為信。他在《寄方禮部書》中說:“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謂讀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回萬復,亦無由識也。”⑨讀書人如果一味抱定書本,當然就很難獲得真正的知識。
昆蟲論文投稿刊物:《昆蟲學報》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中國昆蟲學會共同主辦的昆蟲學學術(shù)刊物,1950年創(chuàng)刊,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2002年起由季刊改為雙月刊。本刊為全國核心期刊,2000年獲中國科學院優(yōu)秀期刊二等獎,2001年被評為中國期刊方陣雙百刊物,曾被SCI收錄,現(xiàn)被《中國學術(shù)期刊文摘》、《中國生物學文摘》、美國《生物學文摘》(BA)、美國《昆蟲學文摘》(EA)、美國《化學文摘》(CA)、俄羅斯《文摘雜志》(AJ)、英國CAB文摘數(shù)據(jù)庫和德國的“ISPI Pest Directory Database”等國內(nèi)外重要文摘和數(shù)據(jù)庫收錄。
這種認可實踐出真知的看法反映在了以《昆蟲草木略》為代表的文字中,說明鄭樵具有相當清醒的頭腦與思維判斷能力,同時兼具超前的理性意識和科學精神,而這對習慣于循規(guī)蹈矩研習明經(jīng)的宋代學者而言,確實具有相當大的挑戰(zhàn)性。基于以上兩種思想,鄭樵的著作自然就較同時代的其他學者更具科學精神,更注重百科知識的記錄與進一步完善,也更側(cè)重對原有認識觀點的批判繼承,從而使《通志》在學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注釋:
①⑧⑨(宋)鄭樵:《夾漈遺稿》卷二《寄方禮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②⑥(宋)鄭樵:《通志·總序》,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③④⑤⑦(宋)鄭樵:《通志》卷七五《昆蟲草木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作者:李啟豪
- 種質(zhì)資源保護和育種創(chuàng)新現(xiàn)狀及發(fā)展對策以湖南、海南兩省為例
- 江蘇河蟹產(chǎn)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現(xiàn)狀與趨勢研究
- 新形勢下茶企經(jīng)濟管理的創(chuàng)新策略
- 大學生農(nóng)產(chǎn)品電商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模式與實踐
- 農(nóng)業(yè)工程科技創(chuàng)新與中國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研究
- 德芙巧克力品牌策劃
- 5G應用創(chuàng)新與6G技術(shù)演進
- 關(guān)于電力農(nóng)網(wǎng)工程管理模式的創(chuàng)新與運用探討
- 林木種植創(chuàng)新在林業(yè)建設(shè)中的重要性分析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hù)SS
- 2025-01-22語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guān)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nèi)容?
- 2025-01-24醫(yī)學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