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莊子·齊物論》中的“天籟”
時間:2020年07月24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
【提要】《莊子》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哲學著作,其中以《齊物論》篇最能體現莊子的思想。“天籟”是《齊物論》開篇第一個提出的要點,然而莊子對于“天籟”卻只留下了“怒者其誰邪?”這樣模棱兩可的描述,故而史上為此作注者也爭論不休。本文擬從《齊物論》行文邏輯入手,以《莊子》讀莊子,進而對“天籟”的旨歸進行探討,望能拾得一點真意。
【關鍵詞】莊子天籟行文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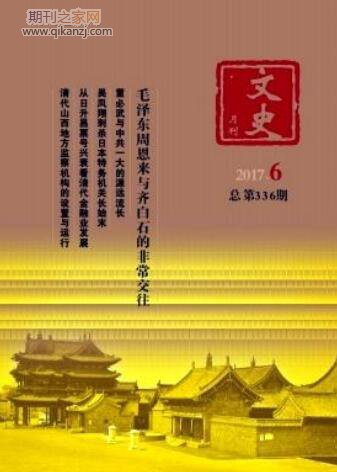
一、“天籟”的幾種解說
從各家對莊子的注解來看,對“天籟”的爭論大體可就“天籟”是否是外在于“人籟”“地籟”具體可感的存在而言分為兩派。
(一)“天籟”在“人”與“地”之中
主張“三籟”并無不同的代表便是郭象、成玄英一派的疏注。郭象說:“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天籟”并不是在“人籟”“地籟”之外的另一種東西,“天籟”就是萬物的自然“獨化”的狀態,“天”不是役萬物以為主的造物主,你看那花開花落,春去秋來,生死無常,就是美妙的“天籟”。而成玄英在對其疏上進一步闡釋,“使其自已,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這一種把“三籟”均看作是自然狀態的解讀對后來許多注解有深遠的影響。牟宗三說:“‘天籟’義即‘自然’義,明一切自生自在,自己如此,并無‘生之’者,并無‘使之如此’者。”陳鼓應也寫道:“‘天籟’是指各物因其各己的自然狀態而鳴。可見三籟并無不同,它們都是天地間自然的音響。”張默生更是直接點明:“本節所謂天籟,是就聲音而言。雖就聲音而言,但是天籟卻是無聲;雖是無聲,而又為眾聲之所處,所以地籟里有它,人籟里也有它,沒有它,則人籟地籟也無從說起。但地籟人籟又不可違反了天籟的自性,即不可違反了自然之理。”雖然后來譯者漸漸把“天籟”解讀為一種聲音,但其意旨說明“天籟”不在“人籟”“地籟”之外的觀點并沒有改變。
(二)“天籟”在“人”與“地”之外
持另一種觀點的則有王先謙、池田知久等人,王先謙認為,所謂“天籟”,與下文“真君”應是同一個涵義,“‘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他說,“風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地籟”雖然“自取”而有不同的鳴聲,然唯一的“怒者”就是“天籟”。池田知久同樣認為“天籟”是一種在“人籟”“地籟”之上的“發起者”,他認為,“‘人籟’‘地籟’之‘自已’‘自取’的主體性不會是真正的主體性,而是通過其背后的‘怒者’即‘天籟’(亦即下文的‘真宰’‘真君’‘道’)產生出來的。”錢浩也傾向于這種觀點,他把“天籟”看作是莊子心中的“道”的實體,是“現實音聲形而上的本源”,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獨化’的狀態”。
也有學者說“籟”喻指言論。楊柳橋說:“人籟,喻分辨是非之語言;地籟,喻不存是非之語言;天籟,喻不言之言或無聲之言也。”“三籟”是言論的不同層次,“天籟”是境界最高的一種層次。劉武說“天籟”是“心動而為情,情宣于口而為言”,“天籟”即是人言。
綜上之言,對于“天籟”,學界并未取得統一的理解。那究竟何者是對的,何者是錯的呢?或者說哪一種更靠近莊子的本意呢?本文且從頭說起。
二、以“隱機”通“天籟”
要明白子綦為何要言“天籟”,首先得從故事的開頭看起。“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于是子游問他:“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游見到子綦“荅焉似喪其耦”的樣貌,發出了疑問:這是為什么吶?一個人的形體確實可以使其像干枯的樹木一般沒有生氣,但是一個人的心難道也確實可以使它像完全熄滅的火灰嗎?“荅焉”,即形容子綦是一副好像什么都不記得什么都已忘卻的樣子。“似喪其耦”,陳鼓應在《莊子今注今譯》中寫道是指“精神活動超越于匹對的關系而達到獨立自由的境界”,“耦”作“偶”,“通常解釋為精神與肉體為偶”。然而若是子游已看出子綦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又有何發問的呢?后文子綦又何以答“汝知之乎?”因而事實上子游并不知道子綦發生了什么變化。
那么子綦到底在做什么呢?就得從“隱機”講起。“隱機”,成玄英疏“憑幾坐忘”,也就是把“機”通作“幾”,《說文》解“幾,坐所以憑也”,意指席地而坐用的坐具。李勉說:“‘機’為靠椅,似床,可以靠背而坐臥。《禮記》曾子問‘遂輿機而往’,《疏》云‘機者,狀如床’,可資為證。”如此,將“機”解作坐具,則“隱”作依據、憑借意思可解。
《莊子·達生》篇說:“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雖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一只斗雞最盛的狀態是什么?不是其反應多么敏捷,其姿態多么兇狠,而是“呆若木雞”,如此“其德全矣”。因而收斂于內則若“大音希聲”,“鼓琴”“考石”反損其道矣。據此,有學者認為這里的“機”可通道教對于“機”的解釋,作樞紐講,理解為“事物變化的關鍵、征兆、跡象、機會、時變”,從而將“隱機”看作是一種精神狀態。如《陰符經》中的“動其機,萬化安”、《悟真篇淺解》中的“了了心猿方寸機”,都將“機”作變化之樞紐而言,從而認為“隱機”者,“隱去生機,淡化外在,精神內守”,是得道的體現。釋德清也說:“要人悟自己言之所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之言,如風吹竅號,又何是非之有哉!”筆者認為單從這種解釋而言,似有點自圓其說之感,畢竟“機”與“機”舊是兩個字,“機”指的是榿木樹,是一種木頭的名字,《說文》“機,機木,從木,幾聲”,“單狐之山多機木”,“春機楊柳”等都表明“機”本來只是木頭的名字,而“機”的含義才應作樞紐解。《莊子·至樂》篇云:“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然此番解說,“隱機”者,似隱去了外在的生命氣息,并不與后文所傳達的意思沖突,或云莊周一語雙關,也未嘗不可。莊子此言本意是指子綦依靠著案幾而坐,然同時也暗含其隱去“心機”之境。故而亦可以換一種說法:“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幾者也。”
三、“吾喪我”與“天籟”
明白了“隱機”所指之后,那么就會產生一個疑問,今昔不同之處具體是什么呢?根據子游的發問,很明顯可以得到——同時也是“天籟”一段旨在說明的一個中心問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如今“隱機者”是“心如死灰”了。那么從“心”出發來看待子綦的回答“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立即就能領會“吾喪我”便是對這個問題的直接回答。“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斗”,他們睡覺的時候精神交錯,醒來也形體不寧,與外界糾纏不清,整日把“心”拿出來爭斗,最后“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隱機”便是修心,只有把那個處處為“我”的心守住,才能與道相合。到這里,答案已經出來了:吾喪我而后心便如死灰。子綦說,我現在達到了一種“吾喪我”的狀態啊,因此你看到今天的我和以往的我不一樣了。
既然有了答案,那為何子綦還要說“人籟”“地籟”“天籟”呢?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1.先有“吾喪我”而后“聞天籟”;2.先“聞天籟”而后方可“吾喪我”。
(一)“喪我”后才能聞“天籟”
“喪”意指喪失,丟棄,失去,《說文》解:“喪,亡也。”《孟子·告子上》言:“非獨賢者有是心,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耳。”子綦丟掉的“我”是什么呢?陳鼓應認為:“‘喪我’的我指偏執的我,‘吾’即真我,吾喪我即摒棄我見,由‘喪我’而達到忘我、臻于萬物一體的境界,與篇末‘物化’一節相對應。”方東美說:“‘喪我’,也就是要喪小我,忘小我,而成就大我。”林逸希言:“吾喪我三字下的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這說明學界對于“吾喪我”基本有著統一的認識,皆是言舍棄了主觀之“我”,忘記了是非成見的狀態。
按第一種邏輯,若先得“吾喪我”之狀態,則可依王雱“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唯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由于我本與萬物同根,因此請丟掉這個“我”。正如《秋水》所寫“‘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子我相對立,魚我相對立,故而惠子云不知也,然我亦非道,何能知道?故不知者,在“我”也。今者子綦“喪我”,而后知“天籟”,故可知“人籟”“地籟”“天籟”并無不同。王孝魚說:“所謂人籟也,當與地籟無殊。”這表明“三籟”其實都是說自然產生的、沒有成見的言論。因而“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在此種邏輯下應做如下理解:你聽過人吹的樂器的聲音,你還想要聽大地的樂器的聲音,你聽過大地的樂器,你還想聽那無上的樂器的聲音哩!“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則是說吹奏這種種樂器,言“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不過都是“自取”,使我們這樣做的又是誰呢?言外之意便是“吾喪”之“我”。《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而“人籟”法“地籟”,“地籟”法“天籟”。正如馮友蘭所提:“《齊物論》在這里并不是提出這個問題尋求回答,而是要取消這個問題,認為無需回答。”“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萬物形殊而道為一,何必苦苦追問“人籟”“地籟”“天籟”呢?唯有“知止”,方能達“至人”之境。
(二)因“天籟”而“喪我”
若按第二種邏輯,“聞天籟”是進入“吾喪我”的工夫,則解“天籟”成為了重點,明白了“天籟”是什么就可以修得“喪我”之境界。“籟”者,古之樂器,《說文》“三孔龠”,《史記·司馬相如傳》“吹鳴籟”,集解“籟,簫也”,《滕王閣序》“爽籟發而清風生”,意思是排簫的聲音引來徐徐清風。“天”者,至大無上也,《說文》:“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而從“天地人”三者層次而言,無疑“天籟”是最高一級,那么要解“天籟”,需得從“人籟”“地籟”入手。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而子綦回答之關鍵就在于“怒者其誰邪?”很好理解,“人籟”是人所吹奏的樂器,“怒者”自然是人;“地籟”是大地所吹奏的樂器,“怒者”即是風;那么“天籟”是天所吹奏的樂器,“怒者”自然是天。若天是這“天籟”的吹奏者,則天下萬物自然就是這“天籟”。《老子》中也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天地之間就好像一個風箱!不正是與“天籟”異曲同工嗎?后文“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不正是世間眾生貌嗎?或者如止庵所言:“天籟在地籟、人籟中。
地籟人籟都是物,天籟是體現于其中的自然狀態。”子綦所強調的并非這“天籟”是何種樂器,而是欲明這“天”之自然無為意。“《莊子》為強調‘咸其自取’,與有待于人、有待于風的不同而提出‘天籟’,以區別‘人籟’、‘地籟’,實則‘天籟’也可以涵蓋‘人籟’‘地籟’。”“人籟”者待人,“地籟”者待地,“天籟”者待天,故而有“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事物的是非關系皆是“天倪”,何必要“彼所非明而明知,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世間各人各種不同的說法,不過是像山間的空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因風而作,“風濟則眾竅為虛”,所待者皆天也。正如景答罔兩:“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我所依賴的都是“天然”罷了,我哪里知道所以然呢?“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將“天籟”解讀為世間萬物,則是這第二種邏輯的解答。
四、“天籟”的全體性即解讀之統一
筆者此時對“天籟”一段行文邏輯稍作了解讀,從而得出了“天籟”之“我見”,發現似乎與前人解讀又有不同。因而是時候回到本文第一節之問題——千萬解讀孰更接近莊子?答曰:“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莊子所言者,“道”也,非言辭也。是故有云“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當我們的關注點在于言語的修辭時,就忽視了言下之意,所謂“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是道外之物也。勞思光說:“一切理論之建立,皆必受一定之限制。無論思考中之解析,或知覺中之綜合,皆為永不完成者……故任何一理論成立時,所顯示之‘是非’皆不能與‘最后之真’相符。”這正是“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之理。
文史論文投稿刊物:《文史月刊》辦刊宗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變遷,深刻揭示發展運作規律,積極而又生動具體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設置欄目有:新語絲、世紀回首、共和國腳步、人物與回憶、特殊年代、鄉俗民情、民國殘頁、考證與爭鳴、愛國者之歌、神州攬勝、崢嶸歲月、長卷連載、熱門考場、書刊擷英、文壇藝界、編讀之間、文史博覽。
方東美先生說:“在這個一切的觀點及角度里面,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焦點,再在這焦點上面,把一切思想對立的差異,統統匯集到此一共同焦點,然后從這個共同點再回看各種理論系統,而后發現,各種理論系統都有它存在的價值,都有它相對的理由,也因而可以容納各種不同系統的見解。”正如“荃魚”之比,“天籟”之比于《齊物論》而言,亦是以明其意而已。或按第一種邏輯解,則明物我為一也,“我”自己樹立起成見是非之心,因而觀萬物不得其解,有成必有虧,“暮四”則必“朝三”,因而“致虛極,守靜篤”方能近道;或按第二種邏輯解,則明孔竅萬殊皆因風起,《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言無是非,宮商不同皆是音也,因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而從莊子所想表達的意思而言,“天籟”是千人千面,解讀亦是千人千語,顧此失彼非緣道行。故而此二解亦無孰是孰非,皆是“天籟”之意一也。
總之,緊扣莊子的《齊物論》以及道的思想而言,“天籟”可以視作闡明萬事萬物全體性的一種喻體,體現了“道”至大無外的特點。
作者:唐晨中真義梟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