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暴力視域下看林京子的原爆文學(xué)
時(shí)間:2021年10月09日 分類: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內(nèi)容摘要:羅伯·尼克森融合后殖民與生態(tài)批評(píng),在著作《慢性暴力與窮人的環(huán)境主義》中提出慢性暴力這一理念。 就倡導(dǎo)環(huán)境正義、對(duì)抗歷史記憶的風(fēng)化而言,原爆文學(xué)與慢性暴力不謀而合。 本文力圖從慢性暴力的視角解讀日本當(dāng)代女作家林京子的原爆文學(xué)作品,通過對(duì)比早、晚期文學(xué)作品進(jìn)而分析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特點(diǎn)及思想歷程的轉(zhuǎn)變。
關(guān)鍵詞:慢性暴力 原爆文學(xué) 林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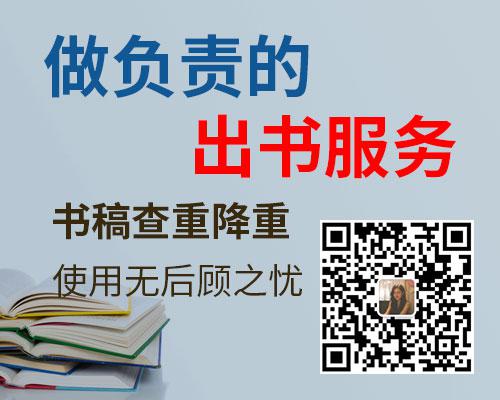
世界首次核試驗(yàn)爆炸于1945年7月16日發(fā)生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托立尼提市的郊外,截止到各國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yàn)條約》的1966年,全世界范圍內(nèi)約進(jìn)行了兩千多次的核試驗(yàn)。 在《條約》正式生效之后的十年內(nèi)依然進(jìn)行了六次核爆試驗(yàn)。 核爆所伴隨的核放射有著難以想象的破壞力,給當(dāng)?shù)丶暗厍蛏鷳B(tài)帶來了難以預(yù)估的影響。 然而一般民眾對(duì)于核事件的認(rèn)知,大多停留在1945年的廣島·長崎核爆事件,或是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事件。 以核爆為例,文人作家訴諸筆端以文字為武器書寫核的非人性化,很大程度上推動(dòng)了對(duì)核爆的認(rèn)知。
文學(xué)方向論文范例: 交織的藝術(shù)淺析文學(xué)著作影視化的現(xiàn)象
繼原民喜,大田洋子等第一代原爆文學(xué)作家之后,被譽(yù)為日本當(dāng)代文壇的“礦山云雀”的林京子(1930-2017)的創(chuàng)作多以八月九日長崎事件為出發(fā)點(diǎn),著眼于當(dāng)今社會(huì)身處困境中的幸存被爆者的現(xiàn)狀,在日本原爆文學(xu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以本名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作品《祭場》問世之后,一舉斬獲群像新人文學(xué)獎(jiǎng)、芥川龍之介文學(xué)獎(jiǎng)兩項(xiàng)大獎(jiǎng),得到井上靖、大江健三郎等文壇前輩的青睞。 以少年時(shí)上海經(jīng)驗(yàn)為題材創(chuàng)作的《上海》獲得了當(dāng)年的女流文學(xué)獎(jiǎng),次年憑借《三界之家》獲川端康成文學(xué)獎(jiǎng),之后接連斬獲多項(xiàng)文學(xué)大獎(jiǎng)。 作為核武器受害者的林京子始終以書寫原爆為己任,向世界傳達(dá)核的非人道性以及其暴力所在。
歲月流逝,核事件漸漸淡出了大眾的視野,但核輻射所引發(fā)的社會(huì)、生態(tài)問題依然嚴(yán)峻。 羅伯·尼克森在《慢性暴力與窮人的環(huán)境主義》一書中結(jié)合生態(tài)批評(píng)與后殖民批評(píng)提出“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這一理念,指的是那些發(fā)生緩慢、時(shí)常為人所忽視的威脅,這種威脅超越時(shí)空的束縛,以一種暴力的形式隱性存在。 是一種損耗性的暴力。 [1]比起海嘯、火山爆發(fā)等時(shí)間維度較短,效果駭人的大事件,尼克森關(guān)注的是無法瞬間引起轟動(dòng)性效應(yīng)的,但隨著長年累月的積累同樣能夠引發(fā)毀滅性變化的一系列環(huán)境災(zāi)難,如:核輻射。 自1948年起,美國曾在西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現(xiàn)已獨(dú)立)進(jìn)行了67次核試驗(yàn),其中輻射量最大的一次約廣島事件的一千倍。 時(shí)至今日,“水母寶寶(jellyfish babies)”的噩夢依然縈繞在馬紹爾群島,而相關(guān)歷史記憶早已被遺忘。 為了具象化慢性暴力,尼克森著眼于非歐裔環(huán)境作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呼吁關(guān)注那些被忽視的環(huán)境暴力問題。 為窮人們的環(huán)境正義正言。 從慢性暴力的視域下分析林京子原爆文學(xué)作品中暴力的表現(xiàn)形式及變化,有助于進(jìn)一步把握原爆于人類于生態(tài)的影響,拓展原爆文學(xué)的生態(tài)意義。
一.慢性暴力與原爆文學(xué)
在普遍認(rèn)知中,暴力多指向?qū)θ祟愔苯釉斐扇怏w或心理傷害的作為,中斷或限制了人類基本需求如生存、自由,例如恐怖襲擊、火山爆發(fā)等顯然易見的直接暴力。 氣候變化、化學(xué)性污染、核輻射等一系列的環(huán)境災(zāi)害,雖不能瞬間造成極具轟動(dòng)性的變化,但是隨著歲月積累同樣能夠給人類社會(huì)、自然生態(tài)帶來毀滅性的破壞。 但遺憾的是,時(shí)常為人所忽視。 羅伯森強(qiáng)調(diào),和平學(xué)者加爾通所提出的結(jié)構(gòu)暴力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引發(fā)暴力行為的原因及其行為主體,事實(shí)上暴力,尤其是生態(tài)暴力,不僅要和空間、身體、資源做斗爭,更是與時(shí)間的斗爭。 [2]25總的來說,慢性暴力有以下四個(gè)特點(diǎn):發(fā)生緩慢、隱性破壞力、延遲性影響、隨時(shí)間流逝衍生其他暴力。 曾處于美國占領(lǐng)統(tǒng)治之下馬紹爾群島,在短短十年之內(nèi)經(jīng)歷了大大小小共計(jì)67次的核爆試驗(yàn)。 其中比基尼群島海域附近的原子彈核試驗(yàn)引發(fā)的“第五福龍丸號(hào)事件”掀起了日本全國范圍內(nèi)的反核運(yùn)動(dòng),更加速了以核的和平利用為主題的原發(fā)文學(xué)的誕生。
約翰·惠蒂埃在《書寫歸零點(diǎn)—日本文學(xué)與原爆》一書中提到“這場論爭所涉及到不只是暴力的規(guī)模……(略)如果考慮到放射性物質(zhì)污染以及被曝的遲緩又微妙的影響,人類受到的傷害從未得到精準(zhǔn)的計(jì)算”,“傳達(dá)暴力、書寫暴力成為了原爆文學(xué)最重要的兩大主題”。 [3]5廣島·長崎事件之后的數(shù)十年,原爆文學(xué)早已成為了核時(shí)代的文學(xué),在文學(xué)史上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 早期的原爆文學(xué)作品多以作家本身的被爆體驗(yàn)為出發(fā)點(diǎn)紀(jì)實(shí)性地描寫了原子彈剛投下之后的人間慘狀。 進(jìn)入發(fā)展期,原爆暴力這一事實(shí)逐步被大眾接納,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作品主要描述了核爆所衍生出的個(gè)人、社會(huì)問題,井伏鱒二《黒雨》、井上光晴《地上的一群》等作品大放異彩。 最后,以大江健三郎、安倍公房為代表的作家圍繞著核時(shí)代下人類的命運(yùn)該何去何從創(chuàng)作了多部引人深思的佳作。 在時(shí)間的洗禮之下,原爆文學(xué)逐步被大眾文學(xué)所接納,原爆文學(xué)研究也立足于生態(tài)批評(píng)將目光轉(zhuǎn)向核輻射污染問題逐步展開了新的研究局面。 不變的是,與暴力記憶的風(fēng)化做斗爭這一姿態(tài)依然強(qiáng)硬。 故而,無論是環(huán)境正義的倡導(dǎo),還是對(duì)抗歷史記憶的風(fēng)化,原爆文學(xué)與慢性暴力可謂是不謀而合。
1945年8月9日,15歲的林京子在三菱兵器大橋工廠(距離原子彈爆炸中心約1.4km)勞動(dòng)做工,迎來了“命運(yùn)之日”。 盡管同普通人一樣結(jié)婚、生子,但從那一天起林便背負(fù)上了被爆者、核武器受害者的身份,最終也因此婚姻破裂。 離婚后迫于生計(jì)的林京子不得已開啟了職業(yè)寫作生涯,其創(chuàng)作基本圍繞著上海體驗(yàn)、被爆體驗(yàn)、戰(zhàn)后體驗(yàn)等三大方面進(jìn)行,攬獲了以當(dāng)代作家為對(duì)象的多項(xiàng)文學(xué)獎(jiǎng)。 放眼國內(nèi),對(duì)林京子文學(xué)作品的研究論文成果較少,其中以介紹性文章,以及對(duì)其上海體驗(yàn)相關(guān)的文學(xué)作品的研究占據(jù)了多數(shù)1。 故本文分別從選取林京子早、晚期文學(xué)作品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祭場》、《陰天的行進(jìn)》、《收獲》等,通過分析慢性暴力的作用形式及其變化以窺林文學(xué)創(chuàng)作特點(diǎn)及其思想歷程。
二.言說慢性暴力與創(chuàng)傷
不同于原爆后即刻書寫個(gè)人被爆經(jīng)驗(yàn)和見聞的紀(jì)實(shí)性作品,《祭場》的視角不停轉(zhuǎn)換在長崎被爆少女與三十年后的幸存者之間,生動(dòng)地還原了8月9日長崎的人間煉獄的同時(shí),傳達(dá)了被爆幸存者的人生經(jīng)驗(yàn)。 《鉆石玻璃》講的是被爆者的“我”應(yīng)友人西田的邀請(qǐng)一同前往長崎看玻璃工藝品,卻因店家的一句話—如今的長崎早已沒有完好無損的玻璃器皿,意外變成了尋找“完好無損”的故事。
原子彈爆炸往往伴隨著強(qiáng)烈的沖擊波,導(dǎo)致周圍物體高速飛濺。 《祭場》中,“我”的友人幾乎被飛濺的玻璃殘?jiān)闪舜题呐率侨曛蟮默F(xiàn)在她的體內(nèi)依然殘留著不少,這些殘?jiān)杂尚凶咴谒纳眢w里。 友人前往醫(yī)院取出體內(nèi)殘?jiān)t(yī)生說道:“它們是屬于你的勛章,留著吧”。 [4]24雖然只是一句玩笑話,對(duì)于被爆者而言體內(nèi)的玻璃殘?jiān)烤瓜笳髦裁措y以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被爆者的醫(yī)生又或是普通民眾無法想象被爆者所經(jīng)歷的苦痛。 盡管時(shí)光荏苒,刻在身體里的“勛章”所帶來的痛楚卻絲毫不見緩解,時(shí)時(shí)刻刻提醒著友人那段創(chuàng)傷記憶。
除了肉眼可見的外傷以及燒傷之外,原子彈爆炸產(chǎn)生的核輻射所引發(fā)的原爆癥,例如急性、慢性的輻射病、白血病,各種癌癥等令被爆者苦不堪言。 《陰天的行進(jìn)》中寫道被爆者一年需完成兩次健康體檢,血液檢查必不可少,若是血液檢測結(jié)果不如人意,有必要進(jìn)行更精密的檢查。 “總是擔(dān)心鼻子會(huì)不會(huì)突然大出血,每個(gè)月的生理例假一來更害怕就這樣血流不止”2(133),被爆者終日生活在“血流不止就此逝去”的恐怖之中。 多年以來,原爆癥帶來的身體上的痛苦和情感上的恐懼一直折磨著友人汀子,她最終因血流不止而撒手人寰。 “汀子睡在孩子的被褥上,臉頰像以前一樣閃著白色,與健康的人沒什么兩樣。 受夠了! 是時(shí)候該讓我們擺脫原子彈爆炸這一痛苦的過去了吧(149)”。 看著瀕死的友人的臉龐,作者不禁吐露出了她的真實(shí)想法。 對(duì)于在痛苦的地獄中掙扎的幸存者來說,死亡便是解脫嗎? 對(duì)此,在《祭場》中林極其客觀冷峻地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原子彈爆炸,即刻死亡最好不過”。
廣島·長崎事件的幸存者往往被貼上了“原子彈疾病患者”和“受害者”的標(biāo)簽。 幸存者又如何看待自己? 《鉆石玻璃》描繪了幸存者不懈地與“核”和“死亡的恐懼”作斗爭,但壽命越長其罪責(zé)感卻愈發(fā)沉重。 正如店主所言,“踏破鐵鞋,長崎也找不到一件完整的物件”(196)。 殘缺的不僅是物件,在幸存者的自我認(rèn)知中自己也是一件壞了的東西。 “那是一段無法忘卻的過去,但是直到我看到眼前的玻璃磚,我才有意識(shí)地試圖成為一個(gè)普通的旅人,單純路過”(208)。 作為主人公的“我”想要拼命忘記1945年8月9日的一切,只是一個(gè)旅人(非被爆者)以客觀的視角穿過家鄉(xiāng)的街道。 對(duì)于始終找尋著自我的幸存者而言,時(shí)間也許可以治愈外傷,卻無法治愈精神創(chuàng)傷,反而讓她們?cè)谧晕覒岩珊妥晕曳穸ǖ囊庾R(shí)困境中越陷越深。
原爆這一暴力體驗(yàn)不受時(shí)間束縛,始終以一種慢性暴力的形式侵蝕著幸存者的身心。 在時(shí)間維度上未能達(dá)到立竿見影效果的慢性暴力,其隱性破壞力不言而喻,時(shí)間的流走還衍生出了其他的暴力形式,例如社會(huì)歧視。 幸存者恐懼周圍異樣的眼光,為了掩蓋過去,拒絕作為證人按下有自己名字的印章,拒絕領(lǐng)取被爆者手賬。 “原子彈幸存者的歷史不是一種榮譽(yù)。 還牽扯到了遺傳問題,如果可以的話想盡可能地隱瞞下去”(《祭場》34)。 歷史的車輪滾滾,苦于暴力體驗(yàn)的幸存者逐漸被公眾所遺忘,甚至成為嘩眾取寵的手段。 “《斯貝爾星人》中人類打扮的“被爆星人”全身呈燒傷狀”(33)。 出版商將幸存者比作“外星人”漫畫無疑能收獲更多的關(guān)注度,也間接證明了很廣島·長崎事件正在逐漸風(fēng)化。 對(duì)此,林寫道“這很好,無論是漫畫還是小丑,總算還有人在關(guān)注我們”(33)。 對(duì)于長崎原爆,林京子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以求客觀全面。 貶低也好歌頌也罷形式都無關(guān)緊要,只望銘記史實(shí),這便是林京子真正想要傳達(dá)的吧。
《陰天的行進(jìn)》將目光轉(zhuǎn)向幸存者的家庭,描繪了核爆受害者的妻子需定期體檢,又擔(dān)心孩子的健康會(huì)受到影響,對(duì)此普通人的丈夫難以理解妻子的不安,冷言相待的故事。 精神困境中的被爆者女性傾向于否定懷疑自我,除了執(zhí)拗于自我完整性之外,無法成為合格的母親也是緣由之一。 當(dāng)代著名創(chuàng)傷研究學(xué)者凱西·卡魯斯談到創(chuàng)傷的代際傳遞性,她認(rèn)為“創(chuàng)傷在猶太一神教中被延遲的經(jīng)歷表明歷史不僅是危機(jī)的傳遞,而且也是幸存的傳遞,這種幸存只有在一個(gè)比任何個(gè)人或者一代人更大的歷史中才能被擁有”。 [5]核爆不僅在被爆者女性的身體上刻下了傷痕,在被爆二世也留下了創(chuàng)傷。
面對(duì)孩子,身為母親的幸存者總是為自己被爆者的身份感到愧疚。 為了兒子,主人公的“我”決定領(lǐng)取被爆者手賬,瀕死的汀子為了不讓兒子看到自己最后一刻的丑陋,寧死不見最后一面。 對(duì)于身為人母的幸存者而言,“關(guān)于母親的記憶,留給孩子一個(gè)溫暖的微笑就好”(151《陰天的行進(jìn)》),無疑是一個(gè)低微又充滿暖意的愿望。 然而具有強(qiáng)大破壞力(遺傳影響)的核輻射無情地切斷了母子羈絆。 “我們幸存者的骨頭,勉強(qiáng)維持了人的樣子,支撐著我們的背部,脖子,四肢,但是用手指一壓就知道,它們脆弱到能夠會(huì)碎成沙子”(130),單就外觀而言,被爆幸存者及其后代與普通人并無區(qū)別。 然而幸存者自身很清楚,自己并非普通人那般健康。 尤其是女性幸存者,擔(dān)心自己能否懷孕,自己的不幸是否會(huì)遺傳后代。 “如果不幸在第一代幸存者就能夠結(jié)束中,我甘心放棄只當(dāng)自己時(shí)運(yùn)不濟(jì)。 但是,那道閃光使得人類遺傳基因畸變,甚至給第二代、第三代人帶來痛苦。 就在無辜的孩子們的生命里埋下相同苦痛的種子這一項(xiàng)罪行,我們需要向孩子們致歉”(143)。
三.慢性暴力與環(huán)境正義
縱觀林京子的原爆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難發(fā)現(xiàn)林始終將自己看作是“8月9日的講述人”,小說大多都以“我”的第一視角展開敘述。 早期作品《祭場》、《鉆石玻璃》也不例外,盡管《陰天的行進(jìn)》中包設(shè)定了非被爆者西田這一角色,但故事的展開始終以“我”的敘述展開。 然而,林后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收獲》把目光集中于非被爆者的山田老人和兒子的身上,第一次采用了第三人稱視角。 視角的轉(zhuǎn)換得益于三位一體核試驗(yàn)遺址之旅,以這次旅行的經(jīng)歷為材料創(chuàng)作的《長時(shí)間寫成的人生記錄》寫道:“直到現(xiàn)在,我一直認(rèn)為地球上首個(gè)核受害者是我們?nèi)祟悺?不,被爆者的前輩! 在這里。 無法哭泣無法呼救的這片土地”。 [6]
遺址之旅使得林京子重新認(rèn)識(shí)了核的本質(zhì)—核武器受害者不僅限于人類,腳下的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無數(shù)動(dòng)植物同樣也是被曝的受害者。 《祭場》中提到“但是,據(jù)報(bào)道,受輻射的影響細(xì)胞分裂異常。 蓖麻缺乏葉綠素長了白斑。 葉子變形或是卷曲。 在當(dāng)時(shí)的長崎,經(jīng)常報(bào)告雙胞茄子,雙胎南瓜,番茄株上綴滿鈴鐺一樣的果實(shí),還有其他畸形植物”(42)。 “如果語言相通的話好想聽聽這些植物的感想,太滑稽了(48)”,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林來說,變形的葉子只能被認(rèn)作是途中的異樣的風(fēng)景或某種科學(xué)現(xiàn)象。 三位一體遺址歸來的兩年后,基于東海村JCO臨界事故的采訪而創(chuàng)作的《收獲》充分證明了林京子核意識(shí)的轉(zhuǎn)變。
《收獲》的主人公是靠耕種為生的老人山田,故事圍繞著老人收獲芋頭的日常展開。 老人的喜怒哀樂始終被芋頭的成長牽動(dòng)著,對(duì)他來說,芋頭不是謀生的手段,更像是澆灌了愛與汗水的家人。 相較于人類的后知后覺,小狗(動(dòng)物)率先察覺到了核泄露的異常不停地吠叫。 核泄漏事故發(fā)生之后媒體蜂擁而至,喧囂過后卻僅剩老人自己關(guān)注腳下這片被污染的土地。 林以第三人稱的視角表達(dá)了對(duì)核輻射導(dǎo)致的土地污染的憂思,更揭露了核時(shí)代下底層人民的無助與困境。 一直以人類幸存者為中心堅(jiān)持創(chuàng)作的林京子,在遺址一行之后意識(shí)到第一個(gè)受核害者是那片曠野,和棲息在曠野中的蛇和植物。 敘事視角以及創(chuàng)作重心的轉(zhuǎn)變不在于核爆或是核電,而是源于林再次認(rèn)識(shí)到了核非人道、暴力性的本質(zhì)。 巖川指出剖析林京子的創(chuàng)作可以發(fā)現(xiàn),其根本在于林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了我們生活在一個(gè)核危機(jī)遍布的世界。 [7]可以說,林京子的原爆文學(xué)給予了處于核時(shí)代下的我們一個(gè)重新認(rèn)識(shí)核的本質(zhì)的契機(jī)。
花田俊典如是說,之所以有必要持續(xù)言說原爆問題,不是因?yàn)樗菤v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是因?yàn)閷?duì)于現(xiàn)在,它依然在向我們傳達(dá)其當(dāng)下的意義[8]。 林京子作為八月九日的敘述者其文學(xué)作品中一如既往的反核思想,其從書寫廣島·長崎事件的原爆文學(xué)再到關(guān)注核能發(fā)電的原發(fā)文學(xué),又或是以核為題材的核文學(xué)一批又一批的優(yōu)秀作家以文字發(fā)聲,向全世界敲響了核時(shí)代的警鐘,呼吁大眾關(guān)注核爆這一慢性暴力導(dǎo)致的社會(huì)問題,環(huán)境污染傳達(dá)生態(tài)憂思。
注 釋
1.根據(jù)中國知網(wǎng)數(shù)據(jù),林京子文學(xué)作品相關(guān)研究成果共有學(xué)術(shù)期刊論文4篇,碩士畢業(yè)論文6篇。
2.原文引用,如無具體標(biāo)注默認(rèn)與前文一致。
參考文獻(xiàn)
[1]李程.融合與碰撞:后殖民生態(tài)批評(píng)的認(rèn)識(shí)論與“慢性暴力”[J].鄱陽湖學(xué)刊,2015(01):96-102.
[2](美)羅伯·尼克森.慢性暴力與窮人們的正義[M].美國:哈佛大學(xué)出版社,2011.
[3](日)約翰·惠蒂埃·著.水島裕雅監(jiān)譯.書寫歸零點(diǎn)—日本文學(xué)與原爆[M].日本:法政大學(xué)出版局,2010.
[4](日)林京子.祭場/鉆石玻璃[M].日本:文藝文庫,2012.
[5](美)凱西·卡魯斯.無人認(rèn)領(lǐng)的經(jīng)歷:創(chuàng)傷,敘事和歷史[M].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出版社,1996.
[6](日)林京子.長時(shí)間寫成的人生記錄[M].日本:講談社文蕓文庫,2005.
[7](日)巖川亞理紗.記憶與前未來―連結(jié)林京子《祭場》和《長時(shí)間寫成的人生記錄》[J].言語科學(xué)情報(bào),2013(11):9.
[8](日)花田俊典.敘説XIX.特集.原爆的表象[M].後記.東京:花書院,1999.
作者:陳 瑤
- 中國史傳文學(xué)視域下的人才流動(dòng)觀基于《三國演義》中典型人物與事件的考察
- 新媒體視域下非遺的傳播現(xiàn)狀與策略研究以武漢天樂社相聲為例
- 文化自信視域下林語堂《莊子》英譯本研究
- 非遺視域下廣西壯族七十二巫調(diào)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 美學(xué)藝術(shù)視域下“牛皮烙畫”的設(shè)計(jì)研究
- “互聯(lián)網(wǎng)+”視域下高校學(xué)生支部主題黨日活動(dòng)有效性研究
- “健康中國”視域下常德市全民健身生活化研究
- 用戶消費(fèi)視域下的耳朵經(jīng)濟(jì)市場現(xiàn)狀及前景研究
- 媒介生態(tài)學(xué)視域下皮影藝術(shù)研究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jià)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dòng)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hù)SS
- 2025-01-22語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xué)國際會(huì)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píng)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shí)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guān)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xué)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nèi)容?
- 2025-01-24醫(yī)學(xué)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xiàn)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