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因的“游藝”之學與文藝思想兼論理學“流而為文”現象的書畫視域
時間:2021年08月09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元初理學家劉因不僅于義理之學有所自得,且致力于游藝之事,詩文創作外,在書畫琴棋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詣。他不僅明確提出了“藝是小學工夫”的理念,而且首次將作為今人之“藝”的詩文書畫與古人的“六藝”之教對接起來,進一步提升了文藝在道學事業中的地位。在“游藝”實踐中,他將“觀物”思想與格物致知精神貫徹淪浹其間;而且將自己的歸隱情志安放于藝術世界,表現出“適意玩情”的游藝態度。形神兼備的繪畫觀念和尚古的書學取向是劉因文藝美學的集中體現,但其終極旨趣卻指向同一妙境———“天”。在致事理之廣大而盡藝術之精微的努力中,劉因理學家的身份意識與文藝家的藝術素養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可見,元代理學家更為熱情地接納文藝,在詩文書畫游藝中也留下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和理論主張,更為深入地向文藝領域輸入理學的思維方式與價值理念,從而影響著元代文藝思潮走向。所以,書畫游藝之學理應被納入理學“流而為文”現象的考察視域。
關鍵詞:劉因;游藝;題畫詩;文藝思想;流而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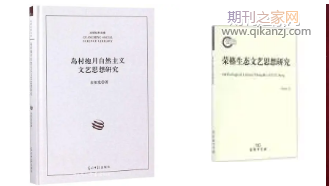
元初理學家劉因(1249—1293年),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宋濂等4008),故得“靜修先生”之號。其學術思想深受家學與北方學術環境的影響,“出江漢之傳,又別為一派”(黃宗羲3020),與許衡、吳澄鼎足而三。難得的是,劉因不僅于性理之學有所自得,且致力于詩文書畫并取得高深造詣。前人對其詩文成就已有較多關注,往往推賞其為開元代詩文風氣之先的人物。①
但他的書畫游藝實踐以及由此而呈現的文藝觀念卻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即使有學者注意到其文集中的近百首題畫詩,如王韶華《元代題畫詩研究》等,但他們主要對其思想內容作分析。而劉中玉《混同與重構:元代文人畫學研究》等雖涉及劉因的繪畫理論,但僅對其形神觀念略作介紹。有的學者甚而指出:“劉因在文藝理論上,除了形神關系外(《書東坡傳神記后》),沒有明確提出什么主張。”(黃琳31)事實上,劉因在書畫、琴棋、器物等方面的游藝活動中,提出了諸多頗具個性的文藝觀念,這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其人格性情與文藝思想的理解,也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元代理學“流而為文”的時代現象。
一、“藝是小學工夫”及新“六藝”的提出
宋代理學家普遍重視早期儒家的“六藝”之教,卻始終對詩文、字畫、琴棋等保持警惕,多認為其有妨道學事業(楊萬里139—145)。劉因的進步之處在于,他認識到了世變所帶來的“藝”之內涵的變化,首次將詩文書畫與古人的“六藝”之教對接起來,從而提升了文藝的地位。“游藝”之學是在孔子“游于藝”的基礎上被提出的,古人之所謂藝多指“六藝”之教。如劉寶楠《論語正義》引何晏注解之語曰:“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257)明確了“藝”之地位居末的基本認識,這也是北宋理學家重道輕文的主要依據。南宋理學家在濡染文藝和精思義理的過程中對“游于藝”之精神內涵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朱熹指出:“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余,而心亦無所放矣。”(《四書章句集注》94)其對“游于藝”的解讀彰顯出鮮明的格物窮理意識陸九淵高足楊簡的闡釋則頗能代表其時心學家之游藝觀念,其《論〈論語〉》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為末務而棄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于藝’,是謂‘彝倫攸敘’。”(楊簡11)可見,南宋學人多將“游于藝”闡釋為儒門需要掌握的六種伎藝,并認識到“游藝”之學雖處末端而不可或缺的意義。這些都對劉因的“游藝”觀念有著直接影響。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對“游于藝”有著詳細闡發,頗能體現其道與藝之觀念。他說:“自‘志于道’至‘依于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于仁’至‘游于藝’是自本兼末。能‘依于仁’,則其游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
[……]藝雖小學,至‘依于仁’既熟后,所謂小學者,至此方用得它。”(劉因,《四書集義精要》227)依仁為游藝之本,游藝為仁體之用。其邏輯關系在于,天體物而不遺,萬事萬物無非一理。天理流而為人文,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即仁體事無不在也,如此則游藝亦是體仁工夫。聯系其由道至仁為由粗入精的解讀來看,作為小學的“藝”終極旨歸仍在修道上。重視為學次第,是劉因學術思想的一大特點。他進一步指出:“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后,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后;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后。文中子說:圣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后藝可游也。此說得好。”(227)
他認為,就本末言,藝處“三者”之末端;然論先后,習藝作為小學工夫,又是“三者”之起點。圣人先立其本,而后游藝無所不至。作為圣人的孔子即是多才多藝的代表,對此劉因說:“蓋圣人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見,尚德不尚藝之意,其實圣人未嘗不多能也。”(256)孔子以其多能固能成圣,又因其大本既立,故其于藝能自可從容潛玩,多出一份圣人氣象。劉因又說:“圣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
只且如禮,圣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255)由此可見,劉因對“游于藝”的解讀在繼承前人基礎上又有所推進,明確提出“藝是小學工夫”的主張,進一步肯定了游藝之學在道學事業中的階梯意義。如果僅是將“游藝”之學停留在傳統的“六藝”之教上,雖極力逼近孔子“游于藝”的本意,但仍具有時代的局限性。劉因的超越之處在于,他對于世變而“藝”亦變的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并努力將古今之藝對接起來,作出更具實際意義的延伸。劉因在《敘學》中說:孔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
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靜修先生文集》6)他認為,古今之藝的內涵在當時已有所不同,古之藝已不適宜當下的時代環境,今之士人所崇尚的是詩文字畫,或可謂之為文人化之后的新“六藝”。士不可不游藝,古今同然,今之藝華國、藻物、飾身的作用不可忽視。文之于國而言自是一種盛世祥瑞的象征,所謂“天畀以文,用瑞斯世” (《靜修先生文集》89)。
于物之美與身之修而言,藻飾之文亦無所不在。可見,劉因對“游藝”之學審美功能的推崇,“超越了理學家的眼界,突破了傳統儒家文藝觀念,是很有美學理論價值”(張晶70)。有學者指出:“他把歷來為儒者賤視的‘詩、文、字、畫’所謂‘末技’‘小道’與孔子重要的教育內容‘六藝’也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同,以‘六藝’為‘古之藝’,而詩文書畫則是‘今之藝’。‘六藝’對古人有多重要,詩文書畫對今人也就有多重要。”(查洪德,《北方文化背景下的劉因》76)誠然,這位學者看到了劉因在理論層面提升藝之地位的貢獻,但據此得出他將古今之藝等同對待的結論卻值得商榷。劉因實在已經認識到詩文字畫與古之“六藝”相比有所下移的趨勢,并表示出些許無奈心理。
而且從游藝功能上來說,古之藝可以涵養性情而優入圣域,今之藝卻更多停留在藻飾層面,兩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詩文字畫固非學者所當棄,然但當自寓而已,不可陷溺其中以致移奪情志。在《輞川圖記》中,劉因首先贊美了王維之畫具有坐窮泉壑的暢神怡情之功,但轉而嘆曰:“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靜修先生文集》40)可見其對繪畫之事的警戒心理。然他所批評的并非畫藝本身,而是士人沉溺自嬉的態度。他說:嗚呼,古人于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
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為修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其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于陷賊而不死,茍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靜修先生文集》40)再次指明,作為今之藝的書畫之事,其重要性難以與作為修己治人之資的古之藝比肩而論,今之藝在古人是“不暇”與“不屑”為之的。其《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中也有類似表達:“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
[……]而況后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靜修先生文集》35—36)在劉因看來,王維之以畫師自居,以畫藝“自名”“自負”,與閻立本相比其人品又在下矣,但如果他能將古人游藝以“修己治人”的精神移之于繪畫之事,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于有后來之紊亂錯逆。此處的“文”正如“文之以禮樂”之“文”,“修己治人”之“修”,最終指向的還是“人之大節”的完善。由此可見,劉因不僅重視“六藝”之教,提出“藝是小學工夫”的理念,且將由古之“六藝”流變而來的詩文字畫琴棋等新“六藝”也納入士人致力的范圍之內,主張以今藝行古藝之事,成古人之功,從而延續古人“游藝”志道的精神傳統。
二、“游藝”實踐中的觀物思想與格物
致知精神在理學思想上,劉因兼綜各家,而于邵雍、朱熹尤為服膺。故蘇天爵稱其學術“本諸周、程,而于邵子觀物之書,有深契焉”(110);當代學者論及劉因時,則多認為其繼承了朱子的“即物窮理”之學(蒙培元154—160)。②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邵雍的“觀物”思想與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學不僅深刻影響了劉因的為學精神,也滲透進其詩文創作和書畫游藝的實踐中。在題畫時,劉因習慣以即物窮理的思維方式去觀察畫中景物,以物觀物,隨處體認天機。其《百蝶圖》詩云:“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靜修先生文集》202)從芳蝶紅翠之中見出天地生生不息之德,正是其看畫的動機與體驗。
靜觀物象本是理學家日常的修養功夫,劉因《野興》詩云:“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145)其《雜詩五首》之三云:“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偷安故隱淪。”(220)這種觀物思維被劉因移植于藝術世界,隨即以理性精思代替了藝術審美,從而獲得了更高層次的精神愉悅。作為世界本源的“陰陽”“乾坤”,又常被劉因稱為“天化”“氣機”“理”“天”等。在《宣化堂記》中,劉因集中闡釋了“天化”論思想:“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圣人。”
(《靜修先生文集》36)全文分別從自然與人文兩個系統進行演說,認為造化宣而為陰陽五行,繼而為物、為人,終而為人倫、禮樂。就本體論來說,“理”與“天”同在陰陽五行之先,可謂“同出而異名”。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劉因以‘理’為宇宙本體,也就是以‘天’為宇宙本體。”(陳谷嘉122)他在題畫時也常表露“天化”論主張,如《神農畫像贊》云:“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種與俱生。于赫炎皇,繼天而已。圣德神功,止于如此。”(《靜修先生文集》89)《堯民圖三首》其二云:“風氣初開理漸融,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誰及乾坤再日中。”(213)對于傳說中始教民耒耜的神農氏,劉因認為其圣德止于“繼天”而已。因為上天在生民之初,糧食與之俱生,并非神農之功。
《堯民圖》中也說,混沌鑿破而天理漸融,鳶飛魚躍,各適其性。這種“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37)的理想狀態,皆天化而成,圣人承天化而立人化者也,堯帝何功于民焉?“帝力”何敢與“天恩”爭功?“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146),是劉因看畫題詩時的主要心態。除繪畫外,書法、器物等皆被劉因視作靜觀格致的對象,正所謂:“鄙事雖云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四書集義精要》256)譬如,劉茂之送給他兩個漆硯,摩挲賞玩之后,他從中悟出了陰陽開闔之理:“硯漆未為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
茫茫兩儀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游戲,觀物供研摩。”(《靜修先生文集》140)方寸之間卻能演繹乾坤萬象,因此他欣喜地將其命名為“先天硯”,并從中觀摩天機。破除耳目之見和好惡之心,從而得窺萬物性理與世事規律,是邵雍“以物觀物”思想的核心精神。《伊川擊壤集序》中說:“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邵雍180)在《觀物內篇》中他也指出,唯有圣人才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7)。可見,邵雍所謂觀物,并非限于自然物質世界,亦涵括對世運更替與精神世界的分析。這對劉因的歷史觀念與觀世方式也有著深刻影響,他在題寫前朝文物及歷史題材圖畫時,往往以冷靜之眼與理性之思,推察世運和氣機。
三、歸隱于藝術世界以適意玩情
“古人于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靜修先生文集》40),是劉因的又一游藝觀念。劉因曾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接受元廷征召,但旋即辭官歸鄉,絕意仕進。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說:“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為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黃宗羲3023—3024)當代學者對此也多有探討,大概認為其經歷了一個由積極用世到尊道自尊的過程。④其閑適自得的高逸情志,除了在大量的隱逸詩中得以抒發外,又常被安放于圖畫琴棋的藝術世界。
在注目山水畫圖時,劉因往往被其林泉高致吸引,興發出一種“添我入圖”的強烈沖動。其《范寬雪山》云:“老寬胸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況復玉立千尺孤。安得晨光滿東壁,試看龍燭昆侖墟。赤塵鴻洞天為爐,一丘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冰壺。”(《靜修先生文集》130)北宋山水畫家范寬主張“師諸造化”,后在終南山終日對景危坐,終成大家。劉因正是在盛贊范寬筆下山川靈秀的基礎上,流露出歸隱愿望。再如以下幾首,《題山水扇二首》其一:“山近雨難暗,樓高秋易寒。憑誰暮云表,添我倚欄干。”(207)《華山圖》:“水墨驚看太華蒼,夢中千載果難忘。
三峰雖乞希夷了,應許劉郎典睡鄉。”(224)《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其二:“諸公久矣笑吾貪,是處云山欲結庵。只有皇卿解貲助,畫山須畫靜修龕(原注:謂皇甫安國)。”(225)這些詩皆是劉因觀水墨云山畫圖后興發而作。臨圖摩挲久之,不覺生出一份結庵其間的想象。這種幻想出的圖景排解了現實中的郁氛,也暢通了觀者的胸臆,頗有一種“感發志意”及“導情性而開血氣”(3)的意味。
在題花鳥畫時,劉因欣賞的也多是孤芳自賞之花草和昂藏忘機之禽鳥,以寄托自己高潔自得之情懷。如《瓊花圖》贊美幽獨清疏的瓊花:“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靜修先生文集》104)《薛稷雙鶴圖》描繪雙鶴與世不爭、超群出塵之姿態:“前鶴忘機如易馴,后鶴昂藏不可群。”(121)《僧惠崇柳岸游鵝圖》寫出群鵝悠閑自適的神情:“河堤煙草柳陰勻,舒雁群游意自馴。”(231)《雁圖》一詩則表達了自己與畫中之物渾然一體的心理境界:“夢回煙水寒,鴻雁驚不起。道人心久閑,相忘有如此。”(207)真正做到了玩物之情以得吾之情,盡物之性以適吾之性。
人物故事畫則會引發劉因的思古幽情,題畫時或激賞畫中人物的凜然高節,或仰慕其閑逸自得之趣,或體貼其隱逸之志,真可謂“以一心觀萬心”了。其《四皓圖》云:“雖戀紫芝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尚豈初心。”(《靜修先生文集》202)認為四皓采芝商山非其初心,從他們眉皓須白之際仍肯驅馳奔走即可見出。
在其《幼安濯足圖》中有詩句云:“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為丕太中。丹青白帽凜冰雪,高山目送冥飛鴻。”(121—122)寫出了管寧不慕富貴、傲視群雄的高蹈形象,與追逐名利的華歆形成鮮明對比。但四皓也好,管寧也罷,其凜然冰雪之姿背后,都有一段欲出不能轉而瀟灑遨游的心路。劉因將他們引為異代知音,以獲得自我情志的適意。殊不知,上古之民適意自得的至樂境界正是劉因所向往的,《堯民圖三首》其一云:“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邵家窩。”其三:“平生喜作許東鄰,百過摩挲畫本昏。”(《靜修先生文集》213)能夠令其真切體驗太和之樂的只有畫圖了。
圖像再現了往古世界,觀畫者便可從當下之維切換至另一重時空,使趨向之心有所安放。有時,劉因欲結伴而游的竟是一些神仙人物,如《呂洞賓畫像》:“微茫洞庭曉,瀟灑昆侖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游。”(《靜修先生文集》206)《浙江潮圖》:“海中仙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
試問濤頭何當還,為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游其間。”(139)對此,有學者認為:“劉因恬退后,存在傾慕釋道的情緒。”(王素美261)其實,劉因這種頗具游仙色彩的作品并不多,或者可視作其偶爾的“出位之思”吧。他對老莊及道教的真實態度主要是批判,如在《仙人圖三首》其一中的懷疑譏刺:“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應悔虛名落世間。”其三中的批評憾恨:“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跡得崆峒。
可憐千古稱黃老,誰識當年立極功。”(《靜修先生文集》211)在《莊周夢蝶圖序》中對莊子“齊物”思想的辯解:“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后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莾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于名教,失志于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籍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28)可見,劉因所謂“齊與可”的從容自適,是以循序窮理以至“此心透徹”的道德境界為主宰的。
四、作為美學境界的“天”形神兼備的繪畫觀念和崇尚復古的書學取向
是劉因藝術美學的集中體現,但他在游藝活動中所經常標舉的“天機”“天全”“天真”“天理”“天成”等,皆指向同一妙境———“天”。元時畫壇盛行著重神似輕形似的風尚。如湯垕《畫鑒》引述趙孟頫之語說:“不求形似,所以出眾工之右耳。”(湯垕422)湯垕自己也主張:“蓋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437)自稱“平生畫卷看多少”(《靜修先生文集》231)的劉因卻提出了頗具理學色彩的獨到見解。
他在《田景延寫真詩序》中說: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并與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極,而后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靜修先生文集》34)所謂“意思”是蘇軾在《傳神記》中提出的,他從顧愷之的“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蘇軾401)談起,又舉自己燈下摹寫顴頰影子的例子,得出“凡人意思各有所在”(蘇軾401)的結論。又指出,傳神與相人一樣,必須暗中觀察人物自然情態,才能得“其人之天”(蘇軾401)。“風神氣韻之天”則出自朱熹的《送郭拱辰序》:“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
余論:
理學“流而為文”現象的書畫視域《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中載清人黃百家之語曰:“金華之學,自白云一輩而下,多流而為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斯。”(黃宗羲2801)其實“流而為文”的現象并非金華學派所獨有,而是“元代學術帶有共性的問題”(查洪德,《元代理學》36)。
這一現象雖引起諸多學者的注意,但考察范圍基本限定在詩文領域,對元代理學家亦有所致力的書畫藝術卻缺少應有的重視。殊不知,元代確實出現了眾多具有深厚藝術素養的理學文藝家,如劉因、吳澄、虞集、黃溍、柳貫等。他們在文集中保留了較多題畫論書的作品,儼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藝集團。
而且,理學家語境中“文”之范圍往往比較寬泛,并非僅限于文章之學,書畫技藝之事亦在其中。因此,書畫藝術理應被納入理學“流而為文”現象的考察視域。進一步說,理學家之學術精神也經常貫徹于游藝實踐中,“道之不亡”者,亦應有其游藝之學的一份功績。
比較而言,南宋理學家即使廣泛參與詩文書畫等文藝活動,也絕少直接針對藝術工巧作出評論,而往往將視角著落在作者的人格修養方面。⑤但元代理學家則沖破了理學對文藝所固有的警惕心理,更為深入地理解和接納文藝,并以藝術家的手眼進行創作和開展批評。
文藝論文范例: 論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教育人學內涵
隨著元代理學“流而為文”現象的蔓延,理學精神對文藝思想的浸潤也更為深刻了。一者,元代理學家更為重視詩文書畫作為“小學工夫”接續古人“六藝”之教的功能意義,給予了“游藝”之學回歸道學事業的空間,并賦予其作為專門之學“亦當致力”的地位。二者,元代理學家更為深度地向文藝領域輸入思維方式與價值理念,從宏觀的本體論、主體論,到具體的創作論、批評論和審美論,理學思想對藝術精神的規范和導引可謂無孔不入,深刻影響著文藝思潮的發展走向。
作者:楊萬里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