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統到天道對《史記·伯夷列傳》的政治哲學詮釋
時間:2021年04月09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史記·伯夷列傳》不僅極具史學和文學價值,而且也為我們展現了許多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包括法統之連續、共同體邊界之劃分、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暴力的正當與不正當使用、命運與天道之關系等。正是在伯夷、叔齊看似不公的命運中,我們可以看到天道隱秘的公正。總之,《史記·伯夷列傳》蘊含了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我們從政治哲學角度對其進行詮釋,既可以加深我們對文本的理解,也可以增強我們對歷史與自身命運的理解。
關鍵詞:《史記·伯夷列傳》;法統;天道;政治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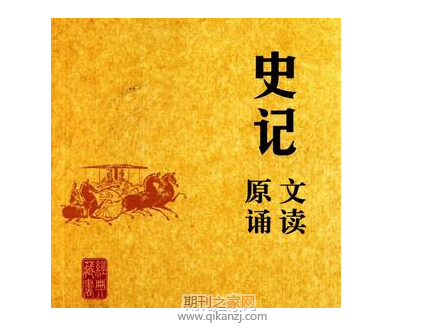
學界以往對于《史記·伯夷列傳》的研究或探討太史公的匠心和文筆,或考證伯夷、叔齊事跡發生的時代背景及相關典章制度等,這些成果自有其價值,但多偏于文史領域。近年來,也有學者注意到了《史記》及其《伯夷列傳》的政治哲學維度,如李長春提出,《史記》是政治哲學,“并不等于說它講了一大堆哲學概念和推理,而是說它展示了各種各樣高低不同,心志各異的人;展示了具有各種各樣政治品性的政治體;展示了心志各異的人都有什么樣的結局;展示了這些品性不同的政治體最后都有什么樣的政治命運”①。
哲學論文范例:行動、實驗與協作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哲學的意蘊
筆者也認為政治哲學不僅可以以哲學的方式書寫,而且也可以以史學、文學等方式書寫,《史記》雖無政治哲學之名,卻有政治哲學之實。本文以《史記·伯夷列傳》為例,縱觀其文本,諸多政治哲學的概念和問題在太史公筆下的敘事和議論中呈現出來。
一、法統問題:立、讓、逃《史記·伯夷列傳》在文體上別具一格,以論說為主,以敘事為輔,用極為簡潔的筆墨敘述了伯夷和叔齊的身世、事跡和言論。敘事部分的開篇寫道:“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②“立”“讓”“逃”三字簡潔地展現了孤竹國統治集團父子三人對于“法統”問題的態度和行動。“法”即憲法,“統”即連續性,故“法統”即連續不斷地依據憲法而統治。法統既有連續性,又有規則性。孤竹國當時的國君是伯夷、叔齊之父,他按照當時的憲法原則(即權力世襲原則),確立叔齊為自己的繼承人,讓政權傳諸久遠。叔齊是三弟,他不愿繼承王位,遂讓位給大哥伯夷,以盡悌道;伯夷則不愿違背父命,遂逃走,以盡孝道。最后,國人擁立孤竹君的第二子繼位。
可見,伯夷、叔齊兄弟也注重法統的連續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法統的規則性,而是根據倫理規范,相互謙讓。在《伯夷列傳》中,司馬遷還專門引用古圣先賢的類似事例,表彰叔齊、伯夷兄弟“讓”“逃”行為之高尚:“堯將遜位,讓于虞舜……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①在法統問題上,司馬遷對伯夷、叔齊與許由的看法是一致的:只要憲制不變,則無論由誰繼承政權———只要符合憲法規則———法統就不算斷絕,這也表明,法統的規則性是有彈性的,在與倫理規范兼容的范圍內可以有所變動。因此,功成不必在“我”,縱使被“立”為王,或“讓”或“逃”,各得其宜。
二、共同體的邊界問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孤竹國是殷商的一個諸侯國,其法統來源是殷商天子的分封,其基礎是契約關系。根據殷商與孤竹國的封建契約,孤竹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與殷商“結盟”,其國君和貴族享有向孤竹國平民征收貢賦的權利,也承擔著保護國內平民的義務,同時,孤竹國國君和貴族也承擔著效忠殷商天子的義務;而孤竹國的平民則對孤竹國和殷商的統治者都負有義務,既應效忠于孤竹國國君,亦應效忠于殷商天子。
正是這種鉤鎖連環的封建契約關系,使孤竹國與殷商成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利害攸關,榮辱與共。在熱愛“祖國”的伯夷、叔齊看來,取代殷商的周,與孤竹國并無契約關系,孤竹國與周并無有機的聯系,亦即二者不屬于同一個共同體。即使商紂王殘暴荒淫,孤竹國各等級(君主、貴族和平民)仍對商紂王負有義務;即使周武王仁義愛民,孤竹國各等級對周武王也不必承擔任何義務。因此,“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②。
伯夷、叔齊沒有隨波逐流。在天下歸附周朝的歷史潮流中,他們以歸附周朝為恥,因為他們能夠明確地認知和堅守共同體的邊界。共同體是憑借對內的團結和對外的排斥來劃定邊界的,越是對內團結就越排外,越是排外就越能鞏固共同體內部的團結。即使殷商亡國了,伯夷、叔齊也沒有忘記孤竹國與殷商曾經是同一個共同體,他們也清楚地知道,無論周朝統治者怎樣厚待前朝遺老,他們與周朝也并不是同一個共同體。人們會很快遺忘那些善于順勢歸附的“聰明人”,卻會長久地記住逆潮流而動、因“不食周粟”而餓死于首陽山的伯夷和叔齊,這不是因為二人比“聰明人”更聰明,而是因為二人比多數人更忠實地遵守封建契約,更忠誠地維護共同體的邊界———甚至不惜以自身的生命為代價。
三、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的沖突:“義不食周粟”
在殷周易代之際,孤竹國君臣面臨著三個選擇:一是歸順周朝,二是反抗,三是歸隱。如果歸順周朝,則孤竹國可以興亡國,繼絕世,這也是當時多數孤竹國貴族做出的選擇;如果反抗,由于孤竹國軍政實力遠遜于周朝,無異于以卵擊石,必定會連累無辜;如果歸隱,則是明確與周朝一切利益做切割,以非暴力而又不合作的方式進行一種消極的反抗,或者說是“逃避”。伯夷、叔齊選擇了第三種方式,基于對殷商的認同和對周朝的排斥(這是一體兩面之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③。
“不食周栗”既可以從字面意義上理解為不吃周朝的糧食,也可以從隱喻的意義上理解為不要周朝的俸祿,從不與當局合作的角度看,其行為可稱之為“清”。“清”即清白高潔,不肯同流合污。“清”與“濁”是一對相反的概念:“舉世混濁,清士乃見。”④從忠于殷商的角度看,其行為可稱之為“義”。“義”即“威儀”,《說文解字》將“義”解為“己之威儀也。”,亦即一個人自身的威嚴法度①。
“義”與“利”是一對相反的概念:“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②因此,伯夷與叔齊的事跡廣為流傳,且為孔子、孟子、韓愈等歷代圣賢表彰。但是,這里有一個矛盾:伯夷、叔齊因忠于商朝而被稱為“義人”,周武王軍隊因推翻商朝而被稱為“仁義之師”,武王伐紂順應民心,伯夷叔齊卻不食周粟,這是為什么?從政治哲學角度看,這一矛盾展示了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的沖突。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指出,個人正義就是一個人靈魂的正義,即靈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比例和諧,激情輔助理性,欲望受到理性的制約;城邦正義就是城邦各等級各安其位,做所應做,得所應得,統治者有智慧,護衛者勇敢,平民以及統治者和護衛者節制,而智慧、勇敢和節制這三種德性的綜合統一就是“正義”。在柏拉圖看來,個人正義(即“靈魂正義”)與城邦正義是一致的,“我們以什么為根據承認國家是正義的,我們也將以同樣的根據承認個人是正義的”③,因為城邦是大寫的人,個人的靈魂與城邦共同分有同一個正義的理念,正義的理念即正義本身。
柏拉圖認為,個人的靈魂與城邦之所以都能分有正義的理念是因為二者結構一致,靈魂各部分與城邦各等級的德性一一對應,即靈魂中的理性與統治者的智慧相應,激情與護衛者的勇氣相應,欲望與平民、護衛者和統治者的節制相應。但是,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所指出的,“靈魂與城邦對應論是《理想國》所闡述靈魂學說的前提,而這個前提顯然是可疑的,甚至是站不住腳的”④。靈魂與城邦對應論的基礎是或然性的類比,屬于歸納推理,不具備演繹推理的必然性。
在《伯夷列傳》中我們就看到,伯夷、叔齊對殷商的忠誠與武王對殷商的征伐,恰恰體現了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的不一致。武王伐紂的理由是商紂王有殺害比干、囚禁箕子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⑤這一理由也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而伯夷、叔齊則對周武王當面批評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⑥可見,伯夷、叔齊從個人正義角度出發,認為周武王應該對其父(周文王)盡孝,對其君(商紂王)盡忠———當然,他們把封建關系理解為君臣關系是有偏差的,但這一要求與伯夷、叔齊本人的忠義觀念和行為是一致的。
而周武王則從城邦正義角度出發,認為商紂王暴虐無道,迫害忠臣義士,已經成為人民和國家之公敵,不配再做國家的主人了,正如齊宣王問孟子,武王伐紂這種以臣弒君的行為,是否具有合法性?孟子回答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⑦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君主本身喪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那么他就不再能夠代表國家了。總之,伯夷、叔齊面臨的問題就是:當一個城邦因統治者的不義而導致城邦本身不正義時,我們是否還要忠于不義之邦?甚至為之獻身?他倆給出了肯定的答案,而周武王則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這表明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并非永遠一致。
四、暴力的正當使用與不正當使用:“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隱居于首陽山的伯夷和叔齊,臨死前創作了一首詩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①歌辭大意是:我們登上西山啊,采摘野菜。(周武王)以暴力取代暴政啊,竟不自知其錯。炎帝、虞舜、夏禹的禪讓時代轉瞬即逝啊,逢此亂世的我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也將逝去啊,可嘆天命之衰微!②伯夷、叔齊在這里又提出了一個深刻的政治哲學問題:“以暴易暴”在政治上是否具有正當性(right⁃ness)?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區分暴力的正當使用與不正當使用。這里,我們依然可以參照柏拉圖的相關論述。
在《理想國》開頭部分,蘇格拉底與玻勒馬霍斯討論什么是正義的行為時,玻勒馬霍斯說,正義就是“把善給予友人,把惡給予敵人”③,而最能利友害敵的行為就是在戰爭中聯合朋友而去攻擊敵人的時候發生的,政治活動首先應當區分敵友,對敵人使用暴力是正當的,因為“我”和敵人不屬于同一個共同體;對朋友使用暴力則是不正當的,因為“我”和朋友屬于同一個共同體。現代世界最重要的共同體是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在現代民族國家中,唯一有權利判定暴力使用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共同體就是國家本身。馬克斯·韋伯在那篇題為《以政治為業》的著名演講中指出,國家就是在一定疆域內肯定了自身對暴力進行正當使用的人類共同體,“就現代來說,特別的乃是:只有在國家所允許的范圍內,其他一切團體或個人,才有使用暴力的權利。因此,國家乃是使用‘暴力’的唯一來源”④。
五、命運與天道:“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在敘述了伯夷、叔齊的事跡之后,司馬遷有感于二人德性之高和命運之薄,對“天道”的公正性提出了困惑與質疑: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穅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①這段議論首先引用老子的一句名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第79章),這句話也反映了人們對天道與命運的一般看法,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然而,正如《伯夷列傳》所說,伯夷、叔齊的行為不可謂不善,其德性不可謂不高潔,但其最終的命運竟然是餓死在首陽山上。接著,司馬遷又舉出兩個強有力的反例:顏淵仁義好學而早夭,盜跖殺人如麻卻得以頤養天年,而這樣的例子在古往今來的歷史中是數不勝數的,那么,我們所信奉的天道,究竟是對是錯?對于“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②
這一偉大的疑問,司馬貞在《史記索引》中解釋道:“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必福,行惡未必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③大意是說天道高深玄遠,以至于人類有限的理性無法理解。許多當代學者則從康德式的“德福一致”問題角度出發,對伯夷、叔齊的遭遇進行了解釋,揭示了德性與幸福在現實世界中往往不相匹配,這固然很有道理。但是,我們還可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一思考關乎“天道”與“命運”的差異性關聯。
結語在本文中,筆者基于《史記·伯夷列傳》文本,依次闡述了五個觀點:其一,伯夷、叔齊寧可逃離孤竹國,也不愿繼承君位,這體現了他們對法統的態度;其二,伯夷、叔齊忠于已亡的商朝,卻不認同新興的周朝,這體現了他們對共同體邊界的堅守;其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行為跟武王伐紂的行為相對比,體現了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的沖突;其四,伯夷、叔齊批評周武王“以暴易暴”,體現了他們對于暴力使用之合法性問題的看法;其五,太史公通過論述伯夷、叔齊的事跡及其意義,對天道之公正性提出了質疑,則體現了德性、命運與天道的復雜關聯,而這一關聯也是貫穿于《伯夷列傳》全文的一條主線。
這五個觀點是層層遞進的關系:有法統而后有共同體;唯有持守共同體邊界,才可以評價個人和城邦是否正義;持有各自正義觀念的人對同一行為———包括暴力行為———是否具有合法性,會做出各自的判斷;比合法性更深層次的根據是天道的公正性,天道對所有個人和共同體的命運做出終極裁決。可見,《伯夷列傳》蘊含了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我們從政治哲學角度對其進行詮釋,既可以加深我們對文本所蘊含的思想和精神的理解,也可以增強我們對歷史與自身命運的理解。
作者:陳鑫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