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魔幻世界
時間:2020年06月12日 分類: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摘要:《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過夢、碎片化的敘事、強烈而新鮮的人物形象、時間空間化等方式在小說中建構(gòu)出一個神秘莫測的魔幻世界,打通了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以及現(xiàn)實與魔幻的界限,為文學(xué)增添了新的維度和多種可能性。有人認(rèn)為托卡爾丘克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事實上,她的創(chuàng)作手法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值得深入研究。
關(guān)鍵詞:《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托卡爾丘克;魔幻世界;現(xiàn)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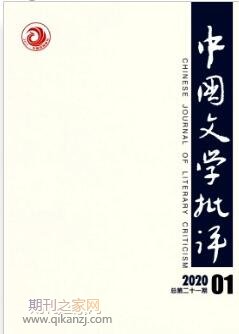
2019年10月10日,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Tokarczuk,1962-)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而成為熱點人物。《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年)是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2002年,托卡爾丘克憑借這部小說獲得波蘭最高文學(xué)獎“尼刻獎”的讀者選擇獎。托卡爾丘克善于將看似相互矛盾的東西聯(lián)在一起:質(zhì)樸和睿智,童話的天真和寓言的犀利,民間傳說、神話和現(xiàn)實生活等等都在她的筆下相互交錯和聯(lián)結(jié),組成一個現(xiàn)實與魔幻甚至不無怪誕的神秘世界。
文學(xué)論文投稿刊物:《中國文學(xué)批評》雜志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dǎo),以建立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xué)理論話語體系為目標(biāo),以研究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理論與批評為中心,緊密結(jié)合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鑒賞的實際。
“她的筆下涌動著不同尋常的事物,但她又將神奇性寓于日常生活之中。”[1]1《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就是這樣一部不同尋常的小說,作者從來不讓你一口氣讀完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在緊要關(guān)頭戛然而止,直接進(jìn)入另一個陌生的故事,在另一個故事未結(jié)束的時候再插入其他故事,幾個故事循環(huán)往復(fù),總有新故事突然出現(xiàn)。作者就這樣帶領(lǐng)讀者不斷地認(rèn)識新主人,進(jìn)入新情結(jié)。這種手法吊足了讀者的胃口,使讀者不斷期待著新的驚喜,從而打破了固有的閱讀習(xí)慣和思維模式,讓讀者獲得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托卡爾丘克通過夢、碎片化的敘事、強烈而新鮮的人物形象、時間空間化等方式在小說中建構(gòu)出一個神秘莫測的魔幻世界,而她的魔幻世界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值得深入研究。
一、魔幻世界的建構(gòu)
托卡爾丘克以她的神來之筆和奇幻思維在小說中構(gòu)筑的是一個神秘莫測的魔幻世界,這個魔幻世界主要通過以下幾方面得以實現(xiàn):
(一)夢《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最初被直接譯作《收集夢的剪貼簿》,21世紀(jì)初在臺灣出版,2017年,這本書由后浪出版公司從臺灣引進(jìn),并恢復(fù)了它原本的名字《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從書名的變動可見,“夢”在這部作品中占據(jù)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整部小說真正的主人翁就是夢。小說以夢開篇,“第一夜我做了個靜止的夢。我夢見,我是純粹的看,純粹的視覺,既沒有軀體也沒有名字。”[1]1“我”所看到的一切忽遠(yuǎn)忽近、虛無縹緲,它們不屬于我,“因為我也不屬于我自己,甚至沒有我這么個人。”[1]
1作者像一個魔法師一樣,將“看”和“視覺”從“軀體”和“名字”這些外在的、物質(zhì)的事物中剝離出來,使“看”和“視覺”成為其本身。不僅如此,“我”還能穿透表象,看到樹皮下面活動的水和樹液的涓涓細(xì)流;看到做夢的人們心臟的搏動、血液的奔流,甚至他們的夢的圖像。這樣就深入到事物的本質(zhì),到達(dá)一種純粹和本源。這樣的開頭充滿了魔幻色彩,也深孕著作家對人生的哲理思考。“我”和我所看到的一切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虛實之間彰顯著作家“人生如夢,夢如人生”的深刻哲思,奠定了小說的基調(diào)。“我在做夢,我覺得時間走得沒有盡頭。
沒有‘以前’,也沒有‘以后’,我也不期待任何新鮮事物,因為我既不能得到它,也不能失去它。夜永遠(yuǎn)不會結(jié)束。什么事情也沒有發(fā)生。甚至?xí)r間也不會改變我看到的東西。”[1]2這些夢囈般的語言告訴人們:在時間的流動里,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只有時間本身才是永恒。作者用充滿夢幻的開頭,引領(lǐng)讀者進(jìn)入了她的魔幻世界。之后,小說中每隔幾頁就有關(guān)于夢的描述:“我”從網(wǎng)絡(luò)上收集夢,并發(fā)現(xiàn)可以通過人們對夢境的描述,來命名夜晚或白天、命名月份、年份或時代,進(jìn)而找到世界的某種運行模式,在此模式下,整個人類世界成了一場空夢。
銀行職員克雷霞千方百計尋找反復(fù)夢見的愛人阿摩斯,最后利用出差之便找到一個名叫安杰伊·摩斯的男人并且和他有了一夜情。但是她仍然在耳朵里不斷聽到阿摩斯的聲音,即使找了占卜師也無法擺脫夢里這個男人,最后她終于習(xí)慣了和夢一起生活,盡管夢醒之后只剩模糊的印象。在這個故事里,愛情成了一場空靈的美夢。鄰居瑪爾塔看到了成千上萬人的夢,“這些人全都睡著了,陷入了一種實驗性的死亡,他們一個挨著一個地躺在城市、鄉(xiāng)村,順著公路,挨著邊界通道,躺在山中的旅游招待所、醫(yī)院、孤兒院,躺在克沃茲科、新魯達(dá),還有看不到甚至感覺不到其存在的一些地方。”[1]
119這是一個昏昏欲睡的世界,“在時間的每一瞬間都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在睡覺。當(dāng)人類的一半醒著的時候,另一半糾結(jié)在酣夢之中。當(dāng)一些人醒來的時候,另一些人必須躺下睡覺,這樣世界才得以保持平衡。”[1]119醒著的另一半是睡眠,如同光明的另一面是黑暗一樣,世界必須在這樣的平衡之中才能正常運行。“當(dāng)夢一再重復(fù)過去發(fā)生的事件,當(dāng)夢反復(fù)咀嚼過去,把過去變成畫面,像過篩子一樣篩掉其中的含意,我便開始覺得,過去跟未來一樣永遠(yuǎn)深不可測,永遠(yuǎn)是個未知數(shù)。”[1]
121在網(wǎng)絡(luò)上收集夢,使“我”和那些帶著自己的夢加入網(wǎng)絡(luò)中的人們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網(wǎng)絡(luò)中的夢時不時穿插在故事中間,像一些雜亂無章的小世界,加在一起組成一個難以理解的大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過去和未來都成為深不可測的未知領(lǐng)域,這就把人類社會拋入一種神秘奇幻之境。在夢中,“我”是一個無肉身的幽靈,通過人的嘴巴進(jìn)入人的身體內(nèi)部,觀察人體內(nèi)部的構(gòu)造,感受生命的溫度;“我”可以發(fā)現(xiàn)自己的后背上也有肚臍眼……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通過這些時隱時現(xiàn)的夢,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夢幻的世界,這世界里的一切既真切可感,又虛無縹緲。
那些實實在在的地方、實實在在的人和事,忽遠(yuǎn)忽近,忽明忽暗,最后在意識中化為烏有。作者仿佛運用了某種催眠術(shù),讀者會不知不覺被她帶入一種意識和無意識相互交織的境界。她的文字不是用眼睛來看的,而是要用心來感受和覺知的。這和她接受過系統(tǒng)的心理學(xué)教育,并且做過專業(yè)的心理咨詢師不無關(guān)系。托克爾丘克自稱是榮格的信徒,她的作品經(jīng)常探討個體夢境、潛意識和無意識,“深邃的哲學(xué)思考賦予其作品極強的思辨性,使閱讀成為一場心理探索之旅……”[2]
(二)碎片化的敘事方式
托卡爾丘克用碎片化的小故事組成這樣一部完整的小說,這種風(fēng)格與現(xiàn)代讀者碎片化的思考方式相互契合。她把自己生活的蘇臺德山脈地區(qū)設(shè)為小說的故事發(fā)生地,蘇臺德山脈地區(qū)是波蘭、捷克、德國三國的邊境,這個地方深藏著許多古老而奇幻的神話傳說、奇聞軼事和過往歷史。托卡爾丘克將她聽聞的短小故事穿插講述,每個故事都充滿了戲劇性,扣人心弦,令人觀之難忘。馬雷克·馬雷克吊死的故事;圣女庫梅爾尼斯的神話傳說;圣女傳的修士帕斯哈里斯的傳奇人生;尋根的彼得·迪泰爾猝死在邊界,被捷克和波蘭的邊防軍沒完沒了地從一邊搬到另一邊的故事,等等。
這些故事和故事相互交錯,卻沒有混亂之感,反而可以不斷地調(diào)動讀者的好奇心,期待下一個精彩情節(jié)的出現(xiàn)和神秘人物的登場。交叉講故事給人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夢里見到的人物清晰而模糊,情節(jié)時而連貫、時而間斷,讀者就在這“太虛幻境”中追隨著作者的腳步,直到夢醒,故事中的人物有的有結(jié)局,有的不了了之。但無論如何,都充分滿足了讀者的期待,體驗到了閱讀的別樣快感。總體而言,這部小說更像是一個文本混合體,里面不僅包括許多不同情節(jié)、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故事,還有與之毫無關(guān)系的夢境、私人日記、菜譜、散文式的筆記等等。這些故事看似缺乏統(tǒng)一性和整體性,卻收到了奇異的效果。“讀者宛如置身于一個殿堂,目眩神迷,亦真亦幻,微塵般的個體渺小與宏大時空既對立又統(tǒng)一和諧。”[3]小說中現(xiàn)實的實感和夢境的虛幻相互交融,貫穿全書,給整部作品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而在其背后隱藏著的,則是作家對人生、世界、生命和宇宙等領(lǐng)域的思考與探索。
(三)強烈而新鮮的人物形象
小說貫穿始終的人物形象只有“我”和瑪爾塔,其他形象都分散在各個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小故事當(dāng)中,使命完成后便自行消失。許多人物形象令人匪夷所思,給人的印象是強烈而新鮮的。其中較為典型的人物形象包括如下幾位:瑪爾塔是一個做假發(fā)的老婆婆。她行跡怪異,冬天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早春時節(jié)便自行出現(xiàn)。她就像一個高深莫測的哲學(xué)家和神秘的預(yù)言家,說過許多令人震驚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話,她說:“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將永生”[1]244;“人就像他生長的土地,無論他愿意還是不愿意,無論他知道這一點還是不知道”[1]262。盡管“我們”是朋友,但關(guān)于瑪爾塔,“我”卻知之甚少,因為她很少講自己,并且每次告訴“我”她生日的時間都不一樣。
然而,她卻很喜歡講別人的故事,不知道她從哪里知道那么多。庫梅爾尼斯是一位圣女,她具有非凡的美德和苦難的死亡。從小被送到修道院,長到婷婷少女時,父親決定將她嫁人,但是她已決定獻(xiàn)身于主。父親強烈反對,固執(zhí)地將她帶回家待嫁。她逃進(jìn)山中的洞穴里隱居,受到魔鬼的各種誘惑而不為所動。
三年后她返回修道院發(fā)愿修行,卻被瘋狂的父親禁閉。庫梅爾尼斯在沒有窗戶的房間里日日祈禱,臉上長出了絲絨般的胡須,她說:“我的主讓我從自身解脫了出來,他把他自己的面孔給了我。”[1]86她的父親由于無法控制她而發(fā)狂,暴怒之下將她釘在天花板的方木上,圣女庫梅爾尼斯受盡折磨最終殉難,而她的事跡卻被人們到處傳頌。這個史詩般的故事具有《圣經(jīng)》般的魅力,令人讀后獲得一種崇高的審美體驗。17歲的帕斯哈利斯(原名約翰,成為修士后改為帕斯哈利斯)容貌俊秀,最大的愿望就是擁有女兒身。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女修道院一個塵封已久的小禮拜堂里見到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圣女庫梅爾尼斯,他被少女的軀體上赫然一副耶穌的面孔的圣像嚇得發(fā)抖。從此以后,他開始寫圣女傳。帕斯哈利斯見到圣女的第一感覺是似曾相識:一個是神話中的圣女,一個是現(xiàn)實中的修士,這兩者似乎有著某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
也許,修士正是圣女在現(xiàn)實中的顯現(xiàn),他的出現(xiàn)就是為了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使其流傳久遠(yuǎn)。帕斯哈利斯的結(jié)局也充滿了疑問,有多種說法,一種是說他自殺了,另一種說法則含混不清:“他似乎在歐洲漫游,也可能到世界各地周游列國,宣講自己的圣女事跡,摻和著介紹刀具匠人的憂傷。他在空間里活動,多半像在時間里活動一樣——每個新的地方都在他心中敞開了不同的潛在的可能性。”[1]316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以無限遐想的空間。吃過人肉的中學(xué)教師埃戈·蘇姆,因為看到柏拉圖《理想國》里的句子“誰若是嘗過人的內(nèi)臟,誰就一定會變成狼”[1]255而懷疑自己時刻都可能變成狼,他被這可怕的想法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后他給農(nóng)民當(dāng)了免費的長工,在繁重的勞動和頻繁獻(xiàn)血中得到解脫。一對恩愛夫妻一直平靜而甜蜜地生活著,直到阿格尼出現(xiàn)。阿格尼忽而是個十八歲的小伙子,成為女方的情人;忽而是個神秘女郎,成為男方的情人。
本來非常恩愛的夫妻各自有了心事,雖然生活在一起,卻越來越沉默。他們都強烈地思念著自己的情人,而他們的情人都叫阿格尼。阿格尼洞悉他們的一切,總能在合適的時間出現(xiàn)在他們面前。他們和阿格尼的情愛如夢似幻,令他們神魂顛倒又痛苦萬分。他們越來越疏遠(yuǎn)彼此,滿腦子都是對阿格尼的相思,而阿格尼再也沒有出現(xiàn)。這對夫妻再也無法回到過去,雖然沒有分開,但卻沒有了愛情,就這樣疏離地相伴到老。這是一個寓意十分深刻的愛情故事。盡管阿格尼只是個幻影般的人物,但是他/她帶給夫妻雙方的影響卻是巨大的。他們都被他/她的愛情所迷惑,忘記了彼此曾經(jīng)的感情和眼下的真切生活,去追尋一種虛無縹緲的愛,直到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盡管陪伴到老的只有彼此,而這種陪伴卻變得冰冷和麻木。
故事娓娓道來,卻有著震顫人心的力量。即使把這些人物形象放在整個世界文學(xué)里,也很容易辨認(rèn)出來:需要冬眠的瑪爾塔、通過文字合二為一的圣女和修士、吃了人肉而被“變成狼”的幻覺折磨著的中學(xué)教師、以靈異的方式迷惑一對夫妻的雙性人阿格尼等等,他們以自己強烈而新鮮的特征在文學(xué)殿堂里熠熠生輝,使得世界文學(xué)人物畫廊更加豐富多彩。
(四)時間“空間化”
托卡爾丘克常常將時間“空間化”。她的故事時而過去、時而現(xiàn)在、時而未來,讓三者在同一空間交匯,組成一個立體魔方。讀者置身于久遠(yuǎn)的過去、可感的現(xiàn)在和遙遠(yuǎn)的未來共同組成的立體魔方當(dāng)中感受時間的蒼茫和滄桑、人世的變幻與無常,產(chǎn)生強烈的震撼之感。“每一個閱讀托卡爾丘克的讀者都不會忽視這種跨越時空的自由:在這里你可以找到過去和未來,找到親人和陌生人,找到無形的神和哀訴的鬼,找到自然的心和人造物的靈,找到故鄉(xiāng)與流亡,找到瞬息和永恒,但是無論你找到了什么,一旦你試圖抓住它,它就會從你手中溜走。”[4]
這樣的例子小說中比比皆是:關(guān)于圣女的傳說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神話故事,圣女傳的作者卻是現(xiàn)代的修士,他在圣女傳的過程中與圣女合而為一,最后不知所終,仿佛回到了過去;瑪爾塔的身份是個謎,她就像一個從遠(yuǎn)古一直生活到現(xiàn)在的人,她仿佛知道一切,給“我”講述別人的故事,她像個善良的女巫,又像個預(yù)言家,因為她也常常預(yù)測未來;刀具匠們的故事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百年孤獨》中的某些情節(jié),他們的祖先都從某處遷移到另一處,他們都有奇異的風(fēng)俗,所不同的是,刀具匠不僅具有過去性,更具有未來性,因為他們有一個拯救機,這是一種關(guān)于宇宙學(xué)的圖像,里面隱藏著宇宙運動和世界末日的秘密……這些跨越千百年的故事錯落有致地交替出現(xiàn),組成了一個立體的時光空間,過去、現(xiàn)在、未來都匯聚在這里,具有了共時性和空間性,共同講述著人類的故事。于是,人類的歷史也被立體化了。
正如艾略特在《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中所說的:“(者)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xiàn)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時有他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xué)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xué)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這個歷史的意識是對于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tǒng)性的。同時也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dāng)代的關(guān)系。”[5]在托卡爾丘克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她對于過去之“現(xiàn)存性”的深刻理解力,并且將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個時空一起聚攏到自己的小說中,擴充了傳統(tǒng)小說的容量,產(chǎn)生了奇幻的效果。
二、托卡爾丘克小說的“后魔幻”色彩“
托卡爾丘克認(rèn)為,現(xiàn)實主義寫法不足以描述這個世界,這樣總會錯過一些東西。因為人在世界上的體驗,包括情感、直覺、困惑、奇異的巧合、怪誕的情境以及幻想,如此豐富多彩,我們感受到的只是現(xiàn)實的某個側(cè)面、某個維度。”[3]為了跟上變幻莫測的世界的腳步,呈現(xiàn)人們豐富多樣的體驗,托克爾丘克采用了魔幻手法來構(gòu)筑她的小說。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托卡爾丘克的作品與魔幻現(xiàn)實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它們之間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她的小說更具有“后魔幻”的色彩。
魔幻現(xiàn)實主義是諾貝爾文學(xué)獎中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fēng)景線,自20世紀(jì)初期拉丁美洲兩位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米·安·阿斯圖里亞斯(MiguelAngelAsturias,1899—1974)和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JosédelaConcordiaGarcíaMárquez,1927-2014)伊始,魔幻現(xiàn)實主義以其神秘性和新奇性吸引著人們的眼球。魔幻現(xiàn)實主義本身是一個很難解釋清楚的概念,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法國的超現(xiàn)實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試圖掙脫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切利害關(guān)系,通過表現(xiàn)夢境和心理狀態(tài)解決人生問題。超現(xiàn)實主義追求的目標(biāo)為:“改造世界,改變生活,重建人類理解力。”[6]超現(xiàn)實主義者采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和自由聯(lián)想法,運用“自動繪畫”或“自動”的技巧,把夢境和心理狀態(tài)直接移植到文學(xué)當(dāng)中。至于超現(xiàn)實主義是如何發(fā)展衍變成為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已經(jīng)超出了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
可以知道的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和超現(xiàn)實主義猶如一顆樹上的兩根藤,很難區(qū)分什么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什么是超現(xiàn)實主義。我們只要通過超現(xiàn)實主義了解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某些基本特點即可。“魔幻現(xiàn)實主義”這一術(shù)語本來是用于造型藝術(shù)領(lǐng)域的,但是后來卻被文學(xué)藝術(shù)所使用。1925年,德國評論家弗蘭茨·羅在他的論文《后表現(xiàn)主義(魔幻主義)》中最早使用“魔幻現(xiàn)實主義”一詞來說明德國一群畫家的特征。他描繪馬克斯·貝克曼、奧托·迪克斯、喬治·格羅茲等后表現(xiàn)主義畫家,認(rèn)為他們那些變形的、好像來自外星世界的畫作是現(xiàn)實與魔幻的藝術(shù),是為“魔幻現(xiàn)實主義”。
到1958年,人們不再稱當(dāng)年那群畫家為“魔幻現(xiàn)實主義”畫家,而是代之以“新客觀主義”畫家。“魔幻現(xiàn)實主義”則成為文學(xué)評論的術(shù)語被廣泛使用。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特點可以歸納為:神奇的想象、奇妙的事物、表現(xiàn)無意識、將現(xiàn)實與非現(xiàn)實和幻象相結(jié)合等等。這些特點,在托卡爾丘克的小說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xiàn)。但是,她的小說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是有區(qū)別的。首先,托卡爾丘克試圖掙脫一切“主義”的束縛,努力開創(chuàng)一個屬于自己的傳統(tǒng)。這就是為什么她不愿意人們稱她為魔幻現(xiàn)實主義者的主要原因。她喜歡一切新奇的、有個性的東西,魔幻現(xiàn)實主義正合她的胃口,于是她加以借鑒,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獨創(chuàng)性的嘗試。我們很難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歸入某一個流派,托卡爾丘克運用了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手法。她的創(chuàng)作手法隱含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某些片段中,讀者可以從她對修士帕斯哈利斯創(chuàng)作圣女傳過程的描述,窺見其創(chuàng)作狀態(tài)和方式:“實際上他弄不明白自己寫的是什么,有什么意義。
或者他明白了,但不是靠文字,也不是靠思想理解。他躺在地板上,閉著眼睛,一再重復(fù)這些句子,直到它們完全失去意義。”[1]160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她不是靠文字或思想來創(chuàng)作,而是靠一種無意識的意念。她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似乎進(jìn)入了一種被催眠的狀態(tài),意識已經(jīng)無法完全控制她的筆,流瀉于筆端的不是經(jīng)過理性過濾的世界,而是一個“本我”的世界,是世界的“潛意識”。無怪乎她那些奇異的故事、夢幻的語言、古怪的人物,仿佛夢囈般讓人難以捉摸。誠如瞿瑞所言:“即使放在整個世界文學(xué)史中,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依舊是一個古怪的異類。她的作品似乎繞開了文學(xué)中的所有流派和‘主義’,并且身姿輕靈地從任何試圖定義它們的詞語中逃逸出去。她的敘事聲音獨一無二,兼具遼闊高遠(yuǎn)的音域和輕靈慈悲的嗓音,仿佛來自一個混合了天使、精靈、女巫、幽靈和隱居于世界心臟地帶的人類女性的神秘生靈。”[4]
其次,《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的人物之間常常沒有必然聯(lián)系,幾個故事交錯穿插,但故事與故事之間也沒有必然聯(lián)系。這一點和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品不同,在魔幻現(xiàn)實主義代表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人物之間有著密切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并且有貫穿始終的故事情節(jié)。只是在此基礎(chǔ)上增加了魔幻的手法,諸如變現(xiàn)實為神話、變現(xiàn)實為夢幻、時空交錯等等。而托卡爾丘克則完全脫開了人物形象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故事的連貫性,代之以碎片化的圖片的拼接。
最后,傳統(tǒng)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品透露出某種歷史的沉重感和滄桑感,托卡爾丘克的小說滲透紙背的是對人生、世界、宇宙的哲學(xué)思考。魔幻現(xiàn)實主義產(chǎn)生在20世紀(jì)中期前后,拉丁美洲還處于較為落后的時期。因而,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承載著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歷史重任,中小資產(chǎn)階級作家為主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在作品中抨擊社會弊端、揭露獨裁政權(quán)、表達(dá)對拉丁美洲貧困落后狀態(tài)的不滿,但也往往因為束手無策而流露出虛無主義的觀點和頹唐的情緒。
1962年出生的托卡爾丘克,沒有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受過良好的教育,生活條件優(yōu)越,因此,她沒有那么沉重的歷史負(fù)擔(dān)。這樣,她可以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天賦才能,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表現(xiàn)一切愿意表現(xiàn)的主題。只要樂意,她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自由創(chuàng)作。這就使文學(xué)成為文學(xué)本身,文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多變性、容納性等內(nèi)部特征能夠充分展現(xiàn)。托卡爾丘克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似乎預(yù)示著文學(xué)的“后魔幻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
結(jié)語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小說《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打破了既定的文學(xué)樣式,顯示了對文學(xué)邊界和流動性的探索,她那靈性的洞察力,能夠覺知當(dāng)下人們的所思所想和所需,“如今,我們的思考方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簡單。我們和電腦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改變了我們自身的感知——我們接受了大量迥異的、碎片化的信息,不得不在頭腦中將它們整合起來。
對我來說,這種敘事方式似乎比史詩式的龐大線性敘事要自然得多。”[3]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托卡爾丘克如是說。從她的言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創(chuàng)作是緊跟時代步伐的,是在一種非常自然和放松的狀態(tài)下進(jìn)行的精神體操。心理學(xué)的背景帶給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諸多創(chuàng)作的靈感,她獨辟蹊徑,以一種奇特的創(chuàng)作視角,解讀越來越紛繁蕪雜的世界。她像一個催眠師,又像一個魔法師,先運用催眠手段讓自己進(jìn)入無意識狀態(tài),再“通過一種魔法敘事,用寓言、神話、夢境等超現(xiàn)實方式,將個體在相同情境下產(chǎn)生的迥異體驗,融入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并非神秘,它就存在于每個波蘭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沉痛歷史和破碎社會現(xiàn)狀的縫隙之中。”[7]
參考文獻(xiàn):
[1](波蘭)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M].羅麗君,袁漢镕,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2018年5月重印).
[2]李怡楠.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神秘深邃的文學(xué)旅者[N].文藝報,2018-06-11(005).
[3]凌琪.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輝煌壯麗的文學(xué)拼圖[N].合肥晚報,2018-06-03(A02).
[4]瞿瑞.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收集夢境的文學(xué)女巫[N].北京日報,2019-10-18(017).
作者:李春香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hù)SS
- 2025-01-22語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xué)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guān)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xué)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nèi)容?
- 2025-01-24醫(yī)學(xué)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xiàn)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