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文主義理念下科教館展品創(chuàng)新發(fā)展
時(shí)間:2018年05月24日 分類: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下面文章通過解讀機(jī)械木偶展中的若干大型敘事性金屬機(jī)械劇場(chǎng)展品,分析其展項(xiàng)敘事中的后人文主義主體性表征,可給予國(guó)內(nèi)科技館展品研發(fā)以諸多有益的借鑒。在后人文主義跨界融合理念的指導(dǎo)下,進(jìn)一步對(duì)科教館展品研發(fā)模式提出了建議。
關(guān)鍵詞:技術(shù)文化,人類身體,后人丈主義,機(jī)械劇場(ch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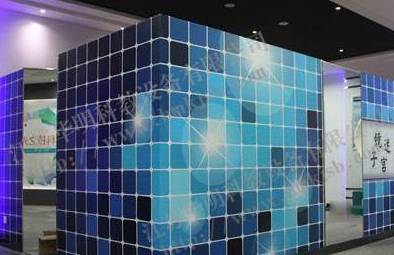
1引言
技術(shù)文化 (technoCUlture)是一個(gè)較新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yǔ),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開始廣泛使用語(yǔ)于西方學(xué)術(shù)界,指的是技術(shù)和文化之間的互動(dòng)以及技術(shù)與文化雜糅形成的政治 。該詞在學(xué)術(shù)界的興起要?dú)w功于康斯坦斯 ·彭利和安德魯 ·羅斯于 1991年編輯 出版的《技術(shù)文化》(Technoculture)一書。技術(shù)文化與科學(xué)文化 (scientific CUlture)同是當(dāng)代科技哲學(xué)文化轉(zhuǎn)向的產(chǎn)物 ,科學(xué)文化是科學(xué)人在科學(xué)活動(dòng)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態(tài)度,或者是他們自覺和不自覺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態(tài)度 ,即科學(xué)共同體內(nèi)部的規(guī)約,是知識(shí)、技藝和態(tài)度的組合 。
二十世紀(jì)無疑是人類科技迅猛發(fā)展的一百年,與科學(xué)的進(jìn)步相比,技術(shù)的進(jìn)步對(duì)人類生活的影響更加快速,實(shí)時(shí)更新著人類對(duì)自我的認(rèn)知;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于對(duì)人類身體的認(rèn)知、視覺化和操控,讓 “我們”與其他種族和機(jī)器人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控制論把人類的身體既視為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者,又視為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納米技術(shù)讓我們把審視自我的基本單位縮小到了原子級(jí)別,身體只是在某種環(huán)境下無數(shù)原子的組合物 (assemb1ages) 。技術(shù)文化研究學(xué)者黛布拉 ·肖在2008年出版的《技術(shù)文化:關(guān)鍵概念》 (Technoculture: The KeY Concepts)一書中甚至提出了 “技術(shù)身體” (technobodies)一詞,身體與權(quán)利、空間、美學(xué)、語(yǔ)言并列成為了技術(shù)文化研究的關(guān)鍵概念 u 。堅(jiān)持身體性的技術(shù)文化研究需要打破原有秩序的束縛,在技術(shù)調(diào)節(jié)的文化中尋找人類表達(dá)對(duì)技術(shù)改造后身體的認(rèn)知的新途徑。
2機(jī)械木儡展中的后人文主義
法國(guó)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家吉爾 ·德 勒茲 (Gil1es De1euze)和心理分析學(xué)家菲利克斯 ·瓜塔里 (FeliX Guattari)在 《千座高原:資本主義和精神分裂》 (A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1987)中提出了 “成為少數(shù)” (becoming-minoritarJan) 這一概念 ,并對(duì)存在 (being)與成為 (becoming)做出了重要的區(qū)分:在存在的視角下,世界被劃分為了不變的類別:男性/女性,人類/動(dòng)物,而在成為的視角下,世間萬(wàn)物都處于動(dòng)態(tài)流中,占據(jù)的空間也沒有固定的邊界,所以男性和女性存在于一個(gè)連續(xù)體中,人與動(dòng)物也不再被視為截然不同的范疇。
本文借用近年來活躍在科技文化研究領(lǐng)域的加州大學(xué)河濱分校科技文化專業(yè)謝莉爾 ·文特教授 (Sherryl Vint)對(duì)德勒茲和瓜塔里相關(guān)理論的闡釋歸納形成的 “成為他者” (Becoming Other) 踟一詞做為對(duì)后人文主義基本哲學(xué)范式的描述,結(jié)合當(dāng)代意大利哲學(xué)家、女性主義理論家布萊 ·多逖 (Rosi Braidotti) 的《后人類》 (The Posthuman,2013)中基于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哲學(xué)理論進(jìn)一步推導(dǎo)出的后人類身體的三種可能范式:成為機(jī)器 (BecomingMachine)、成為動(dòng)物 (Becoming Anima1)和成為微粒 (Becoming Imperceptible) 。
這次展出的機(jī)械木偶展的主體部分始建于 1996年,部分展品已經(jīng)在歐洲巡回展出了20年之久,可謂經(jīng)久不衰,這次來到亞洲首站的廣東科學(xué)中心,也是受到了當(dāng)?shù)赜^眾的如潮好評(píng)。該展項(xiàng)的目的除了向觀眾展示機(jī)械傳動(dòng)的科學(xué)原理,更重要的是表達(dá)技術(shù)對(duì)我們?nèi)粘I畹挠绊懀磻?yīng)了后人類的生存境況。觀眾看到的一個(gè)個(gè)展品,不僅感慨于其精巧的機(jī)械裝置,更被展品的創(chuàng)意所打動(dòng),與其說觀眾是為眼前的一件件初次蒙面的展品所震撼,不如說是在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序廳開章明義:你是人還是機(jī)器? “如果你有一個(gè)身體,那么你可能兩者都是 i你的胳膊和腿可以做成杠桿,你的門牙是楔,你的肌腱是彈簧”。
在黑幕環(huán)繞的展廳中,在特殊的光影效果下,隨著一段段樂曲的想起,不同的機(jī)械木偶輪流啟動(dòng),齒輪連著杠桿,懸繩連著鈴鐺,裁縫踩著踏板,一個(gè)個(gè)故事,通過設(shè)計(jì)精密的部件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這種劇場(chǎng)式敘事的模式在科技館中并不算稀奇,但以機(jī)械作為主角的后人類敘事實(shí)屬罕見,之前在少部分歐洲科技館中設(shè)立了機(jī)器人劇場(chǎng) ,機(jī)器人形似人類,說著人類的語(yǔ)言,模擬人類的表情,震撼效果卻不及本次的大型機(jī)械木偶。下面就以幾個(gè)大型金屬機(jī)械劇場(chǎng)展品的身體敘事為例展示后人類成為他者的三種范式。
“當(dāng)我被問及我的靈感來自哪里,我只能說 ‘來自天堂’。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不是我創(chuàng)造了機(jī)器,是他們創(chuàng)造了他們自己,我只是輔助者” ,愛德華這樣評(píng)價(jià)這些機(jī)械劇場(chǎng)展品的創(chuàng)作,與傳統(tǒng)的提線木偶不同,這些機(jī)械可以擺脫人類的操控,展開自敘事,向觀眾展現(xiàn)了生與死之間無盡的循環(huán)。用金屬機(jī)械作為主角,配合音樂、燈光進(jìn)行劇場(chǎng)式的表演,雖然機(jī)械代提了血肉之軀,但觀眾卻能從中獲得共鳴,機(jī)械式的重復(fù)恰好與當(dāng)代人的生活節(jié)奏產(chǎn)生了共振,燈光下的機(jī)械是 “成為機(jī)器”的后人類身體,由廢舊的金屬物品等舊物拼接而成,打破了人類身體的局限,更加包容地接納了多元化的組件,用后人類的身體栩栩如生地訴說著一段段或荒誕或悲傷的故事。
“大師與瑪格麗特” (2002)根據(jù)俄國(guó)作家米 ·布爾加科夫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同名小說 《大師與瑪格麗塔》創(chuàng)作。小說講述了瑪格麗塔為搭救被關(guān)入精神病院的愛人一大師,與偽裝成馬戲團(tuán)藝人的惡魔一撤旦 (沃藍(lán)德)交易的故事,撤旦提出的條件是要她扮演撒旦舞會(huì)的女王。在小說中,撒旦 (沃藍(lán)德)來到 1930年代的 5月的莫斯科,目的對(duì)外宣稱是做魔術(shù)表演,這個(gè)展品就展示了女巫 (瑪格麗特)與惡魔 (撒旦)的共同狂歡。
撒旦的形象由小說中的具象化男性沃藍(lán)德變?yōu)榱苏蛊分械膭?dòng)物頭骨,處于最上位,狂歡化的場(chǎng)景讓觀眾聯(lián)系到中世紀(jì)的嘉年華盛會(huì),共同之處在于關(guān)系的倒置,撒旦代表的黑暗籠罩著整個(gè)展品,周圍的鏈條仿佛其張開的雙臂,將世間的一起都拽入了黑暗之中。底層托盤上旋轉(zhuǎn)的戴眼鏡頭像就是被 “鎮(zhèn)壓”在精神病院的大師,反映了 1930年代蘇聯(lián)文人壓抑的生存境況。
“東方快車” (2002)中有一個(gè)相對(duì)完整的女性人物形象,這個(gè)女性的頭部是與撒旦的頭部如出一轍的動(dòng)物頭骨,在俄語(yǔ)中,東方快車是死亡的意象,在俄語(yǔ)中總是呈現(xiàn)陰性,即表現(xiàn)為女性,駕駛著一列火車穿過俄國(guó)的茫茫草原,疾馳著駛向死亡的彼岸。讓人聯(lián)想起俄國(guó)1917-1923年間讓人絕望的革命和內(nèi)戰(zhàn),交戰(zhàn)雙方乘坐列車穿越俄國(guó)廣袤的土地,奔赴戰(zhàn)場(chǎng),奔赴死亡。又如 “自畫像” (2002)配樂是一首俄國(guó)傳統(tǒng)的手搖風(fēng)琴,講述了離開故鄉(xiāng)和愛人的悲嘆,其中人類的形象也是動(dòng)物頭像和假肢的混合體,展品的名字更加耐人尋味,似乎成為了全人類的自畫像,表現(xiàn)了 “成為動(dòng)物”的后人類身體。
在 “勿忘我 (俄羅斯三套車)” (1996)中,趕車人的身體變得更加模糊,似乎只剩下機(jī)器式的頭部和用來踏車前行的雙腿,人的身體與代表俄羅斯國(guó)家機(jī)器的三套車合為一體,表現(xiàn)了 “成為微粒”的后人類身體的流動(dòng)性。果戈理的《死魂靈》一書的結(jié)尾處把俄羅斯比作一駕不可思議的飛鳥般疾馳的三套車,遠(yuǎn)遠(yuǎn)奔馳而去,象征著國(guó)家的光明前, “俄羅斯,你究竟要飛到哪里去?回答我!她沒有答復(fù) ”只有車鈴在發(fā)出美妙迷人的叮當(dāng)聲,只有被撕成碎片的空氣在呼嘯,匯成一陣狂風(fēng),大地上所有的一 切都在旁邊閃過,其他的民族和國(guó)家都側(cè)目而視,退避在一旁,給她讓開道路。三套馬車以及趕車人從一個(gè)角度展現(xiàn)了俄羅斯民族的精神和性格。車夫們通過歌聲訴說人生的艱辛、對(duì)親人的思念:歌聲時(shí)而高亢歡快,時(shí)而低沉壓抑;歌聲與馬蹄聲、鈴鐺聲交織在一起,回響在無垠的原野上空,匯成一支人生的交響曲。
3結(jié)語(yǔ)
在技術(shù)高速發(fā)展的二十一世紀(jì),技術(shù)文化研究在理論層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后人文主義轉(zhuǎn)向,科技館作為科學(xué)文化和技術(shù)文化的載體與傳播者,如何在工作實(shí)踐中作出相應(yīng)的創(chuàng)新與變革無疑是科技館面臨的一大考驗(yàn)。機(jī)械木偶劇場(chǎng)就對(duì)這一問題作出了很好的詮釋,其展品大多以運(yùn)動(dòng)中的機(jī)械或動(dòng)物為主題,或戲謔,或荒誕,以小說中的場(chǎng)景為認(rèn)知背景,表現(xiàn)了向著或美好或危險(xiǎn)的未來飛奔的大無畏精神,其中人類形象的表現(xiàn)手法體現(xiàn)了當(dāng)代西方技術(shù)文化中的后人文主義轉(zhuǎn)向,不再以具象化的人類身體作為主角,而采用跨界拼接的方式,將機(jī)器、動(dòng)物、環(huán)境等傳統(tǒng)意義上的他者融入了主體的范疇,傳達(dá)了成為機(jī)器、成為動(dòng)物、成為微粒的后人類哲學(xué)范式。
機(jī)械劇場(chǎng)的展示形式對(duì)于國(guó)內(nèi)科技館的展項(xiàng)研發(fā)具有借鑒意義,在科學(xué)傳播中融入了豐富的文學(xué)敘事手法,用科學(xué)、技術(shù)、文學(xué)、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形式生動(dòng)地描繪了當(dāng)代人類的生存現(xiàn)狀。在科技館展品研發(fā)設(shè)計(jì)的過程中也需要注意技術(shù)文化中的后人文主義轉(zhuǎn)向,為了研發(fā)出與后人類轉(zhuǎn)向相適應(yīng)的展品,我們需要將跨界的思想銘記心間,注意展品的多元化設(shè)計(jì),消解觀念中固有的界限,從觀眾的體驗(yàn)與感知出發(fā),在不同領(lǐng)域的知識(shí)點(diǎn)之間建立聯(lián)系,使之融合為流動(dòng)的統(tǒng)一體,可以邀請(qǐng)不同領(lǐng)域、不同專業(yè)的人士共同參與展品研發(fā),比如注重認(rèn)知體驗(yàn)的美國(guó)探索館,常年都有駐館藝術(shù)家、學(xué)校教師和科學(xué)家,共同進(jìn)行展項(xiàng)的研發(fā)。
從觀眾主體性的角度出發(fā),對(duì)于后人類而言,機(jī)器已經(jīng)成為了身體的一部分,比如手機(jī)就是最為典型的人類身體的延伸,展項(xiàng)可以設(shè)計(jì)觀眾用手機(jī)參與互動(dòng)的方式,通過技術(shù)手段讓觀眾實(shí)現(xiàn)仿生或者成為動(dòng)物都是與后人文主義相適應(yīng)的展項(xiàng)設(shè)計(jì)理念,還要注重布展環(huán)境的營(yíng)造,讓觀眾擁有變成一顆渺小微粒的安全感和融入感。
相關(guān)閱讀:廣西文化館老師評(píng)副高職稱需要幾篇論文
廣西文化館老師評(píng)副高職稱需要發(fā)表3篇論文,其中包括撰寫本專業(yè)或相近專業(yè)論文2篇,另外也要求在省級(jí)以上刊物公開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1篇,或者公開出版學(xué)術(shù)著作、教材或譯著1部。
- 以陶身體的數(shù)位系列作品為例探究其創(chuàng)作理念及審美內(nèi)涵
- 韓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學(xué)科教育的現(xiàn)狀和啟示
- 公共圖書館服務(wù)平等、開放、共享理念解析
- 純粹理性的運(yùn)用與何種理性的運(yùn)用相對(duì)
- 從中國(guó)傳統(tǒng)元素談繪畫創(chuàng)作實(shí)踐
- 基于OBE理念的應(yīng)用型翻譯專業(yè)本科人才培養(yǎng)模式研究
- “后碳”理念下皖北篾器工藝的生態(tài)傳承
- 茶文化健康理念在體育舞蹈訓(xùn)練排演中的實(shí)踐研究
- 單簧管音樂教學(xué)中如何有效的融入茶文化理念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jià)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dòng)化與控制系統(tǒng)4區(qū)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fā)的藝術(shù)SS
- 2025-01-22語(yǔ)言專業(yè)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yī)學(xué)國(guó)際會(huì)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rùn)色
- 2024-11-22國(guó)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guó)際中文教師能在國(guó)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guó)際中文期刊評(píng)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shí)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fā)展相關(guān)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xué)外文期刊合集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nèi)容?
- 2025-01-24醫(yī)學(xué)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xiàn)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