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祭祀詩中名物記載實用性探析
時間:2022年01月14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 《詩經》作為上古詩歌有著傳授知識的功能,實用性是《詩經》傳習過程中的重要功能,在《國風》和《雅》《頌》類詩歌中對于相同種類事物的記載表現出不同的特點,這與先秦時期的教育觀念直接相關。
【關鍵詞】 《詩經》; 祭祀詩; 實用性; 傳授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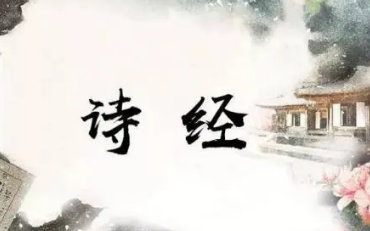
祭祀詩是《詩經》中比較特殊的一種詩歌。 他的寫作意圖并不如《詩經》中的其他篇章那樣以傳授知識作為基本職能,而是具有更為明確的祭祀職能,表達對于祖先的敬仰之情。
自古以來,我國文化中祭祀就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的就是這個現象。 但是,從對《詩經》發生的時代和《詩經》篇章的客觀考察中發現,即使是在這樣一種目的性更為明確的詩體中,還是不能擺脫原始先民在那種特殊環境下無奈產生的傳授目的,只是這種目的性更多被祭祀時的莊嚴性所掩蓋,并且,其間更體現出只屬于祭祀詩所有的傳授特征。
這種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以《周頌》為考察對象,其中對于事物的嚴格區分并不如《國風》當中那么明顯,換言之,祭祀詩對于“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詩歌功能并不如其他詩歌篇章重視。 盡管祭祀詩中的“鳥獸草木”并不多,但是其作者也在有意無意之間在著錄著它們,這些著錄的名物和其他篇章中的事物有時是相似的,但是這些事物在“祭祀詩”這種大的環境中又與其他篇章又表現出不同的特征。
以下以“魚”“馬”“酒”等字作為對象,將《頌》詩中的相同事物與《國風》做一對比,通過比較,展現其中的相同點和不同之處。
一、關于“魚”的記載
在《國風》當中主要有以下幾首詩中有魚的記載:
《周南·汝墳》,高亨先生認為這首詩是作者烹魴魚給丈夫吃,見到魚尾紅得像火一樣,聯想到王室曾經經受烈火焚毀。
《齊風·敝笱》是諷刺文姜和齊襄公幽會所做的詩。 用魚比喻文姜,用破漁網網不住魚來比喻魯國的禮法不能約束文姜。 《陳風·衡門》是隱士(《詩三家義集疏》說是指子夏)甘于貧賤,以詩來表達他的高潔志趣。 其中的魴和鯉都是比喻自己志向的高潔。
《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詩解釋有三:一是《毛詩序》:“《九罭》美周公也。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是方玉潤《詩經原始》:“此東人欲留周公不得,心悲而作此詩以送之也。 ”三是高亨先生認為這首詩創作于西周末年大亂之時,豳邑中的人要去鎬京,他在路上留宿的店主人認為危險,作這首詩勸告他不要去。 這里是以魚喻人。
在《頌》詩中,主要是《潛》中有很多魚的記載。 《毛小序》和《正義》均認為《潛》是冬季薦魚,春獻鮪的樂歌。
二、關于“馬”的記載
《國風》中主要有:《邶風·擊鼓》《周南·卷耳》《鄘風·干旄》。 在《國風》中,馬的所指意義基本都在于其本身,并且在于表現馬的具體情態,以具體形態的描述來體現作者寫作的心情和背景。 在《頌》詩中則主要有《有客》《魯頌·駉》《有駜》,在《有客》中,“客”的“白馬”在殷周的禮儀制度中是尊貴的象征。 “客”騎乘白馬顯示出他的地位,并顯示著有崇高的德行。
在《魯頌·駉》和《有駜》中出現了許多種類的馬。 這種對于馬種類的窮舉式的描述是上古我國農業社會的性質決定的,農業社會本隨著放牧和飼養,其中在這兩首詩中,馬匹成群的出現,并伴隨著它們所駕車輛的威武和莊嚴,這從兩個方面呈現了先秦時期我國社會的狀況,即畜牧業的發展和貴族地位彰顯。 這可以和《潛》詩作一對比,《潛》詩的句式也是“有……有……”式這樣的句式,提示人們在先秦時代,當畜牧業、農業逐漸發達的時期,作為貴族的上層,在祭祀活動中往往以對農業品種廣泛地列舉來表現國力的強盛,其中不乏自美之詞和驕傲的感覺。 相對于《國風》中的對于相同種類的描寫,在《雅》《頌》中對于名物的窮舉式羅列,也許缺少了活潑的氣氛,但是在這里多蘊含著比《風》類詩歌更多的文化因素。 正是由于先秦時期對于祭祀的重視,才使得這些今天列舉得以完好的保存。
三、關于“酒”的記載
在酒的記載中,通過《國風》和《雅》《頌》的比較,可以發現在《國風》詩中只有“酒”而不見“醴”。 而在《國風》中,酒都寄寓著作者在某一事件當中的感情傾向,比如《七月》中的“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這里不單單在于“以介眉壽”的目的所在,更在于在“酒”前作者加入了一個“春”字,這種似乎是無意識的寫法中,酒便隨之而具有了春天所特有的醉人感覺,其中也體現出作者對于生活、對于自然的酒醉似的熱愛。 在后世的詩歌中“春風熏得游人醉”,這其中的酒意與這里的“春酒”有著人類自古以來對于自然的相同感情。 反觀《頌》詩中的描述,會發現在以祭祀為主要用途的詩歌中,酒在感情上的意義已經大大淡化,在這里“酒”常常與“醴”相對應,“醴”是一種甜酒,在今天看來和“酒”是一種被包含的關系,但是,當頌詩的作者將二者放在一起,便使得酒也具有了貴族氣。 酒與醴放在祭祀的環境下,是為祖先和神靈所享用的,所以,這里的酒更多的只是一種祭祀時的象征,祭祀者通過酒的香氣引起祖先的注意,并借酒向祖先表示自己的崇敬。 可以說酒在這里的意義表現得更為理性,展現的是其作為祭品的神圣功用。
由于上古知識傳授途徑狹窄和落后,以及對于農業的極度重視,使得人們對生活經驗格外重視,而有利于口耳傳授的最佳途徑就是詩歌。 詩歌憑借其在韻律上的朗朗上口,使得極容易記憶,這在知識傳授中具有了先天的優勢。 尤其是在下層人們中,和生產實踐相結合,這種勞作之間以及勞作過程中的歌詠形式,不但具有了調節勞作、抒發情感的作用,更使人們加入了生活知識,這在一定意義上和農諺有著相同的作用,在農業知識的傳授中甚至具有更為重要和全面的意義。
另外在上古人們表達方式相對匱乏的狀態之下,人們將復雜生活中的多樣事物都準確地加以區分,就不得不運用更多的名稱加以表達,但是這種努力往往又表現得力不從心,從而使得這種窮舉式的表達不斷升級,有時甚至表現出對于對象物的夸張。 在《雅》《頌》中,很少有關于植物的描述,而多是關于祭器的記載,這也和《國風》形成了對比,這無疑是二者生產者和生產環境所決定的。 荀子在其《正名篇》中說:“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后止。 ”可見在戰國時期,關于事物分類的理論已相當成熟了。 那么作為年代比較久遠的《詩經》作品,正是這種對于事物名稱考究的先導。
上古的采詩之官是迎合著殷周時期統治者觀民風的傳統設立的,《詩經》中的名物,來自民間,源自農業社會及原始先民對于農業知識傳授的需要。 古人用詩的目的之一在于對自身以及組織內部,從“禮儀”角度的管理和約束。 也是在貴族內部的教育中,以《詩經》為媒介,以“禮”為最終目的,同時“禮”也是“德”的體現,即詩與德相對應。 在這樣的傳授中,其中的名物尤其是對名物細加區分的意義,也在于使貴族子弟加深對天下風物的考察,以表現出對于農業的重視,當然這也來源于我國農業社會的本質屬性。
《詩經》作品在這種意義上的實用性,也是造成《詩經》中有些詩歌的相似性,比如《黃鳥》與《碩鼠》,《良耜》與《七月》。 在《黃鳥》中作者運用了許多和《碩鼠》中句式相近的句式。 這中間也許就有采詩之官的作用,在民歌被采集進宮廷之后,經過整理和篩選,是作為貴族中間的教育之用的。 《碩鼠》屬于《國風》,而《黃鳥》在祭祀詩歌中,這之間的聯系可以用這種教習來解釋。 現存《詩經》正是周代社會對于歌詩藝術的多種需要,即省風知氣、頌美諷刺等政治功能、朝廷禮儀功能與藝術消費功能相混合的產物。 所謂省風知氣功能,即《詩經》中部分作品所擔當的描寫民事生活與古老民風傳統的詩篇所承擔的功能,如《豳風-七月》可屬此類; 所謂頌美諷刺功能,大小《雅》包括《國風》中的一些贊美詩與諷刺詩與之相關; 所謂朝廷禮儀功能,像《周頌》和大小《雅》的各類祭祀詩與禮儀詩承擔著這種功能。
正因為《詩經》承擔著如此多的功能,而這些功能的實現與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聯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社會宗教、政治、文化、風俗生活和各個領域的內容,所以,《詩經》中的各種詩篇才體現了原初作者的多樣性,也體現了作品內容的豐富多彩性。
綜上所述,“實用”包括兩方面,即教科書和宗教儀式中的祭祀職能,祭祀詩的實用目的在于宗教。 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對同一事物的重復式描述,由于所使用場合的不同而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這兩種實用性最后被整合,其中一些意象也成為我國詩歌中的獨特范疇。 在先秦社會的各階層中,《詩經》的藝術生產中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他們既是各種活動的參與者,也是不同類型歌詩藝術的原初生產者,《詩經》在這個意義上承擔了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王先謙.荀子集解[M]//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6.
[2]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9:278.
[4]高亨.詩經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9.
[5]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孔穎達.毛詩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9.
[7]趙敏俐,吳湘洲.中國古代歌詩藝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趙亮,男,漢族,河北唐山人,研究生,講師,現任河北師范大學匯華學院教務處處長,畢業于河北師范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