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自然主義生命觀解讀
時間:2021年11月15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內容摘要:盧梭自然主義的生命觀強調通過研究人的生命的自然原則來拯救當時病態的社會。 在自然狀態下,人的生命是良善的,具有自愛心和憐憫心。 當人進入社會狀態后,作為社會文明標準的科學與藝術本身使人的生命開始墮落。 究其原因,是人類逐漸膨脹的物欲破壞了生命的平等。 但是,盧梭并沒有否定社會狀態,否定理性,他將救贖的途徑訴諸于教育,試圖通過回歸自然的生命教育,使人們重新認識生活的意義,實現生命救贖。
關鍵詞:盧梭 自然主義 生命觀 社會契約 道德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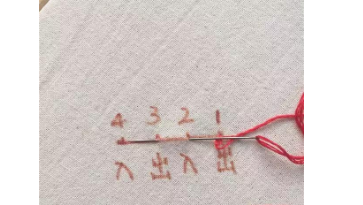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是在差異和矛盾中進行的,啟蒙思想的精神實質是對理性的追求。 與孟德斯鳩、百科全書派人物相比,盧梭的啟蒙思想具有自然主義的內涵。 自然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和社會思潮在哲學史上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 盧梭在構建自己關于生命與道德體系的時候,首先發展的就是他的自然主義思想。 盧梭自然主義思想的出發點,就是崇尚自然,批判現實社會,強調通過研究人的生命的自然原則來拯救當時病態的社會。 正是在這種自然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盧梭形成了自己的生命觀:自然使人良善,社會使人墮落。 盧梭把人的生命劃分為由大自然創造的生命和在社會環境中被重重包圍的生命。 自然的生命是純樸良善的,當生命被社會環境重重包圍,受身體氣質的變化和欲念的不斷沖動,生命開始走向墮落。 然而,盧梭并不像伏爾泰等人所指摘的一樣,主張返回自然狀態,他雖然懷念遠古時代,但他并不是烏托邦主義者。 他主張通過教育的手段,從心理上凈化人們的內心世界,使人的生命的獲得救贖。
一.生命的本真:自然狀態下良善的自我
盧梭把人的生命劃分為由大自然創造的生命和在社會環境中被重重包圍的生命。 為了研究自然狀態下人類生命的基本原則,盧梭曾經走進圣熱爾曼的原始森林去沉思和推測生命的原始狀態。 他在沉思中看見了許多前所未見的美妙景象,發現了已塵封千百萬年的真實事實,他通過觀察和推測總結出生命的自然原則有兩種表現:“一是自愛心,即自我保全的能力,二是憐憫心,不愿意看到同類的生命受到傷害。 ”[1]正是自愛心和憐憫心這兩種自然的情感使自然狀態下的人類溫和,不好斗,從而保全了生命的完整性。 正如盧梭所言:“人天生是善良的”。 [2]
1.自然狀態下的自愛心
生命是自然賦予人的天賦,人人都可以享受。 盧梭說到:“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則是保護他自己的存在; 他首先關心的,是照顧好他自己。 ”[3]一個人如果拋棄了生命,便完全消滅了自己的存在。 因為任何物質財富都不能抵償生命,所以以任何代價拋棄生命,都是違反自然同時也是違反理性的。 盧梭將這種自我保存的情感稱為“自愛心”,自愛心被盧梭肯定為生命的第一原則。 在自然狀態下的人是良善的,生命的欲求與個人能力的大小是相適應的。 自然狀態下的人只有自我保存的欲望和與生俱來的同情心,沒有傷害他人的欲望。 人與人之間天賦的差異對于個體生命來說并無意義。 人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對自己生存的感情,最原始的關懷就是對自我保存的關懷。 自然供給他們維持生命所需的食物。 饑餓以及種種欲望使他們學會了克服自然的障礙,變得更勇敢。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過著簡單而淳樸的生活,他們的欲望極少。 他們是自由自主的人。 正如盧梭在《愛彌兒》中所說:“自愛心所涉及的只是我們自己,所以當我們真正的需要得到滿足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滿意的; 可見,敦厚溫和的性格產生于自愛。 ”[4]當人的欲望減少且處處不與他人計較時,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2.自然狀態下的憐憫心
盧梭設想的自然狀態是一個完美社會的邏輯起點,人在自然狀態下是淳樸而美好的,人們不知道什么是惡,只有本能的憐憫之心,因此可以和平相處,沒有爭斗。 這種自然的情感是形成建設性人類關系的基礎。 在盧梭看來憐憫心和自愛心一樣都是表達人之天性的自然情感,是優先于理性的原則。 盧梭說道:“我們如此柔弱又如此易于遭受苦難,憐憫心是我們最因該具備的稟性:它是最普遍有用的美德,在人們開始理性思考以前就產生了。 ”[5]盧梭認為憐憫心是產生社會美德的基礎。 在憐憫心的觸動下,我們看到那些遭受苦難的人,想去幫助他們。
盧梭將憐憫心看作自然狀態下人的本性中最觸動人心的情感。 他在《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以及之后的著作《愛彌兒》中都有詳細的描述,其意義在于首先,為論證自然狀態下生命的良善提供一個最好的論據。 盧梭假設早期的人類生活處于一個非競爭的狀態,人類可以友好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爭強好斗。 人們在看到他人遭受不幸時,給予幫助,這給我們提供了自然狀態下人與人之間可以和諧相處的一個充分的理由。 其次,為人們尋找一條通往幸福之路的原則。 盧梭認為,要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就需要促使他心中產生善良、博愛、憐憫、仁慈的自然情感,能夠設身處地的想到那些更需要被同情的人,能夠感受到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盡可能多的去設想別人遭受痛苦時的感覺。 只有這樣,人們才能遠離嫉妒、貪婪、仇恨以及所有一切有毒害的欲念,使人感受到幸福。
盧梭并不是十八世紀提出“重返自然”的第一人,在當時的法國,關于對原始生活贊美的言論數不勝數,只不過說法大同小異。 卡西勒在《盧梭問題》中的敘述:“人們渴望對原始人風俗的描繪,人們越來越迫切地想對原始的生活方式有更廣泛的了解。 狄德羅將布干維爾南太平洋之行的一份報告作為起點,用抒情詩一般的語言歌頌了原始人的簡樸、天真與幸福。 ”[6]當盧梭寫作《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時,上述趨勢已大行其道。 但是盧梭并不像人類學家或者歷史學家那樣僅僅是將事實還原。 盧梭所訴諸的是試圖從自然狀態中尋找他提出的原則和假設的證據。 盧梭坦言,尋找自然狀態下本真的自我即不需要回到已經逝去的遠古時代,也不必環球旅行,每一個人自身都保留著自然狀態下良善的自我,只是被身處社會中人為的自我所掩飾,人人尋找表面的幸福,因過份追求奢靡的物質生活而忽視了人本質中最淳樸的幸福,這是導致生命墮落的根本癥結。
二.生命的墮落:社會狀態下不幸的根源
盧梭發現與其他動物的生命相比,人的生命有一種趨于完善和向前發展的能力。 而盧梭卻發現這種生命自我完善的能力包含著對抗,同時也是一種退步。 人從自然狀態進入市民社會以后,就有了貪婪和吝嗇,他們為了爭奪個人利益而互相爭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虛偽,罪惡。 盧梭認為:“后來的種種進步,表面上看起來是使個人走向完善,但實際上卻使整個人類走向墮落。 ”[7]人類生命的墮落有兩種原因。 第一,是作為社會文明標準的科學與藝術本身使人的生命開始墮落,另一個原因則是對財富的追求破壞了生命的平等。
1.科學與藝術使生命腐蝕
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的開篇提及:“藝術、文學和科學扼殺了人類與生俱來感受自由的能力,導致他們喜歡自己的奴役狀態,使他們變成所謂的文明人。 ”[8]接下來他對這一觀點做了進一步的論證,人們在進行科學、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會被自己獲得的榮譽腐蝕,淪為追求利益和名譽的奴隸。 這里盧梭注意到科學、藝術與道德的相關性。 科學、藝術的繁榮可以使人的道德墮落,從而腐蝕人的生命。 盧梭認為科學和藝術的進步是由多種動機促成,其中,利益的驅使是不可忽視的動機。 他并不是反對科學和藝術的進步,而是揭示那些為了個人利益而探究科學和創造藝術的人,一旦知識等同于榮譽和尊重,人們就會將研究和創作當成個人取得威望和榮譽的途徑。
可見盧梭并不反對科學和藝術,相反,他指出:“只有培根、笛卡爾和牛頓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天才,他們的成就代表了人類理解力的巔峰。 ”[9]盧梭認為,即使沒有溢美之詞或者顯赫的威望,他們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但是,在十八世紀的法國,虛假的學問層出不窮,為獲得豐厚的回報,而夸夸其談的虛假學者極其常見。 他們提出觀點得出結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引人注意和獲得稱贊,而不管這個觀點和結論是多么不切實際。 盧梭認為當時的社會風氣不僅沒能讓青年人學到鑒別真理與謬誤的本領,反而學會了善于詭辯的技能,混淆是非,讓人分不清真偽。 盧梭抨擊的正是這種為追求名利而混淆是非的風氣,人們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科學和藝術中去,目的卻不是為了追求真理,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在追求名利的同時也失去了社會責任。 事實上不是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導致生命的墮落,而是學術界和藝術界追求利益和名望的奢靡浮夸之風腐蝕人的道德,使生命走向墮落。
2.物欲破壞了生命的平等
盧梭在《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一書中黑白分明的論述了自然狀態下生命的良善和社會狀態下生命的墮落,過度開發的文明破壞了人類的天真無邪,因虛榮和貪婪導致物質欲望的過度膨脹,破壞了自然狀態下生命的平等。
盧梭從人的心理和需求角度揭露了人如何脫離原有的善良的自我,逐漸失去憐憫心,揭露了當時社會人的生命腐化和墮落的心理原因。 類生活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一步步變化,生命也逐步開始墮落。 人與人之間的攀比心導致了社會萬象。 人的才能和欲望的不同打破了原始的平衡。 貧富差距的出現,攀比心和虛榮心導致了生命的墮落。 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使自己高于他人,人們開始為了利益去傷害他人,人自然的憐憫心被忽略。
隨著人類的繁衍,人們的痛苦也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當人類逐步學會使用工具,他們開始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用來為自己安排各式各樣的享受。 這是人們無意間給自己套上的枷鎖,也是痛苦開始的根源。 當舒適的享受成為了習慣,人們便逐漸感受不到享受帶來的幸福,而把它看成是真正的需要。 于是得不到享受時人們會覺得痛苦,而有了這些享受卻不覺得是幸福了。
過度安逸使人們耗盡了精力,人們因貪圖舒適的享受而失掉了真正幸福和對高尚道德的追求。 所有的社會進步使人類和他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 生活的過度放縱,體力的疲勞,精神的枯竭讓人產生無盡的煩惱,這一切都是生命墮落的憑證。 由于無數新的需要的不斷滋生,人們不能不被這些欲望所支配,變成欲望的奴隸。 人們在欲望的驅使下不斷創造財富,同時他們開始不斷設法關注自己的利益。 這樣就使人與人之間變得奸詐和虛偽。 積聚財富的狂熱使人產生隱蔽的嫉妒心。 這種嫉妒心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傾軋,以及利害沖突的發生。 財富破壞了人的平等。 扼殺了人的自然憐憫。 于是人變得慳吝,貪婪。
盧梭的《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有著許多合理內核,閃耀著歷史辯證法的光輝。 然而,盧梭在論述社會不平等的起因和歷史發展過程時,并沒有考慮到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而是從人的主觀心理、從人性的貪婪和欲望的膨脹等情感因素來加以說明,這就不能科學地解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因此,它終究未擺脫歷史唯心主義的局限。
3.對墮落根源的再審視
盧梭并不是要回到原始狀態,也不是批判社會狀態。 相反,盧梭對人類對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持肯定態度的。 盧梭認為人類從自然狀態進入到社會狀態,他們行為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具備了道德性。 正義代替了本能,義務代替了生理的沖動,權利代替了貪欲,理性成為了人類行為處事的重要原則。 在社會狀態下,人的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鍛煉和發展,獲得了新的能力——理性,如果人類沒有濫用這種能力,社會狀態下的人類應該是幸福的,因為正是這種社會的進步使人的生命具備了社會的屬性,盧梭從心理上分析人不幸的根源是人的欲念與能力的不平衡所導致。 當欲念超過了能力,而無法得到滿足時,生命便開始走向墮落,因此,盧梭主張應當通過教育的方式,倡導人們減少欲念,重視道德品行,在追求至善生活的道路上實現生命救贖。
三.生命的救贖:回歸自然的生命教育
在自然原則的背景下,盧梭通過考察人一生的經歷,提出了自己的生命觀:人的生命可以說是誕生過兩次:“一次是為了存在,另一次是為了生活。 ”[10],欲念是人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人之有欲念是人的天性,因此,欲念成就了人的第一次生命。 然而,生命由于欲念的不斷膨脹而日趨墮落。 為了防止生命的自然之善受到腐蝕,教育承擔了對生命的救贖功能,只有通過教育,教會人如何在生活中減少欲望,才能保持人性之善,實現對生命的救贖,成就人的第二次生命的誕生。 “教育救贖實現的是一種內在的救贖,通過拯救人的內心來實現人的幸福。 ”[11]
盧梭的生命教育思想是從他的自然原則出發的。 他認為人生而自由,只是后來進入文明狀態之后,人類之間的奴役、不平等使得人們逐漸失掉了自己的本性。 為了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他主張對兒童進行適應自然發展過程的“自然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服從自然的永恒法則,聽任人的身心的自由發展。 概括而言,他的生命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回歸自然的教育。 《愛彌兒》是盧梭專門論述教育思想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充分展現了盧梭自然主義的生命教育思想,并且對現代生命教育產生深刻地影響。 在《愛彌兒》中,盧梭認為兒童教育應該改變片面追求書面知識的狀況,應當重視兒童的情感教育。 主張情感先于理性的教育思想。 他尤為重視讓兒童通過自然教育來學習。 這種自然教育就是生活和實踐,讓孩子從真實的生活與實踐中去感受和學習他需要的知識。 同時,在生活和實踐中去感悟生命的真正意義,樹立正確的生命觀和世界觀。 為此,他主張采用實物教學和直觀教學的方法,反對抽象的啃書本的教學方式,使兒童的自然天性得到最本真的釋放。
二是教育階段論。 盧梭根據人的年齡將教育分為相應的幾個階段,并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的原則、內容和方法。 總體來說,盧梭對教育內容按照年齡不同來進行體育、智育、德育的劃分,這一思想也許在當今的教育實踐中會存在硬性的斷裂感,但是這種思想背后所蘊含的生命發展規律卻是值得當今的教育工作者們借鑒的,即我們應根據人的生命發展所處不同階段而“因齡施教”,以便讓學生獲取在他所處的實際年齡階段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知識,而不會因過度施教而損害他的性格,扭曲他的心靈。
盧梭認為教育的意義在于教會人們如何保護自己,如何面對困境,經受住命運的打擊,教會人們不要過分注重金錢和物質,減少欲念提高能力。 生命是短暫的,生命教育的目的“不在于防他死去,而在于教他如何生活。 ”生活不僅僅是呼吸,而是活動,是用人身體的各個器官,人的所有才能去體會生活的意義。 生活的最有意義的人并不就是年歲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對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參考文獻
[1][2][5][7][法]盧梭著.李平漚譯,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M],商務印書館2005:8,135,76,95
[2][法]盧梭著.李平漚譯,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商務印書館2005:135
[3][10][法]盧梭著.李平漚譯,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2011:5,28
[4][法]盧梭著.李平漚譯,愛彌兒[M],商務印書館2019:320
[5][法]盧梭著,李平漚譯,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商務印書館2005:76
[6][德]恩斯特·卡西勒著,王春華譯,盧梭問題[M],譯林出版社,2009:43
[7][法]盧梭著,李平漚譯,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商務印書館2005:95
[8][9][法]盧梭著,何兆武譯,論科學與藝術[M],商務印書館,1963:8,35
[9][法]盧梭著,何兆武譯,論科學與藝術,商務印書館,1963:35
[10][法]盧梭著.李平漚譯,愛彌兒[M],商務印書館2019:315
[11]林泉,高宣揚.論盧梭啟蒙思想的獨特性及其幸福導向[J].求是學刊,2014,41(03):43-49+2
作者:馬小川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