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i)�w�Ď�(k��)����ˮ�G־���u(p��ng)�֡�
�r(sh��)�g��2020��11��21�� ���(l��i)���ČW(xu��)Փ�� �Δ�(sh��)��
����ժ Ҫ����ˮ�G־���u(p��ng)�֡��Ǻ�(ji��n)����ˮ�G������һ��(g��)�dz���Ҫ�ı��ӣ��P(gu��n)�ڴ˱��İ汾�о������� ͨ�^(gu��)��(du��)��桶ˮ�G־���u(p��ng)�֡����ձ�݆���²ر����ձ���(n��i)�w�Ď�(k��)�ر��ɂ�(g��)�汾�ıȌ�(du��)�о����l(f��)�F(xi��n)�˶���ͬ�棬Ȼ�����u(p��ng)�ֱ��ij��̱����҃�(n��i)�w�Ď�(k��)�����̕r(sh��)�g����݆���±�; ݆���±������ް棬�ڰ��ĵȷ���������ͬ���Ҕ��̎�����a(b��)��Ȼ��֪���ް����ղ�������߀�ǿ��̕�(sh��)�����顣
�����P(gu��n)�I�~����ˮ�G����; �u(p��ng)�ֱ�; ݆���±�; ��(n��i)�w�Ď�(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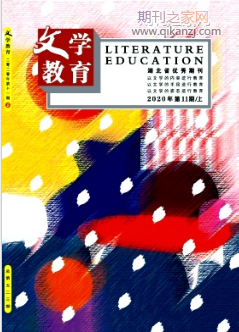
������ˮ�G־���u(p��ng)�֡���ȫ�Q(ch��ng)�顶�������a(b��)У��ȫ�����xˮ�G־���u(p��ng)�֡���ȫ��(sh��)��Ӌ(j��)25������18���(sh��)���}�������һ�㺆(ji��n)�Q(ch��ng)���u(p��ng)�ֱ��� �u(p��ng)�ֱ��ǬF(xi��n)�����������Rȫ�ĺ�(ji��n)����ˮ�G�����п��̕r(sh��)�g�����һ����ͬ�r(sh��)Ҳ����o(w��)��(zh��ng)�h��һ���ɽ��(y��ng)�����ġ�ˮ�G������ �����xȡ�ɷN�����^���������u(p��ng)�ֱ��M(j��n)���о���һ�N���ձ��չ�݆���²ر�����һ�N���ձ���(n��i)�w�Ď�(k��)�ر��� ��Ҫ���о�?j��)?n��i)���Ѓɂ�(g��)���棬��һ���ɷN���ӵĻ�����r��B�Լ����R(sh��); ������ɷN���ӵıȌ�(du��)�о���̽�������Ƿ����̱����Ƿ�ͬ�桢���߿������ȵȆ�(w��n)�}��
�����ČW(xu��)Փ��Ͷ�忯����ČW(xu��)��������һ������̎��͌W(xu��)���Č�(zhu��n)�I(y��)���Ҳ��ȫ��(gu��)Ψһ��һ���ռ��ČW(xu��)�����Č�(zhu��n)�T(m��n)����������ּ�ǣ����ČW(xu��)�ă�(n��i)���M(j��n)�н��������ČW(xu��)���ֶ��M(j��n)�н��������ČW(xu��)���ˑB(t��i)�M(j��n)�н�����
����һ��݆���±���ˮ�G־���u(p��ng)�֡��śr
����݆���±���ˮ�G־���u(p��ng)�֡���ȫ��(sh��)��Ӌ(j��)�˃�(c��)��������ã�����ʮ����ȱ�~�� �˕�(sh��)���~���}ˮ�G������������“�캣��”���֣�����“�캣��”���������Õ�(sh��)��(xi��)�w��(xi��)�ɣ������S����(sh��)���`�J(r��n)��ˡ��}ˮ�G���������������캣�ء� �䌍(sh��)������ˣ����^“�캣��”����ָ“�캣”�@��(g��)�����ؕ�(sh��)������˼�� “�캣”���˕�(sh��)��ԭ�����캣��ɮ��(1536—1643)���ַQ(ch��ng)����۴���̖(h��o)�Ϲⷻ���ǘ�(l��)Ժ�����ձ�����(h��)���r(sh��)�����_(t��i)�ڵ�53��؞�����´�Ļ���ЙC(j��)�ĺ������࣬�ձ��vʷ���Д�(sh��)���L(f��ng)����� “�캣��”ָ���캣��ɮ�������x�������A��֮���Ճ�(ch��)��݆���´�����——����ɮ���`�Ã�(n��i)�ă�(n��i)�����z���� �@Щ��(sh��)�������캣��ɮ���x�^(gu��)�ĕ�(sh��)������(xi��)�ĵ伮��Ҳ��ɽ�T(m��n)�����ľ�ٛ(z��ng)����߀�г�͢����ľ�ٛ(z��ng)���� ��ˮ�G־���u(p��ng)�֡�����(c��)�����@Щ��(sh��)��֮�g�� ������T(m��n)���֮�ص�݆����֮���ԕ�(hu��)�ղ��@ЩС�f(shu��)��Ҳ�����鮔(d��ng)�r(sh��)ɮ����Â��W(xu��)��(x��)�h�Z(y��)��(du��)Ԓ(hu��)�Ľ̲ġ�
������(gu��)�����������ҵ����M(j��n)��݆�����M(j��n)��̽�صČW(xu��)���������������� ���������ձ��L��(sh��)֮�H����1941��ͨ�^(gu��)�ձ��|���Ļ��W(xu��)Ժ�|���о����о��T�S���������֪�����÷���(k��)�в����Ї�(gu��)�ŵ�С�f(shu��)������ͨ�^(gu��)�S���������òؕ�(sh��)Ŀ䛣���(j��ng)ݚ�D(zhu��n)�c�S�������ͬ��݆�����L��(sh��)�� ���gҊ(ji��n)����֮ǰһֱδ���T�����ġ�ˮ�G־���u(p��ng)�֡���������ˮ�G־���u(p��ng)�֡�ȫ��(sh��)�Ĕz�˕�(sh��)Ӱ�� �؇�(gu��)����Ƭ��Ƭ��I(xi��n)�o���Ļ���(����������ČW(xu��)������)��1956�����ČW(xu��)�ż�������Ӱӡ���档 ֮�������������P(gu��n)���u(p��ng)�ֱ���Ӱӡ���������ČW(xu��)�ż�������ķ�ӡ����
���������f(shu��)��������ɽ֮�е�݆���±���ˮ�G־���u(p��ng)�֡��܉��Ҋ(ji��n)���ա��ɞ�F(xi��n)��(ji��n)����ˮ�G�����������еı��ӣ�������������Ī���ɡ� Ȼ���P(gu��n)�������������Ĕz݆���±�߀��һ�ι�������Ҫ�ڴ˳��塣 �ձ��ĝh�W(xu��)����L(zh��ng)��Ҏ(gu��)��Ҳ������(du��)�����������Ĕz݆���±��H���~��
������(zh��n)�r(sh��)�����Ζ|����W(xu��)�v���r(sh��)���������وD��(sh��)�^�ĺ͡��h��(sh��)ȫ���g�[��һ�¡� ����Ҋ(ji��n)�����}��“�չ�����òؕ�(sh��)Ŀ䛳���”���Ͽ��Ď�(k��)�f�ر���������õ�“��ƿ÷Ԋ(sh��)Ԓ(hu��)ʮ����”��ӛ�d�� ��ʮ�ָ��d�ظ��V��ͬ���S����������S������V��������������֪�Y��(ji��)��������ͨ�^(gu��)���(w��)ʡӲ��Ҫ��ȥ݆���£������S�������ͬ���J�M(j��n)��݆���¡� �@�r(sh��)�Ӵ������ǬF(xi��n)�ڵĈ�(zh��)���L(zh��ng)���T(m��n)Ժ�������@�N�����ه(l��i)�ͺ�ĘƤ���ˌ�(sh��)�ڞ��y�������������Ĕz���҇�(gu��)����Ĺŕ�(sh��)���w��(gu��)���ִ����س��棬������ӛ�ˌ�����ĕ�(sh��)�ͽoԭ���ߣ�����һ���z�����¡� �F(xi��n)�����mȻ�I(y��)�ѳɞ�����ˡ�
����Ӱӡ��ȱ��ԭ�������o(w��)�Ķ��(y��)����݆���´��������ر����С� ��Ҳ��ʲô�r(sh��)��һ�������òؕ�(sh��)����������ɽ���Ͼ��ĺ��⣬���Լ���“�x�u(m��i)��”�չ��Ļ�ؔ(c��i)�a(ch��n)���{(di��o)�飬�{(di��o)��F(tu��n)��ɢ��Ҳ�������չ�ɽ��(n��i)�����ȫ���ؕ�(sh��)���{(di��o)�顣 �����@��(g��)���֣��Ǖr(sh��)�����ԁ�(l��i)��һ��ȥ�չ���ң��c݆���µĸ�λ�Y(ji��)�������Ľ��飬����߀һֱ����(l��i)��
������(du��)���L(zh��ng)��Ҏ(gu��)��Ҳ������“��֪�Y��(ji��)”“�����ه(l��i)”“��ĘƤ”�@�ӘO�������Ե��Z(y��)�ԁ�(l��i)�����������������@��Ͳ������u(p��ng)Փ�ˡ� ��?y��n)鲻���L(zh��ng)��Ҏ(gu��)��Ҳ������ô�f(shu��)�������������������ṩ����Ƭ�ŵ����ڇ�(gu��)��(n��i)����ĸ��NС�f(shu��)��Ӱӡ����ֱ���F(xi��n)�ڶ��ڝɱ��Ŵ�С�f(shu��)����о��ߣ��@������ȻҲ�����ձ��ĝh�W(xu��)�ҡ� ���Ǜ](m��i)�����������������ܲ��ٕ�(sh��)�����F(xi��n)�ڣ��о��߂���ֻ�������d�@�� �������M(j��n)�뵽݆������醕�(sh��)�ģ��@���Ͽ���Ҳ�͛](m��i)�Ў��ˡ� �����L(zh��ng)��Ҏ(gu��)��Ҳ��������20���o(j��)60���֮ǰ���ѽ�(j��ng)���^(gu��)��݆�����u(p��ng)�ֱ�Ӱӡ��ȱ�ٵă��~������ֱ��20���o(j��)80��������R��ԫ�������ˏ�݆������Ū����(l��i)��֮�����¡� �����@�N�ر��Dz�֮��˽��ֻ���O�ٔ�(sh��)�˰���; ߀�ǹ�֮�ڱ���“���Ĺ����p�����x���c��”���@�Ͳ���Ҫ��Փ�˰ɡ�
�������f(shu��)�L(zh��ng)��Ҏ(gu��)��Ҳ����ԍ������������Ӱӡ�˕�(sh��)���sδ������ĕ�(sh��)��ٛ(z��ng)�ͽoԭ����һ�¡� �����������Ƿ��Ќ���(sh��)��ٛ(z��ng)�ͽo݆���»����Ƿ����@�ӵ���Ը�s��������һЩ�������裬�F(xi��n)���Ѳ��ɿ������������������^��(du��)����һ��(g��)��֪�Y����һ��(g��)С����ˡ� �ڬF(xi��n)������������������c�ձ���ľ����������ͨ���У��������������г����(sh��)���Լ��l(f��)�����£������]�Ľo��ľ�����������˲��õġ�ˮ�G־���u(p��ng)�֡�Ҳ�����⣺
�����g���Ì��������ČW(xu��)�������аl(f��)���°棬���Լ���ӆ���،�(xi��)“����”�������W(xu��)��(sh��)Ŀ�eҪ�ؾ������뱾�����õ����Y�ϣ��M��������N�汾ͬ�r(sh��)һ���ķ�Բ�һ�ӣ����������{(di��o)����ɢ�i����һ��(c��)����ӡ�������f(shu��)Ԓ(hu��)���ļҵķַ�����Ɲ�Ⱥ��ռķ������ �����硶�Ž�С�f(shu��)����“����”“����”�����İ��@�桷עጱ�(ע��eע���Z(y��)���Z(y��)�������ġ��hȥ���x�^(gu��)����ƪĿ)�Լ����ó���Ӱӡ�ġ�ˮ�G־���u(p��ng)��ȫ��(sh��)��(�˕�(sh��)���治�l(f��)�u(m��i))�����O(sh��)���ķ �����^(gu��)ȥ�ږ|���L��(sh��)�r(sh��)���Ĕz�ġ��Ї�(gu��)־���u(p��ng)�֡��ȕ�(sh��)�������O(sh��)��Ӱӡ��ӡ����ÿ�Nһ���ķ�һ�������g��ӡ֮��(sh��)̫�ֻ࣬��Ӌ(j��)��ӡ�У����Ԍ�(du��)�κΕ�(sh��)���e��ӡ��һ��(j��ng)ӡ�����������꣬�Еr(sh��)�B���˶�����ُ(g��u)����
����������ȫ��(gu��)������r��׃��֮����ֵ��һ�εġ� ����(l��i)�ЙC(j��)��(hu��)�r(sh��)���OԸ���������ڱ������������ؿ������_(t��i)��׃�w��r���°l(f��)�����(l��i)�ĸ��N���N�ݳ�Ҳ���Ҵ��ȸ��������m(x��)ꐡ�
�����Ĵ�ͨ������������(xi��)�o��ľ���������ĕ�(sh��)�Ł�(l��i)�������錑(xi��)��֮�˵������������������L(zh��ng)��Ҏ(gu��)��Ҳ�����������f(shu��)��“��֪�Y��(ji��)”“�����ه(l��i)”“��ĘƤ”�Ę��ӡ�
����������(n��i)�w�Ď�(k��)����ˮ�G־���u(p��ng)�֡��śr
������(n��i)�w�Ď�(k��)����ˮ�G־���u(p��ng)�֡��������������ʮ�壬��ʮ�˾���Ӌ(j��)������(c��)�� ȱ��һ�����ߣ��߾��� ��(sh��)����ȱ�~�����~���س�����r�� ���˵����~ֱ��������ʮ���~��֮���ʮ���~���������ڰ��~��ֱ����ʮ���~��������ʮ���~; ����ȱ�˵�ʮһ�~; �Ѓɂ�(g��)��ʮ; ��ʮ��ȱ����ʮһ�~�°��~; ����ʮ��ȱ�ڶ�ʮһ�~���ڶ�ʮ���~�°��~; ����ʮ��ȱ�ڶ��~; ����ʮ��ȱ�ڶ�ʮ���~�°��~���������~��ӛ�~��
�����˕�(sh��)�������ֺ�(1768—1841)�ղأ��ֺ�ԭ�������(gu��)�r�巪����ƽ���N(y��n)֮���� ��������(1793)��W(xu��)�^���ž�֮ز�������^(gu��)�^���ּң����ɞ�ڰ˴���W(xu��)�^�� ���^��W(xu��)�^���Dz�ƽ���W(xu��)��(w��n)�����L(zh��ng)�١� ��ƽ���W(xu��)��(w��n)����Ļ���Ľ����C(j��)��(g��u)����Q(ch��ng)��ƽ�Z�� ԭ�����_ɽ��1630������Ұ�̌��_(k��i)�k�ĕ�(sh��)Ժ��1690������ʥ��(���u)���ɞ��ּҵ�˽�ӡ� 1797���ֺ��δ�W(xu��)�^֮�r(sh��)�Ğ�Ļ�������W(xu��)У���Q(ch��ng)���ƽ���W(xu��)��(w��n)������ƽ���W(xu��)��(w��n)���IJؕ�(sh��)���ּ��f�؞����� ��ƽ���W(xu��)��(w��n)���IJؕ�(sh��)������Ԫ��(1867)�ɴ����ӹܣ��������ʡ����ݠ������������(1872)�����½��ڜ��u�ĕ�(sh��)���^��
������(sh��)���^���IJ�ʡ����������(1872)�����ڲ�ƽ���W(xu��)��(w��n)���fַ�Ͻ������ձ�����Ĺ����D��(sh��)�^����(sh��)���^�ؕ�(sh��)�Բ�ƽ���W(xu��)��(w��n)���ͺ͌W(xu��)�vՄ�����f�؞���A(ch��)���ټ��Ϲ���˽���Ҿ�ٛ(z��ng)�D��(sh��)�M�϶��ɡ� ��������(1874)���Uֹ��(sh��)���^���^�ᱻ���Þ�ط��ٕ�(hu��)�h��(ch��ng)����ȫ���ؕ�(sh��)�w���\�ݣ��ķQ(ch��ng)�\���Ď�(k��)������(du��)���_(k��i)�ţ�ֱ������ʮ����(1881)�����Ď�(k��)�P(gu��n)�]��14�f(w��n)��(c��)�ؕ�(sh��)��(j��ng)��(n��i)��(w��)ʡ�w��(n��i)�w�Ď�(k��)�� �˱�������Ǭ¡��ʮ����(1793)�������ʮһ��(1841)�����ֺ�֮�֣����w����(1881)����ձ���(n��i)�w�Ď�(k��)��
�����P(gu��n)�ڃ�(n��i)�w�������^Ԕ��(x��)��ӛ�Ҫ�ݵ��O��������1931�꡶�ձ��|�������B�D��(sh��)�^��Ҋ(ji��n)�Ї�(gu��)С�f(shu��)��(sh��)Ŀ��Ҫ��һ��(sh��)�� ֵ��ע����ǣ������ᵽ�˃�(n��i)�w���mȻ�F(xi��n)��IJ��ֱ��^�������ĵڰ˾����ڶ�ʮ��������ǵ�ʮ���س��� �R��ԫ����Ҳ�ᵽ���c(di��n)�����J(r��n)�飺“�˱���ʮ���س����@���Ã���ͬ�ӵı��Ӻϲ�����(l��i)�Ŝ��ɬF(xi��n)�ڵĘ��ӡ� ”
�����P(gu��n)���@��(g��)�س��ĵ�ʮ�톖(w��n)�}������Ҫ�Д�һ���@�ɂ�(g��)��ʮ���Ƿ����ͬһ�װ��ӡ� ���ɂ�(g��)��ʮ���M(j��n)�бȌ�(du��)���l(f��)�F(xi��n)�@�ɂ�(g��)��ʮ�����w���D��������һ�ӡ� ������һЩ�e�ĵط����ɂ�(g��)��ʮ��Ҳ��ȫ��ͬ�� ���@�ɂ�(g��)��ʮ������̎һЩ�~�����p�~(y��)β��һЩ�~���dž��~(y��)β���ĵ�1�~����19�~���p�~(y��)β���ĵ�20�~����24�~�dž��~(y��)β����25�~����26�~���p�~(y��)β����27�~(��ĩһ�~)���dž��~(y��)β���@ô��y�İ�����r���ɂ�(g��)��ʮ����Ȼ��ȫ��ͬ��
�������⣬�ɂ�(g��)ʮ������һЩ���@�Ĕ�塢ī����r�����6�~�¡���15�~���¡���16�~���¡���17�~�ϡ���21�~�ϡ���24�~�¡���25�~���¡���26�~���������д������@�Ĕ�塣 ��14�~��“�u(p��ng)���L(f��ng)”�u(p��ng)�Z(y��)�����Ҷ���һЩĥ�p; ��14�~��“�u(p��ng)����”��“��”������ī�c(di��n); ��23�~��“�u(p��ng)ף��”��“¾”����߅�����°롣 �@Щ�������@�Ĕ���Լ�ī���ĵط����ɂ�(g��)���Ӿ�ȻҲ����ȫ��ͬ����ô���Ժ��o(w��)�Ɇ�(w��n)���f(shu��)���@�ɂ�(g��)��ʮ���(l��i)����ͬһ�װ��ӡ�
������Ȼ֪���˃ɂ�(g��)��ʮ������(l��i)����ͬһ�װ��ӣ������Ҫ�_�����ǣ�һ����(sh��)�к����Ѓɂ�(g��)��ʮ��? ֮ǰ�f(shu��)���R��ԫ�����J(r��n)��a(ch��n)���@�N��r��ԭ�����Ãɂ�(g��)ͬ�ӵı��Ӻϲ�����(l��i)���ɬF(xi��n)�ڵĘ��ӡ� �Л](m��i)���@�N������? ��(d��ng)Ȼ���еġ� ����������@�N��r��ጵ�Ԓ(hu��)��ͬ�Ӵ��ڲ��ن�(w��n)�}��
������һ���@��ζ���F(xi��n)���(n��i)�w���������Ƀɂ�(g��)������(g��u)�ɣ�һ��(g��)�ǵڰ˾�����ʮ����������; ��һ��(g��)�ǵ�ʮ�����ڶ�ʮ�������ʮ������ �ɂ�(g��)���Ӷ��](m��i)����ǰ�߾�����ô��(hu��)����˜��ɵĚ��p��r? �ڶ�������f(shu��)�����⌢�ɂ�(g��)���p�ı���ƴ������(l��i)���ϳ�һ��(g��)�^�������ı��ӣ�����ô���ܕ�(hu��)��˴��Ĵ����ƴ��һ��(g��)��ʮ��? ���ԣ����X(ju��)�Õ�(hu��)�a(ch��n)���ɂ�(g��)��ʮ�������п��ܵ�ԭ��߀��ԭ���ı������bӆ�ĕr(sh��)����F(xi��n)�ˆ�(w��n)�}�������ڶ����һ��(g��)��ʮ����
��������݆���±��c��(n��i)�w�Ď�(k��)���Ȍ�(du��)�о�
�������ό�(du��)݆���±��̓�(n��i)�w�Ď�(k��)���ɂ�(g��)���ӵĆΪ�(d��)��r����һЩ��B������(l��i)Ҫ��(du��)�ɂ�(g��)�����M(j��n)�бȌ�(du��)�о��� ��Ҫ��Q�ɂ�(g��)��(w��n)�}�� ��һ���ɂ�(g��)�����Ƿ���ͬһ�װ���ӡ��? �����ǵ�Ԓ(hu��)���ɂ�(g��)��������Щ�ط����ڲ�ͬ���Ƿ����Єe�������l(shu��)���l(shu��)��? �ڶ����@�ɂ�(g��)�����Dz��Ǿ��������p���ÿ��̵�ԭ�������ֻ�������?
������һ��(g��)��(w��n)�}���@�ɂ�(g��)�����Ƿ�����ȫ��ͬ�İ汾������ͬһ�̰�? �ȿ�݆���±��̓�(n��i)�w���İ��档 ���ߴ���һЩ��ͬ��݆���±����Ļ�����ֻ�І��~(y��)β������(n��i)�w���t����~(y��)β�����p�~(y��)β����; ݆���±��������g�����Ͽ�“ˮ�G×��”������(n��i)�w����̳�“ˮ�G×��”����ֱ�ӿ�“×��”; ��(n��i)�w���汾���~��“��”�֣�݆���±���“һ”��; ��(n��i)�w��ijЩ�������~��(sh��)��“إ×”̎(��ʮ�������ʮ��������ʮ�˾����ڶ�ʮ�����ڶ�ʮһ�����ڶ�ʮ�������ڶ�ʮ�ľ����ڶ�ʮ���)��݆���±���“��ʮ×”; �����@��һ�c(di��n)�ǃ�(n��i)�w����ʮ�ĵ�12�~��������“�p����”��ӡӛ����݆���±��s�](m��i)�С�
�����ٿ�݆���±��̓�(n��i)�w���������c��D����ͬ�Ӵ���һЩ��ͬ�� �����ĩ����(n��i)�w����݆���±����“�������a(b��)У��ȫ�����xˮ�G־���u(p��ng)�ְ˾��K”; ����ĩ����(n��i)�w����݆���±����“�������a(b��)У��ȫ�����xˮ�G־���u(p��ng)�־ž��K”; ��ʮĩ����(n��i)�w����݆���±����“�������a(b��)У��ȫ�����xˮ�G־���u(p��ng)��ʮ���K”; ��ʮ��ĩ����(n��i)�w����݆���±����“�������a(b��)ȫ�����xˮ�G־���u(p��ng)��ʮ�����K”; ��ʮ��ĩ����(n��i)�w����݆���±����“�������a(b��)ȫ�����xˮ�G־���u(p��ng)��ʮ�˾��K”; ��ʮ�������~����(n��i)�w���в��ֲ�D��݆���±��](m��i)��; ��ʮ�������~����(n��i)�w����Dȫ��݆���±�ֻ��һ�롣
���������ϲ��ց�(l��i)�����ƺ�݆���±��c��(n��i)�w��������ȫ��ͬ�ăɷN���ӣ�����(sh��)��r������˺�(ji��n)�Ρ� �mȻ݆���±��c��(n��i)�w��������֮̎����һЩ��ͬ�����Ƕ����������Լ���D�ϻ�����ȫ��ͬ��������һЩ���ڔ���ī���ĵط���������Ȼһģһ�ӡ�
�������(n��i)�w�����˵�14�~����һ��(g��)������ī����݆���±���ī�������քt��ȱ; ���ŵ�3�~����ī������(n��i)�w���c݆���±�ͬ; ��ʮ����24�~���D���Д�壬��(n��i)�w���c݆���±�ͬ; ��ʮ���2�~�D���п�ȱ����(n��i)�w���c݆���±�ͬ; ��(n��i)�w����ʮ�˵�1�~���u(p��ng)�Z(y��)����߅���̲���ȱ�֣�݆���±�ͬȱ����հ�; ����ʮ����11�~�¡���12�~���������Д�壬��(n��i)�w���c݆���±�ͬ; ����ʮ�ĵ�22�~�������Д�壬��(n��i)�w���c݆���±�ͬ; ����ʮ���18�~���u(p��ng)�Z(y��)����ī������(n��i)�w���c݆���±�ͬ�� ��Ҋ(ji��n)�����������Լ���D��(y��ng)ԓ�dz���ͬһ�̰塣
�����������Փ�࣬����һЩ�ط����چ�(w��n)�}���ڃ�(n��i)�w�����ִ��ڔ��ĵط���݆���±����ٵط��s����õġ� ��֮ǰ��ӑՓ�ă�(n��i)�w����ʮ����֮̎����(n��i)�w�����^���@�Ĕ��ط��У���6�~�¡���15�~���¡���16�~���¡���17�~�ϡ���21�~�ϡ���24�~�¡���25�~���¡���26�~���£���23�~��“�u(p��ng)ף��”��“¾”����߅�����°룬��Ӌ(j��)13̎�� ���u(p��ng)�ֱ����ĵط��У�݆���±���15�~�¡���16�~�¡���17�~�ϣ���23�~��“�u(p��ng)ף��”��“¾”����߅�����°룬�H�Hֻ��4̎���ȃ�(n��i)�w�����˲��١�
�������һ��(l��i)����r�ͷdz���(f��)�s�ˡ� ����һЩ�ط���(n��i)�w���c݆���±������ͬ��������һЩ�ط��������s������ͬ���y��������Щ��ľ�õ�����ͬ�ģ�����һЩ��ľ�õąs������ͬ? Ҫ���_(k��i)�@��(g��)�i�}����(l��i)��һ��(n��i)�w����ʮ����һ̎��壬��̎�����_(k��i)��݆���±��ںܶ���(n��i)�w�����֮̎�s������õ����ܡ� �@һ̎����ǵ�ʮ����24�~�£���(n��i)�w��“��”“��”“��”“��”“ʮ”“��(l��i)”һ�����ֳ��F(xi��n)��壬݆���±��@�ׂ�(g��)������“��”“ʮ”“��(l��i)”�ѽ�(j��ng)����̫�����ĺ��E��“��”“��”“��”�@3��(g��)��Ҳͬ������ˣ����@3��(g��)�օs���@����Ȼ�����w�����죬�б����a(b��)�ĺ��E��
�����ľ�ʮ��24�~�µ���r��(l��i)����������Ҋ(ji��n)����һЩ��(n��i)�w������݆���±���δ���֮̎������݆���±����a(b��)���ɡ� �ٌ�(du��)�ȶ�������һЩ�ط���ͬ��Ҳ���l(f��)�F(xi��n)݆���±������@�����a(b��)���E�� ���ʮ����9�~�ϡ���10�~�¡���ʮ�ĵ�21�~�ϡ���22�~�¡���27�~�ϡ�����ʮһ��1�~�ϡ�����ʮ����4�~�ϡ�����ʮ����9�~�¡���10�~�ϡ�����ʮ�ĵ�9�~�£���(n��i)�w�����ڔ�壬��݆���±��t�����a(b��)���E��
�������Ͽ���֪������(n��i)�w����݆���±��������Լ���D�ϴ_��(sh��)����һ�װ��ӿ��̶��ɣ����Զ������S������Լ�ī��֮̎����ͬ�� ��݆���±��ڲ��ٔ��ĵط��M(j��n)����̎�������ڬF(xi��n)����Ҋ(ji��n)����݆���±�ֻ��Ӱӡ�������Բ���֪���@Щ�������a(b��)����݆���±����ղ�������߀��֮��ĕ�(sh��)�����顣 �����ղ������飬���ִ_���@�N�����ԣ���?y��n)�F(xi��n)���݆���±��д_��(sh��)���ղ��ߵĹP�E�����е�30�غ�Ļ�?c��i)?sh��)��(sh��)��“��×��”�������ղ��������� ����ˣ���ô�������a(b��)�t�����C����(n��i)�w����݆���±��Ŀ���ǰ�� �����a(b��)�����ĕ�(sh��)�����飬��ô���o(w��)�Ɇ�(w��n)݆���±��Ŀ����ڃ�(n��i)�w��֮��
������Ȼ������a(b��)֮̎�����ж���(n��i)�w���c݆���±����̵��Ⱥ���ô�Ƿ��������ĵط��܉���������ж�? ���ǿ϶��ġ� ֮ǰ�ᵽ��(n��i)�w���c݆���µIJ�֮ͬ̎����һֵ̎��ע�⣬��(n��i)�w����ʮ�ĵ�12�~�����¿���“�p����”���֣���݆���±��s�](m��i)���� ��̎�����µ�“�p����”ӡӛ�ǃ�(n��i)�w��ȫ��(sh��)Ψһһ̎ӡӛ����̎ӡӛ��(y��ng)ԓ�ǃ�(n��i)�w���������ڳ�֮�����z����(l��i)�ģ��@�ӵ���r��犲�������ˮ�G������ͬ�Ӵ��ڡ� ��݆���±��t�](m��i)���˴�̎���ģ������@�ڳ��ĸ��ӏصף��ɴ�Ҳ��Ҋ(ji��n)��(n��i)�w���Ŀ��̮�(d��ng)���u(p��ng)�ֱ�֮ǰ��
�������һ��(l��i)����(n��i)�w���c݆���±��д��ڵ�һЩ��ͬҲ���܉����ˡ� �mȻ݆���±��̓�(n��i)�w���õ���ͬһ�װ�ľ�M(j��n)�п��̣�����݆���±�����һЩ��ӆ��ͬ��Ҳ��һЩǷȱ�� �����ǰ���̎�IJ�ͬ�� ��(n��i)�w���İ��ķdz��Ļ�y��һ��֮�І��~(y��)β���p�~(y��)β��yʹ�ã��������g���“ˮ�G×��”�����“×��”; ݆���±����b�ڴˣ��t���@�N��y�İ������˽y(t��ng)һ��ȫ��(sh��)������~(y��)β���������g����“ˮ�G×��”�� �������ĩ���~�IJ�ͬ��
����݆���±���֮��(n��i)�w������ĩ���~����ȱ�˲��٣����Բ��پ픵(sh��)ĩ���](m��i)��“×××ˮ�G־���u(p��ng)��××���K”���֘ӡ� �@�N��ͬ��������?y��n)�݆���±����ð�ľ֮�r(sh��)����ĩ���~���p�^���(y��n)�أ�Ҳ�п�������?y��n)�](m��i)�Ќ�(du��)�@��ĩ���~�֟o(w��)����֮̎������ҕ������Ҳ������հס�
�������˵�һ��(g��)��(w��n)�}Ҳ�����Q�ˣ���(n��i)�w���c݆���±�����ͬһ�װ��ӿ��̶��ɣ����Ƕ����ִ���һЩ��ͬ���������ڰ���֮̎�� ���@Щ��ͬ���Կ�������(n��i)�w���Ŀ�����݆���±�֮ǰ�� ����(l��i)��Q�ڶ���(g��)��(w��n)�}���@�ɂ�(g��)�����Dz��������p���ÿ��̵�ԭ�������ֻ�������?
�����䌍(sh��)���������f(shu��)�ă�(n��i)�w����ʮ�ĵ�12�~�����´���ȫ��(sh��)Ψһһ̎“�p����”���֣���݆���±��t�o(w��)һ̎������“�p����”���֣���֪���@�ɱ������������p���������ij��̱��� ���̱��İ����·���(y��ng)ԓ������“�p����”���֣����Ǻ��(l��i)�ı��Ӳ�֪���ȫ���ڳ��ˡ� �@�N�ڳ��ֲ��ƱI����ľ�D(zhu��n)�u(m��i)�������F(xi��n)���О飬���Ǵ˃ɷN�О飬�t�϶�Ҫ���������P(gu��n)�����Լ������p���õ�ӡӛ�hȥ��
�����mȻ�F(xi��n)���(n��i)�w�����~��ĩ�~�����棬�����������p���õ�����ӡӛ������݆���±�����“ˮ�G��”����“ʿ���I(m��i)�ߣ����J(r��n)�p���Þ�ӛ”�@ôһ��Ԓ(hu��); ��һ�����}“��ԭ ؞�� �_���� ���丸���� ��W(xu��) ��ֹ ������ �ƵǸ��u(p��ng)У ��(sh��)�� ���_(t��i) ���� �Ӹ߸��a(b��)��”; ��ĩ��ӛ“�f(w��n)�v���缾����(sh��)���p���������_(t��i)��”����¶���˕�(sh��)�������p�������̵���Ϣ��
��������֮�⣬���еط����C��(n��i)�w���c݆���±����������p���������ij��̱��� �ڃ�(n��i)�w����݆���±��İ�������^λ����һЩС����Ĕ�(sh��)�֣���(n��i)�w��С����Ĕ�(sh��)���У����˵�11�~��“��”�����ŵ�9�~��“ʮ”����ʮ��3�~��“ʮһ”����ʮ��25�~��“ʮ��”����ʮ����17�~��“ʮ��”����ʮ���7�~��“ʮ��”����ʮ����1�~��“ʮ��”����ʮ�ŵ�13�~��“إ��”������ʮ��15�~��“إ��”������ʮ�ĵ�7�~��“إ��”������ʮ���7�~��“إ��”�� ��(n��i)�w�������Ĕ�(sh��)���Ǐ�“��”��“إ��”����(sh��)�ֲ����B�m(x��)����Ӌ(j��)11̎��
�����@Щ��(sh��)�ֵ�����ʲô��˼����ζ��ʲô? �䌍(sh��)�@Щ��(sh��)���������ı�����Ҳ�г��F(xi��n)�����ڄ��d�ұ���Щ�~�����^��D���(bi��o)Ŀ���҂�(c��)��ͬ�ӿ���һЩ��(sh��)�֣��@Щ��(sh��)�֏Ķ���ئ�����g��ȱ��إ����إ��֮�⣬��������B�m(x��)���g��Ĕ�(sh��)�֡� ������������(du��)�����^�Ĕ�(sh��)�ֽ�ጞ�“�@Щ��(sh��)Ŀ������ǰ�ľ����(l��i)�ѷŕr(sh��)�Ա���J(r��n)�ķ�̖(h��o)”�� �@�N�f(shu��)���Ŀ��ŶȺܸߡ� Ȼ����Փ��ô����@Щ��(sh��)�֣��@Щ��(sh��)�����_(k��i)ʼ�ĕr(sh��)��϶��Ǐ�“һ”�_(k��i)ʼ��Ȼ�����B�m(x��)�ģ����������(n��i)�w��һ�Ӕ����m(x��)�m(x��)�� ֮���Գ��F(xi��n)�@�Ӕ��m(x��)����r��������?y��n)��Ǻ�̣����Բ��ٔ?sh��)�ֶ���Ҋ(ji��n)�ˡ�
�����@�N��r����݆���±��t�������@���ڵڰ˾����ڶ�ʮ����У���(n��i)�w����11̎��(sh��)�֣���݆���±��s�H�Hֻ���ٵÿɑz��6̎��(sh��)�֣��քe�飺��ʮ��3�~��“ʮһ”����ʮ��25�~��“ʮ��”����ʮ����17�~��“ʮ��”����ʮ����1�~��“ʮ��”����ʮ�ŵ�13�~��“إ��”������ʮ���7�~��“إ��”�� ǰ�߾�H�Hֻ��һ̎��(sh��)�֞飺������13�~��“��”��
��������ǰ�����f(shu��)�ģ���?y��n)�݆���±��Ŀ���߀�ڃ�(n��i)�w��֮������݆���±��Ĕ�(sh��)��?j��n)?sh��)����֮��(n��i)�w��߀Ҫ�١� ͬ�r(sh��)����һ�c(di��n)��Ҫע����ǣ�݆���±���6̎��(sh��)��ȫ���ڃ�(n��i)�w��11̎��(sh��)�ֵĺ��w֮�С� �@�c(di��n)Ҳ�C����݆���±�����ֱ�ӳ����ڃ�(n��i)�w����������Ȼ��Ҳ����(hu��)����˵��ɺϣ���(n��i)�w������Ĕ�(sh��)�֣�݆���±�һ��(g��)Ҳ���档
���������Ŀ��Եó����½Y(ji��)Փ��(1)��(n��i)�w�Ď�(k��)���c݆���±���ͬ�棬�҃�(n��i)�w�Ď�(k��)���Ŀ��̕r(sh��)�g����݆���±�; (2)݆���±�����һЩ�ް棬ʹ�ð����Լ�����һЩС��(x��)��(ji��)̎�c��(n��i)�w�Ď�(k��)����ͬ; (3)�F(xi��n)��݆���±���һЩ���ĵط��M(j��n)�������a(b��)�������a(b��)��֪���ղ������飬߀�ǿ��̕�(sh��)������; (4)��(n��i)�w�Ď�(k��)����݆���±����������p���������ij��̱������̱��İ��đ�(y��ng)ԓ��“�p����”���֣����������ȥ��
��(zhu��n)�I(y��)�I(l��ng)���Q(ch��ng)��(zhu��n)�}
SCI�ڿ�Ŀ�
���T(m��n)�����ڿ�Ŀ�
SCIՓ��
- 2025-01-254�������(l��i)����?x��n)r(ji��)��SCI�ڿ����]��
- 2025-01-23�Ԅ�(d��ng)���c����ϵ�y(t��ng)4�^(q��)�ڿ�IMA J M
- 2025-01-23��SCI�ܸ��������Щ������
SSCIՓ��
- 2025-01-25ͨ�^(gu��)�ʸ�!���]6�����ðl(f��)��ˇ�g(sh��)SS
- 2025-01-22�Z(y��)�Ԍ�(zhu��n)�I(y��)�о����m��Ͷ�������ڿ�
- 2024-12-24�����(l��i)ssci�ڿ���ȫ����(l��i)������ss
EIՓ��
- 2025-01-24�������eiՓ��ˮƽ
- 2024-12-282024.11��EI�ڿ�Ŀ䛣�����18��
- 2024-12-262025�꼴���e�k���t(y��)�W(xu��)��(gu��)�H��(hu��)�h
SCOPUS
- 2025-01-24scopus�l(f��)�����¸�ʽ��ָ��
- 2024-11-19Scopus��䛵Ľ��������(l��i)�ڿ�
- 2024-05-29scopus�����Щ�����(l��i)�ڿ�
�ڿ�֪�R(sh��)
- 2025-01-24�ڿ��κˡ��p����ʲô��˼
- 2025-01-23���н�ͨ�l(f��)չ���P(gu��n)�����m��Ͷ����
- 2025-01-21�������w�W(xu��)�����ڿ��ϼ�
�l(f��)��ָ��(d��o)
- 2025-01-25Փ��Ͷ��ǰҪ�z����Щ��(n��i)��?
- 2025-01-24�t(y��)�W(xu��)�о����Į��I(y��)Փ���x�}�v��
- 2025-01-23�����Ļ������Փ���īI(xi��n)39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