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省級論文發表民間剪紙藝術的文化建構
時間:2016年11月03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這篇藝術省級論文發表了民間剪紙藝術的文化建構,陜北民間文化離不開農耕的社會背景,是華夏民族虔誠樸實的農耕精神文明產物,論文介紹了陜北民間剪紙的地域文化、信天游文化、巫術文化和禮祭文化,傳承和弘揚了陜北的傳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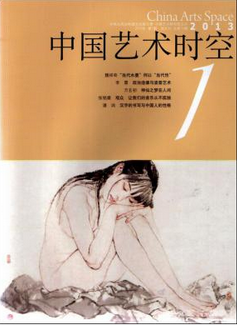
摘要:陜北地域文化形成了粗獷、淳樸的民間剪紙風格;信天游文化構成了自由、奔放的民間剪紙意境;巫術文化是陜北民間剪紙重要的文化基因;陜北民間剪紙的崇拜文化與禮祭文化是民眾的心理需求與精神信仰;祈福文化是陜北民間剪紙永恒的主題。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文化建構離不開農耕社會背景下,人們對陜北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弘揚。
關鍵詞:藝術省級論文發表,陜北民間剪紙,文化建構,地域文化,歷史文化
陜北,廣義上是指陜西省北部的高原;狹義的陜北是指“北至河套、南至渭北北山、西至子午嶺、東至黃河的黃土高原中北部地區”,[1]約為今天的榆林、延安二市,亦稱陜北地區。獨特的自然景觀與厚重的歷史文化使這里早已名揚海內外,其中,提及中國民間剪紙藝術回避不開的一派是陜北剪紙,它是中國民間剪紙藝術的發源地之一,因之受到特殊的自然環境與歷史變遷的影響,形成了具有濃郁地域風情的民間剪紙。一般而言,陜北民間剪紙是一個地域范圍的概念,它是指陜西省北部區域內榆林、延安地區的剪紙藝術,其中以安塞、洛川、延川、定邊、靖邊、綏德等縣城的剪紙為代表,而形成的風格相近的剪紙藝術即為陜北剪紙。著名民俗藝術學者張道一先生認為“民間藝術帶有‘本元文化’的特征,它是一種母體藝術”。[2]陜北民間剪紙是陜北乃至華夏民族的母體藝術之一。在其他種類的民間造型藝術中,如皮影、陶藝、布偶、泥玩、面塑等都能找到陜北剪紙紋樣的痕跡。陜北剪紙的形成是特定地域背景下,底層民眾集體創造意識的結果。它集中反映了陜北的地域、巫術、祭祀、崇拜、祈福等文化。它是底層民眾日常生產生活現狀的反映,是在陜北地域與社會背景下,華夏民族虔誠樸實的農耕精神文明的產物。
一、陜北民間剪紙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由特定區域的地理環境,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以及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主要由地理環境因素和社會人文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3]陜北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發展。法國藝術史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藝術作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的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這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4]他進而用植物存在的環境,來比喻精神文化存在的環境。精神文明的產生與動植物的存在一樣,由其自身所處的環境決定。因此,陜北民間剪紙的地域文化,也可從環境因素來分析,具體分為自然環境與歷史環境。自然環境是陜北民間剪紙形成的地域文化根基。文化生態學認為“文化根植于自然,要徹底認識文化,只有聯系其根源的自然環境。”[5]陜北民間剪紙是當地民眾千百年來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結果,它是陜北生態環境提供人文文化資源。在陜北獨特的自然環境中,一切藝術創作都帶有濃厚的陜北基因。陜北黃土高原,千姿百態的地貌,溝壑縱橫的地表,自古有“千溝萬壑”之稱。陜北夏季很少受到西南季風的影響,造成陜北高原干旱少雨的氣候。冬季內陸地區冷空氣在此集中,形成了寒冷干燥的環境。黃色是黃土高原的主要色調,長期單調的色彩,使得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偏好用艷麗的純色裝飾環境,如紅、黃、藍色成為陜北民俗活動的典型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陜北安塞、榆林的紅色剪紙。陜北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得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逐漸形成一種堅韌的地域性格,它具體表現為人們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如陜北隨處可見的窗花,它成為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視覺表現,也是陜北人民感恩黃土地的一種精神寄托。總之,陜北的自然環境造就了陜北民間剪紙淳樸粗獷的藝術造型美與艷麗的藝術色彩美。歷史環境是陜北民間剪紙的人文積淀。陜北地域文化形成于漫長的封建時代,它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原始社會至秦漢時期,是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期。[6]魏晉至宋元時期,是陜北地域文化的巔峰期。明清時期至近現代是陜北地域文化穩定期。陜北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出土了大量了玉器、陶器、青銅器等。這些出土器物的紋樣成為早期陜北民間剪紙藝術造型的源頭,剪紙貼花陶器成為這一時期典型的代表。因陜北與邊疆接壤,歷史上有狄、匈奴、鮮卑、胡、突厥、黨項、羌族、女真、蒙、滿等各民族在陜北遷徙混居,形成了多民族聚集融合的地帶。這為陜北地域粗獷、彪悍的性格形成奠定了基礎。秦漢至唐代,陜北在區位上占據了絕對優勢,因此秦漢藝術在陜北地域成為主流藝術形態。陜北民間剪紙的稚拙與粗獷沿襲了漢代畫像石的造型藝術特色,如陜北安塞縣剪紙藝術呈現出淳樸、莊重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秦漢畫像石與雕刻藝術的粗獷與恢宏。安塞剪紙藝人白鳳蘭的作品造型簡煉、概括、憨厚,她的代表作《牛耕圖》、《家禽》等,從畫像石的藝術造型中吸取營養,使得她的剪紙作品呈現出概括、憨厚的藝術風格,陜北剪紙早期多直接取材于漢代畫像石藝術題材。[7]
二、陜北民間剪紙的信天游文化
信天游是陜北民歌的一種形式,它以通俗的語言、真摯的歌詞、簡樸的曲調,從而形成了悠長高亢、蒼勁質樸的陜北高原風格。它在藝術創作手法與審美等諸多方面與陜北民間剪紙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信天游是陜北民眾在漫長的生產生活勞作中,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把生產勞作、愛情、娛樂等鮮活的生活場景,用他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娛樂化、藝術化的過程。它是陜北民眾現實生活的寫照,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愿望與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的體現。陜北民歌信天游,主要是底層勞動人民生產勞作時,即興創作的歌曲,以口頭傳唱為主要傳播方式,“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8]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的真實情感,都表現在陜北高原上飄蕩的歌聲中。這種一邊勞作,一邊即興創作的藝術創作手法,被民間藝術學者呂勝中先生稱為“信天游手法”。[9]這種手法在陜北民間剪紙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民間剪紙藝人拿起剪刀,邊剪邊唱,剪到哪一步,唱出什么詞,剪紙藝人的剪紙作品成為他們唱詞的內容。“剪與唱”融為一體成為陜北民間剪紙獨具的表演魅力。如陜北民間剪紙常見的題材《回娘家》、《過河》、《放羊》、《送水》等這些剪紙作品,都有與其相對應的陜北信天游民歌。[10]剪紙藝人自由暢快的歌聲與即興創作的剪紙作品合二為一,歌聲蕩氣回腸,剪紙畫面再現歌詞的內容,觀眾們仿佛在看一場陜北民間特色的歌劇表演。其二,陜北民間剪紙的藝術表現形式上借鑒了陜北信天游民歌的隨意性、自由性的藝術特點。這主要表現在陜北民間剪紙圖形創作方面,剪紙藝人的創意思維隨性自由,不受客觀現實制約。如陜北民間剪紙畫面中常出現雙頭驢的畫面,民間藝人解釋為“驢吃草的時候,它的頭是在不停的動,一會左邊,一會右邊的移動”,這種兩只頭的驢,是剪紙藝人想在平面的剪紙上表現一個動態的過程。陜北民間剪紙的自由性還表現在他們在剪紙藝術中常用一種無阻礙的空間思維,如安塞縣白鳳蘭的剪紙作品《耕牛圖》,她為了表現牛與背景的關系,就把背景的山村也剪出來,這樣鏤空的牛肚中就呈現出山村的畫面。這種直來直去的空間思維是陜北地域勞動人民不拘小節的地域性格的反映,它也是陜北信天游直抒胸臆的暢快表達。陜北信天游的這種自由與即興的表演,源于陜北多民族融合背景下民眾廣闊的胸懷。陜北民間剪紙藝術樸實無華的造型、特立獨行的藝術風格,都是人類“本源文化”的體現。[11]它包含了一種原始藝術精神,也是陜北自然環境和生活環境最本真的體現。
三、陜北民間剪紙的巫術文化
從甲骨文時代的占卜術開始,巫術活動一直與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遠古社會的巫覡活動,有它的歷史價值,它孕育了我們民族文化的許多方面的萌芽,孕育了人類社會最早的知識分子階層”。[12]巫術在農耕文明中長期發揮著重要作用,它是民間剪紙發展至今的一個重要的內在驅動力。它至今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為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潛在的優勢。巫術是人類遠古時代思想文化的產物,它常常成為統治者壓迫底層民眾的工具。它在漫長封建時代點燃了人類文明的星星之火,在封建社會成熟及以后的大多數時期,巫術文化具有很大的消極作用。但不能因噎廢食,就徹底否認巫術在人類文明起源階段所作出的貢獻。巫術之于中國的傳統醫術,巫術之于中國傳統的藝術、各種工藝技術等生產生活的各方面,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古代巫術活動是在人類文明尚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借助一種超越現實的觀念,為克服現實生活的困境,而產生的生產活或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對健康的體魄、富足、平安生活的追求。陜北民間剪紙的巫術文化歷史悠久,剪紙與巫術是一對不謀而合的冤家。巫術作為剪紙的形成思想,剪紙作為巫術的外在表現形式,長期存在于廣大民眾的生產生活之中。唐代詩人杜甫恰逢安史之亂,行至陜北洛川與白水的交界的彭衙時,作詩《彭衙行》“暖水濯我足,剪紙招我魂”的詩句,可見自唐代就有使用剪紙招魂的民間習俗,詩中所描述的“剪紙招魂”習俗是一種民間巫術活動,陜北地區至今流傳著使用抓髻娃娃剪紙叫魂的習俗。[13]民眾將紅色的抓髻娃娃與紙錢一起在離家不遠的十字路口焚燒,燒紙的人要面向北方,以祈求抓髻娃娃喚回病者的魂魄;這是陜北民間剪紙的巫術民俗活動。陜北民間剪紙的抓髻娃娃種類千姿百態,可分為治病、除惡、招魂、避邪、護生、驅鬼、鎮宅、祈雨等各種類型。陜北各地根據需要制作各種巫術類型的抓髻娃娃剪紙。如陜北民間流行的剪紙作品《母嬰抓髻娃娃》,就是貼在孕婦的產房內,以祈求順利生產,它是母子平安的護身符。總之,巫術文化是陜北民眾在人類文明萌芽時期的一種實用主義的生存智慧。它在遠古時代既滿足了陜北民眾生活需要,也滿足了人們的心理平衡。[14]它是陜北民間剪紙藝術重要的文化內涵之一。
四、陜北民間剪紙的禮祭文化
禮是按照儀式行動的意思,禮字本意是一種祭器;禮祭活動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種歷史傳統,它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鄉土社會從上至下都十分重視禮祭活動,民間剪紙藝術只是禮祭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之一。1959年10月,新疆吐魯番縣火焰山公社阿斯塔那村考古出土了北朝剪紙《蓮花團》、《對鹿》、《對猴》等一共七件,這些剪紙是墓主人的隨葬品,可見剪紙在南北朝時期已經作為一種祭祀用品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15]禮祭是民眾的一種精神創造,陜北民間剪紙作為一種工藝只是這種精神創造的附屬產物。因為禮祭活動的需要,民間剪紙藝術才得以長久發展。這是人類精神活動需要反作用于藝術形態的結果。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禮祭文化,主要是指陜北的送葬習俗,孝子孫們麻戴孝,手持引路幡,眾親人們邊走邊撒各種形狀的紙錢;這種紙錢與引路幡都是陜北民間剪紙的一種常見的表現形式。祭祀剪紙是陜北民間剪紙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人去世出殯直至滿五個星期俗稱“五七”,滿七個星期俗稱“七七”等這些重要的日子都有相關的祭祀活動,所用到的各色剪紙紋樣、花圈、仙鶴、金銀山、聚寶盆等祭祀裝飾品,都是陜北民間剪紙禮祭文化的表現。另一種大型禮祭活動是陜北地區流行的各具特色廟會,廟會活動重要的衍生品是各種形式的剪紙作為祭祀文化的用品,如陜北民間剪紙藝人胡鳳蓮,她的剪紙作品常常使用抽象的紋飾,剪紙圖案來源于仰韶文化與廟底溝文化的陶器紋樣,給人一種古樸神秘的感覺。各類剪紙面具、剪紙花樣裝飾廟堂,使得活動氣氛嚴肅而神秘。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為地域的禮祭活動增添嚴肅靜穆的神秘感,禮祭文化為陜北民間剪紙的傳承發展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樣式。
五、陜北民間剪紙的崇拜文化
陜北民間剪紙的崇拜文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圖騰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圖騰是遠古先民對部族歸屬感的一種文化記憶形式,龍鳳是華夏民族共同的圖騰,各部族都也有自己的圖騰,如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被譽為古蜀人的圖騰。與陜北地域相關的圖騰文化主要來自于仰韶文化與廟底溝文化的人面魚身圖案,如安塞剪紙藝人胡鳳蓮剪紙《雞捉魚》是對民間流傳的漢代畫像石造型的摹仿,也體現了陜北地域對鳥圖騰文化的崇拜。生殖崇拜源于遠古社會先民們對人類生殖繁衍的崇拜與敬重。生產力低下的農耕社會,人成為核心的生產力,所以歷朝歷代都祈求人丁興旺。此外,在禮治中國的鄉土社會,將無子嗣視為最大的不孝,這種傳統的習俗與道德標準,讓人類的生殖活動成為更加神圣的行為,反映在陜北民眾的生產生活中,人們延續了鄉土社會對生殖繁衍文化的樸素認知。如陜北常見的剪紙《魚戲蓮》、《魚鉆蓮》等,魚代表男性,蓮代表女性,蓮又表示連(蓮)生貴子等寓意。諸如此類的剪紙還有《娃娃戲葫蘆》、《老鼠吃葡萄》、《抓髻娃娃》等,陜北剪紙元素中的“娃”同“蛙”,常見到人形的蛙狀的剪紙圖形,“蛙”字又與“媧”諧音。趙國華先生認為:“女媧本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發展為女性的象征,爾后再演為生殖女神”。[16]陜北民間剪紙中出現娃或蛙的形象,其實質意義是對生殖文化的崇拜。《扣碗》剪紙也是陜北民間常見的形式之一,這類剪紙主要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以陰陽結合的圖形來寓意男女結合,借以表達生殖崇拜。剪紙藝人主要運用隱喻的手法表達勞動人民祈求多子多福的愿望。陜北民間剪紙的自然崇拜文化,主要是指農耕社會背景下,人對自然現象的不解與困惑,產生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慌與不安,它反映在民眾的生產生活中,就表現為對自然現象的崇拜與迷信。如封建時代人們覺得天有天神、月有月神、山有山神、河海有河神、海神,世間萬物不能解釋的都被稱為神,這就產生了人類對大自然奇異現象的不解與崇拜。陜北民間剪紙中諸如這類題材有《山神救母》、《敬河神》等,前者講的是山神在荒野救了走失的老母的傳說,教導人們要行善積德;后者是為了救治泛濫的黃河水,要在每年固定的時期祭拜河神。黑格爾指出“藝術的起源與宗教關系最密切,最早的藝術作品都屬于神話的一類”。[17]陜北流行的民間故事與神話傳說成為陜北民間剪紙常見的題材與形式。
六、陜北民間剪紙的祈福文化
陜北民間剪紙的祈福文化,是民間剪紙寓意的核心文化。近現代以來,遠古的生殖崇拜、圖騰崇拜等文化影響逐漸隱退。人們追求合家平安、幸福吉祥、多子多福、長壽消災、安居樂業的意味逐漸加強。陜北民間剪紙的這種祈福文化的根源是民眾在面對疾病、災害、戰爭等威脅時,他們所表現出的一種本能生存意念的表達,即“功利先與審美,審美源于功利”,他們用剪紙表達對平安、長壽的祈愿,是發自內心的功用,并非文化娛樂。[18]隨著封建農耕社會的瓦解,陜北民間剪紙也變的越來越趨于實用化、具體化,再加之老一輩剪紙藝人相繼去世,陜北民間剪紙所能傳承下來的就是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的類型。隨著科技與文化知識的普及,民間剪紙的受眾群體越來越小,他們的接受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剪紙創作的內容與形式。當今祈福類陜北民間剪紙僅僅是為了一種文化娛樂與審美之需要。每年農歷三月十八日,陜北綏德縣定仙墕鎮娘娘廟會上所供奉的送子娘娘、奶母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和痘神娘娘、糠神娘娘等七位神仙,來拜廟會的人大多想求取子嗣,人丁興旺,子孫平安的。在廟會的儀式上,秧歌隊的頭傘先唱詞,眾信徒跪拜。秧歌所用的花傘、紙幡與花樹等都是陜北民間剪紙的衍生物,演出隊員所穿的服裝也附加有剪紙的裝飾物。陜北地域廣,各地都有自己的廟會活動,秧歌、社火等民俗活動是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為這些活動特意制作的剪紙,大多被賦予了一種祈福功能。陜北地域的祈福類剪紙除了各地的廟會活動之外,世俗的結婚、生子、喪葬等習俗剪紙一直是陜北各地民間剪紙的常態,這些類型的剪紙最重要的文化寓意就是祈福納祥、安居樂業。陜北民間剪紙創作本身就是民眾的一種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承載著樸素的生活功能。這種功能體現在陜北勞動人民賦予陜北剪紙的一種祈福的儀式上。以上論述了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基本文化構成,它們形成了陜北民間剪紙寶貴的文化資源,是理解與傳承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核心組成部分。陜北得天獨厚的地域文化奠定了陜北民間剪紙的藝術風格,它是陜北地域生態文化的結果。陜北的信天游民歌文化形成了闊達自由、豪爽奔放的陜北民間剪紙藝術風骨精神。巫術文化構成了陜北民間剪紙藝術形成的淵源,它提供了豐富的民間剪紙的內容,它是陜北民間剪紙傳承至今的重要文化基因。禮祭文化與崇拜文化是陜北地域先民在生產生活中所必需的心理與精神信仰,它為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傳承發展奠定了心理接受空間。祈福納祥文化則是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發展傳承永恒的主題。總之,陜北民間剪紙藝術在中國鄉土社會文化背景下生根發芽,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說“文化本來就是傳統,無論哪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環境里,個人可以相信自己的經驗也可以相信祖輩的經驗”。[19]陜北民間剪紙是陜北世代民眾集體意識的結晶,這種集體意識形成于“共同接受了傳統,這是祖先精神的化育”,更是鄉土社會生活環境中民俗鄉情千百年浸潤與潛移默化的結果。[20]這使得民眾的個體意識逐漸融化在強大的集體意識中。鄉土社會的這種集體意識形成了陜北民間剪紙藝術的文化根基。它正是陜北民間剪紙的地域文化、信天游文化、崇拜文化、禮祭文化、巫術等文化的融合。
作者:熊輝 單位:皖西學院 文化與傳媒學院
推薦期刊:中國藝術時空 (雙月刊)創刊于2011年7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管,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以繁榮中國當代文藝為目的,以文化創新為重點的國家藝術類專業期刊。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