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論變革及反思
時間:2019年08月19日 分類:電子論文 次數:
[摘要]人工智能的影響終究在于人自身,在馬克思的存在論視閾下對之加以研究尤為必要。以“存在”維度觀察,人工智能雖發端和借由人類智能來實現,卻以異質的“自為存在”獲得了新的“類存在物”資格。人工智能崛起在人之身體存在、關系存在、實踐存在和生活存在等層面掀發了一場深刻的存在論變革,同時也為人類社會帶來以勞動無用化、自由新異化、隱私牟利化、存在終結化等為關鍵表征的“存在隱憂”。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規范和構建一種符合人類長遠利益的“存在理性”,即立法意義上的“人類智能的自限”和“資本的他限”。
[關鍵詞]人工智能;人類智能;存在論;變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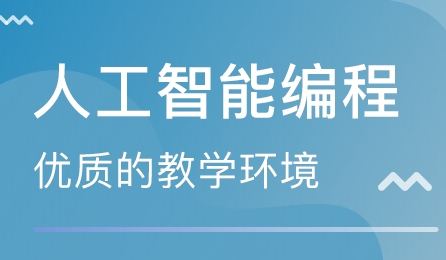
人工智能是近年來國內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最具時代性與現實性的焦點話題之一。人工智能的影響終究在于人自身,因而很多學術討論其實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了人工智能對人之影響。從存在論的哲學視域看,這些影響的關鍵效力集中在人工智能所引發的人類社會自身的存在論變革。而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論變革中,也潛藏著悖論性的張力沖突,帶給當代人揮之不去的集體焦慮與“存在隱憂”。基于馬克思面向“現實的個人”的存在論思想對這些問題進行充分考察和深度反思,對于推進人工智能哲學研究和應對人工智能的風險挑戰都尤為必要。
一、人工智能:一種比照于人類智能的“類存在”理解
在存在論的語境下,首先我們需要厘清,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存在,“是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技術科學”[1]。就其科學技術的實質而言,人工智能屬于軟件和程序,是被設計成能夠根據情況調整并作出細致行為的程序[2]。人工智能以何種形態存在?因提出“中文屋”思維實驗而聞名的哲學家J·R·塞爾曾在《心靈、大腦與程序》一文中,審慎地將人工智能分為此后在學界廣為沿用的弱人工智能(弱AI)和強人工智能(強AI)兩種類型[3]。
弱人工智能乃是這樣一種存在:它完全沒有意識、只能依從程序設定而在某個特定領域單一地執行某項任務,這類人工智能形態本質上仍屬于“工具”的存在范疇。例如人臉識別、圖像識別、語音翻譯、醫療診斷等,就只屬于智能維度單一的弱人工智能之列。強人工智能的存在,通常被描述為如人們想象中的高級機器人那樣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和心智,且智能維度豐富而接近人類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形態。
在強人工智能的基礎上,牛津大學教授尼克·波斯特洛姆又提出一個智能水平更高的“超級人工智能”概念,用以指稱“在幾乎所有領域遠遠超過人類的認知能力”[4]的人工智能存在形態。然而,上述關于人工智能之存在的一般性描述顯然還無法抵達哲學應有的深度。事實上,無論是在認知科學還是在哲學人類學上談論人工智能的存在,都不可能不聯系“人工智能何以能存在”的源頭——人類智能。
只有將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兩種“類存在”進行合乎現代科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比照,才能更清楚地澄明人工智能的哲學定位與“存在”所是。在此,我們切入分析的立腳點,是馬克思存在論哲學中從費爾巴哈那里借鑒過來但又作了創造性轉換的“類存在”概念。有學者指出,“‘類存在’這一概念所指是具有某種普遍的、共同的根本性特質的存在物”[5]。
從這一角度看,人類智能就是一種人類身上所共有的、可以單獨加以考察的“類存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指出:“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做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
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6]盡管馬克思在此并未使用“智能”概念,但其論述卻無意中對人類智能的“類存在”及高明之處作了精辟的剖析。
如果說動物的類智能是片面的、粗陋的,那么人類智能作為地球上迄今為止產生的最高形式的自然智能,它的“類存在”則表現出了不可思議的全面性和高度自由自覺的創造性,包含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理性”“想象力”和改造對象世界的智識能力。
更不可思議的是,人類智能作為人的類特性和能力,作為人身上積極彰顯著的本質力量的核心部分,又按照自己的“形象”與“智能”創造了異質的“類存在”——人工智能,由此構造了一幅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交相輝映的圖景。人工智能既出自于人類智能,就必然與人類智能有很緊密的存在論關聯。
一方面,人工智能之“存在”依賴和借由人類智能來實現,人類智能是人工智能形成與確證自身的模擬對象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人類智能之“存在”又通過人工智能得以加固和外向拓展。或者說,人工智能是人類智能的“對象化”和積極的“自我復現”與“生命延續”。但人工智能作為“其他物的類”與人類智能作為“自身的類”畢竟是有本質性區別的。
第一,從智能的起源講,人工智能是人類設計出來的無機的、非自然的智能,而人類智能是生物長期進化過程中天然生成的有機的、自然的智能;第二,從智能的內在結構來講,人工智能的運行載體是金屬和硅,而人類智能的運行載體是屬于生命肉體的人類大腦,前者是“物在”的智能,后者是“人在”的智能;第三,從智能的功能來講,目前的人工智能只能實現人類智能的部分模擬和延展,其智能的功能維度是單一而有限的,而人類智能則具有高度的自由靈活性和功能多元性。
正因為現階段的人工智能還只能實現對人類智能的部分模擬,近些年來名震一時的無人駕駛汽車、阿爾法狗(AlphaGo)系列軟件也只能歸為弱人工智能。可以說,對人類智能模擬與延展的程度和范圍,構成了人工智能發展的實際限制。
然而正如西方神話中上帝創造人類而賦予“被造物”獨立的主體地位,人工智能在“類主體”的意義上也已是現實的“自為存在”,換言之,人工智能作為人類智能的對象化和虛擬進化,在其不斷向前演進的過程中以異質的肯定方式獲得了新的“類存在物”資格。這種“類存在物”的本體雖是智能機器,卻有其獨立的“類本質”和獨特的“類本質力量”,甚至能部分地超越人類智能。
也許更為影響深遠的是,人工智能的產生是地球智能進化的分水嶺和影響深遠的轉折性事件,它呈現了區別于地球“碳基”生物智能進化的“硅基”非生物智能進化方式,或者說代表了地球未曾有過的全新的智能進化方向。而人類社會,因為當初規定和籌劃的人工智能的存在性介入而開啟了新的文明類型,也不可避免地踏入了新的充滿矛盾和挑戰的存在之途。
二、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論變革
人所共知,真正深具劃時代影響的科學技術必能引起全方位的社會變革效應,而人工智能恰被實踐證明是這樣一門科學技術。揆諸當下,日益廣泛而深度地滲入到人類生產生活各層次領域的人工智能技術,正悄然引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關于“現實的個人”和人類社會自身的存在論變革。人工智能之于人的這場存在論變革,可透過以下幾個方面被關鍵性地揭示和闡釋出來。
(一)身體的非自然化與人之生命存在的超人類變革
馬克思的人學存在論思想清楚地揭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7]。人之存在首先是自然性的生命存在,而人的生命存在無疑又留居在人的身體之中,或者說人的生命存在與身體直接同一,是通過有肉體組織的身體來流動和展現出來的。在此意義上,人類向來是身體的存在者,沒有身體就無所謂人的生命存在。人作為生命存在定向性質的身體的最大特性在于其自然性。
如果聯系人類智能來講,那么不僅人類有生命的肉體組織是自然形成的,就是人類大腦的智能屬性如天賦和才能等也是類猿人長期進化和基因遺傳的自然結果,所以自文明史以來,人類普遍習慣于接受并順應由自然賦予的包括外貌、體型、心理和智能因素在內的身體生命的自然特質。在過去,違反或更改身體的自然生命特質幾乎等同于觸犯人類的禁忌。然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先是生物工程,后又加上人工智能,卻使人類基因預先規定的自然身體日益受到非自然的深刻沖擊。
人工智能技術目前在仿真機器人、半機械人工程、人體芯片等黑科技領域有一定進展和部分應用[8]。芯片植入人體、智能機器與人走向“合體”從而“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馬克思語),表明人部分修改自然肉體生命形式的能力在不斷增強。埃隆·馬斯克便在尼采“超人”的意義上拋出驚人之語:“未來人類需要與機器合體成‘賽博格’,才能避免被人工智能淘汰。過一段時間我們可能會見證生物智能和數字智能更緊密的結合。”[9]
而另一方面,一些超人類主義者如遺傳學家喬治·馬丁、古生物學家格雷戈里·保羅、數學家厄爾·考克斯、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則推崇一種“無身體”的生命存在,認為未來超級智能機器將幫助人類完成“意識上傳”,以超越生命極限,實現脫離身體的“自我”不朽和人類的數字化永生[10]。
無論是科幻般的“人機混合體”還是聽起來荒誕不經的“數字化永生”,其背后都是對人類身體狀態乃至人類定義的顛覆性思考,是一種基于對人工智能過度崇拜而產生的新的存在論哲學,這種存在論哲學表面上提倡人類肉身的“去遠”和生命存在的“虛擬再現”,實則照面出來的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反自然之道而行”[11]。
雖說人的身體和人性在實踐、歷史與文化的敞開境域中從來都不是給定的而是不斷演化的,因而人的存在方式仍是尚待生成和建構的產物,但超人類主義者們有意按照他們的科技烏托邦想象打造出超越自然進化秩序的全新人類進化樣態和后人類物種的價值取向,卻使人類熟悉的身體觀,以及一直以來穩固的“人何以為人”的最為始源和根本的天性部分被徹底擊中。借用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的說法,技術座架“真正的威脅已經在人類的本質處觸動了人類”[12]。
(二)智能機器的介入與人之關系存在的機器轉向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所以在關系性的現實觀中,人的存在始終是一種關系性存在。“人建立何種關系”“人怎樣處理關系”以及“人作為關系存在的具體形態”歸根結底是生產方式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
起初,人無論是與自然的關系還是與他人的一切社會關系,都是直接照面或者借助于簡單的工具來進行的,而當近代工業社會把蒸汽機、機械化勞動工具、火車、電報、電話等機器生產出來,并使機器在生產關系、政治關系和人際交往關系中發揮物質中介作用之后,人的關系存在從此便與機器聯系在一起,就連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階級斗爭關系,也有機器取代勞動的直接緣起。
三、變革中的焦慮:人之“存在隱憂”
由上可知,人工智能的時代帷幕已拉開,并開始深層次地重塑人類社會與人自身。但辯證地看,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論變革顯然并非只有正面效應,其負面效應也深潛在人類社會的日常生活結構之中,這深刻表現為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令人焦慮的“存在隱憂”。
四、總結與思考
關注人工智能就是關注人類未來。人類智能將最接近自身的人工智能這一“類存在物”創造出來,便注定將人類的根本前途和命運推入一個新的充滿變革、挑戰和不確定性的存在論場域當中。從現實和長遠趨勢來看,人類不管如何質疑人工智能,都已無法阻擋人工智能的前進步伐,這在根本上是不以部分人“唯心”的意志為轉移的,原因正如唯物史觀所以為的,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非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社會存在中的生產力要素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需要人工智能這種先進的物質生產力來推動人類社會邁向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級的文明社會形態。
在可展望的技術維度,人工智能甚至是在為未來必然高度智能化的共產主義社會奠定物質基礎。所以,不能因為人工智能的負面效應而否定人工智能的存在價值,無視人工智能難以阻擋的發展態勢。但同時,也不能因為人工智能的積極影響而忽略人工智能之于人類的風險與“存在隱憂”。當務之急,是正視目前某些顯現的“存在隱憂”,并尋求符合人類根本和長遠利益的解決之道。這里的“解決之道”并不只是就具體的技術性方案而言的,也包括深層次的哲學世界觀與“存在理性”。
限于篇幅,我們無法對此處的“存在理性”展開具體闡析,但可以明確的是:這種“存在理性”所要應對的問題癥結,是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的內在張力以及人類生存與資本邏輯直接的矛盾關系,而求解的方案,則是立法意義上具有原則高度與思想延伸價值的“人類智能的自限”和“資本的他限”。人工智能風險的規避之路終歸要回到人類智能本身。
人類智能的偉大并不僅僅在于其絕妙的構造和接近無限的智能潛力,更在于其懂得自我去“惡”、自我凈化、自我馴化的“自限”能力。所謂“人類智能的自限”,就是指要在人工智能的技術源頭有選擇地開啟對人類智能的“自限模式”,避免人類對人工智能的惡意開發和非法使用而可能造成的“創造性毀滅”。
所謂“資本的他限”,則意在表達人工智能“不作惡”的前提是人類智能“不作惡”,而這在現實性上又結構性地依賴于“資本不作惡”;由于資本根本上無法“自限”,所以是在“外部”通過高揚資本邏輯的否定性力量——勞動邏輯,以及制定良好的法律、制度、倫理規則來制衡和監督“資本”,使資本無法在人工智能領域任意橫行。唯有規范和建構這樣的“存在理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實現人工智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進而紓解乃至消除人工智能之于人類的“存在隱憂”。
[參考文獻]
[1]蔡恒進,等.機器崛起前傳:自我意識與人類智慧的開端[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207.
[2]松尾豐,鹽野誠.大智能時代:智能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經濟、社會與生活[M].陸貝旎,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XVII.
[3]瑪格麗特·A·博登編.人工智能哲學[M].劉西瑞,王漢琦,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73.
[4]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級智能:路線圖、危險性與應對策略[M].張體偉,張玉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
[5]賀來.馬克思哲學的“類”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J].哲學研究,2016(8).
[6][7][13][14][18][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209,501,501,500.
[8][23][24]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9-40,293,294.
[9]王麟.“賽博格”從科幻走進現實[N].北京日報,2017-03-08.
人工智能方向評職知識:人工智能應用論文投稿哪類期刊
《計算機與數字工程》(月刊)創刊于1973年,由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七○九研究所主辦。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指定參加全國優秀期刊展覽。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堅持以應用為主,提高與普及并重;堅持創新,堅持以刊登國內外計算機方面的新理論、新技術、新工藝、新成果研究為主;以學術性、技術性為辦刊特色,論文以中短專文為主;力求更快地為讀者提供更多的有益的信息。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