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類論文發表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度量體系構建與實證
時間:2016年03月18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這篇金融類論文發表了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度量體系構建與實證,農村金融還沒有專門的探討,探討農村金融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論文分析了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復合度量體系并進行了實證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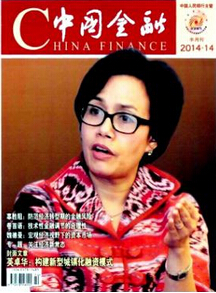
關鍵詞:金融類論文發表,農村金融發展
一、引言
關于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方法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文獻進行探討,現有的研究散見于關于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相關關系的文獻中。徐笑波和鄧英陶(1994)利用1979―1990 年的統計數據,用農村金融相關率來反映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在數值上等于“行社存款”與“農村國民收入”之比。張兵等(2002)對徐笑波和鄧英陶的指標進行了修正,用“農戶存款”“農業存款”與“農戶手持現金”三者之和作為“農村金融資產”數據,同時以“農業GDP”代替“農村國民收入”計算農村金融相關率。宋宏謀(2003)運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所提出的金融相關率指標,采用1979―2000 年中國農村金融數據構建了反映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指標。姚耀軍(2004)利用“農村貸款余額”與“農村GDP”之比來衡量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程度,其中“農村貸款余額”由“鄉鎮企業貸款”與“農業貸款余額”構成。陳文俊(2011)用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來反映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其中,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用“農村存款余額”和“農村貸款余額”之和與農業GDP之比來反映,農村金融發展效率用“農村貸款額”與“農村存款余額”之比表示。姚星垣和夏慧(2012)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現金收入”減去“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支出”再除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現金收入”來反映農村金融發展水平。
以上文獻的度量方法雖然有差異,但基本上是根據“農村存款”“農村貸款”“農業GDP”“農村GDP”等幾個指標進行運算,進而得到相應的度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農村金融資源“嫌貧愛富”的本性逐漸曝露,不少農村金融機構事實上成為了農村金融資源的抽水機,將農村存款大量轉移到城市。因此“農村存款”的多寡已不能反映農村金融發展的真實水平。同時,“農業GDP”與“農村GDP”的差異很大,用“農業GDP”代替“農村GDP”存在很大的偏差。因此,用“農村貸款余額”與“農村GDP”之比反映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相對可取。但在中國的統計系統中,“農村貸款余額”和“農村GDP”都沒有直接對應的統計指標。不少學者用“鄉鎮企業貸款”與“農業貸款余額”之和來表示“農村貸款余額”,但這一口徑并不能完全反映農村貸款的真實水平。另外,隨著鄉鎮企業的沒落,目前對“鄉鎮企業貸款”指標也無法正常統計。而對于“農村GDP”,大多采用估算的方法,但這一估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有些數據不但不容易獲得,而且也難以進行準確統計,其估計結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即使數據不存在問題,現有度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方法也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缺陷:一是現有度量方法無法體現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中數量最大的經濟主體“農戶”和直接生產者“農民”的金融支持情況。農村金融如果不能有效滲透到“農戶”和“農民”層面,可以說農村金融就沒有“生根”,則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必然處于落后的狀態。二是現有度量方法無法體現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農業”的金融支持情況。農村金融如果不能對農業進行有效的金融支持,農村貸款必然出現異化,則會犯方向性的錯誤。三是現有度量方法無法反映農村金融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農村金融往往具有一定政策性質,有些地方雖然貸款增長幅度大,但隨之而來的不良貸款余額也可能大幅度攀升,貸款質量下降,農村金融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四是現有度量方法沒有考慮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農村金融的需求特征。比如第一產業占比依然很大的省份和第一產業占比比較小的省份對農村金融的需求存在較大的差異。由于農村金融含有一定的政策性,農業大省的政策性貸款可能相對較多。因此,采用一刀切的度量指標來度量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存在不科學性。有鑒于此,本文將基于農村金融的功能構建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復合度量體系,并對我國各省區進行實證分析,進而提出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發展與改革的建議,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為有關研究提供方法借鑒,同時也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實踐提供經驗參考和政策依據。
二、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復合度量體系:“三位一體”“5指標+1因子” 付園元,李 敬,付陳梅,劉 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度量體系構建與實證分析本文從農村金融高效、可持續地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功能出發,綜合考慮農村金融發展的滲透度、方向性和可持續性,建立“三位一體”“5指標+1因子”的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度量體系。根據中國農村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實際,如果一個地區農村金融發達,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高,應當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滲透度高,滿足“農戶”和“農民”金融需求的能力強;二是方向合理,貸款方向符合最大化農村金融功能的要求,滿足“農業”金融需求的能力強,滿足農村小企業融資能力強;三是可持續發展能力強,貸款質量高,不良資產少。根據農村經濟金融的現實情況,農村金融的滲透度可用農民人均貸款與地區人均貸款之比Ffarmer和獲得貸款農戶數占總農戶的比例Fhousehold兩個指標來反映;農村金融的方向性可用農業貸款與農業GDP之比Fagriculture和農民人均小企業貸款與地區人均貸款之比FBusiness來反映;可持續發展能力和貸款質量可用良好貸款比例Fgood lending反映。因此,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度量體系可表示為圖1。 考慮不同地區農業發展情況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農村金融的需求有差異,同時考慮到農業大省可能存在的更多的政策性金融,在以上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需要加一個校正因子。由于這些政策因素和需求差異因素與農業在地區經濟中的份額正相關,因此校正因子是農業增加值和地區生產總值之比Ragr的函數。綜合考慮以上因素,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公式可表示為:
三、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實證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游波,2011)。第一階段(1979―1984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形成了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制;第二階段(1985―1996年)是農村金融體制的發展與定位階段;第三階段(1997―2005年)是農村金融體制重新定位階段,中央對農村金融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隨著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退出以及對非正規金融的整頓,農村信用社成為農村金融的主力軍;第四階段(2006年至今)是農村金融體制逐步開放階段,改革的方向是:加快建立健全農村金融體系,推進農村金融組織創新,適度調整和放寬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鼓勵和支持發展適合農村需求特點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下面對2006年以來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會網站《中國銀行業農村金融服務分布圖集》,由于目前公布的最新數據為2010年數據,因此本實證研究的時間區間為2006―2010年。
1.中國農村金融運行的總體情況
隨著農村金融改革的深度推進,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不斷提高。2006―2010年,全部農村金融機構農業貸款的增長速度超過同期銀行總貸款增長速度的1倍;2010年末,農業貸款余額達727 316 366萬元,在2006年的基礎上增長了2.57倍,年均增長29.01%;而同期銀行總貸款僅增長了1倍,年均僅增長14.92%。農民人均農業貸款由2006年的2 303元增長到2010年的8 861元,增長了2.85倍,年均增長30.93%。2010年末,農戶貸款余額達23 989 1691萬元,在2006年的基礎上增長了1.36倍,年均增長18.76%;農戶戶均貸款由2006年的4 281元,增長到2010年的10 142元,增長了1.37倍,年均增長18.83%。2010年末,農村小企業貸款余額達263 529 401萬元,在2006年的基礎上增長了35%,年均增長6.16%;農民人均小企業貸款由2006年的2 212元增長到2010年的3 211元,增長了45%,年均增長7.74%。與此同時,不良貸款率持續下降,2006年良好貸款率為90%,2010年達到97%;不良貸款余額下降了41%,年均下降10%。但不容忽視的是,普通農戶享受金融服務依然存在較大的障礙。2010年末,獲得貸款的農戶數為69 257 121戶,在2006年的基礎上減少了25%;獲得貸款的農戶比例由2006年的37%降至2010年的29%。在農村貸款規模大幅增長的情況下,獲得貸款的農戶比例卻在下降,說明農村貸款的集中度進一步提高,農村金融“嫌貧愛富”的狀況依然在加劇。
2.中國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 運用“三位一體”“5指標+1因子”的度量體系對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需要三個步驟:一是5個分項指標的權重確定,二是校正因子的估算,三是綜合得分的計算。
(1)指標權重的確定
常見的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是專家評分法,但專家評分法具有明顯的主觀性。本研究采用一種客觀的數據挖掘技術――粗糙集(Rough Set)來確定權重。粗糙集方法的主要特點是不需提供問題所
需處理的數據集合之外的任何先驗信息,僅根據觀測數據生成分類或決策規則(Pawlalz,1998;鐘波,肖智,2002)。首先根據圖1所列指標,將每個分項指標的數據進行離散化處理,對每個分項指標的值按優、良、中、差分成4等,并分別賦值為4、3、2、1。對于獲得貸款農戶比例指根據農戶的貸款需求確定等級:參考王雅君(2010)的調查研究,實際有貸款需求的農戶比例平均約75%,因此將獲得貸款農戶比例達到70%以上定為優,45%~70%定為良,20%~45%定為中,低于20%定為差。依據銀行風險控制規范,將良好貸款率在90%以下定為差,90%~94%定為中,94%~97%定為良,高于97%定為優。對于其他三個指標,首先分別計算平均值和標準差,高于平均值加1個標準差定義為優,在平均值加0.5個標準差和平均值加1個標準差之間定義為良,在平均值加0.5個標準差和平均值減0.5個標準差之間定義為中,低于平均值減0.5個標準差定義為差。然后基于離散化處理后的數據,分別計算出各分項指標的信息熵和貢獻值。最后對貢獻值做歸一化處理,便得到各分項指標的權重。
基于2006―2010年的數據,通過粗糙集方法,得到農業貸款與農業GDP之比、農民人均小企業貸款與人均貸款之比、人均農民貸款與人均貸款之比、獲得貸款農戶比例、良好貸款率的權重分別是023、0.16、0.24、0.14和0.22(見表2)。五個指標都顯著大于0,說明五個指標在評價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時都很重要,不能相互代替。
(2)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校正因子的估算
由于各地區農業發展與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農村金融需求以及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存在顯著差異。基于五個指標的評價結果需要用校正因子進行調整,才能更好地反映農村金融發展的實際水平。具體方法是:首先運用粗糙集方法獲得的五個指標權重對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進行初步評價,得到校正前的農村金融發展水平RF′:
式(2)中5個指標采用離散化分等后的值。然后以RF′為因變量,以農業GDP與GDP之比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便可得到式(1)中的校正系數μ。運用2006―2010年31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選擇空間固定效應模型,得到模型的F統計量為8.715 8,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農業GDP與GDP之比的系數為1.117 0,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業發展與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對農村金融需求產生了顯著的沖擊。工業化進程滯后的地區,農村金融的需求面更大,農村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也可能更明顯。通過模型分析,得到式(1)中的校正系數μ為1.117 0。 (3)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
將各分項指標的權重和校正因子代入式(1),可得到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模型:
運用式(3),可計算得到2006―2010年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得分(見表3)。得分在3.5以上是優等發展水平,得分在2.5~3.5之間的為良好發展水平,得分在2~2.5之間的為中等發展水平,得分在2以下的是差等發展水平。根據這一標準,對2010年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進行分等,結果表明:只有浙江省農村金融處于優等發展水平之列,其得分最高,為3.625 2分;寧夏回族自治區、江蘇省、上海市、山東省、甘肅省、山西省、江西省、貴州省、云南省和陜西省等10個省市區農村金融處于良好發展水平;另有17個省市區農村金融處于中等級發展水平;而重慶市、湖北省和海南省得分分別為1943 4、1.909 8和1.437 9分,其農村金融處于差等發展水平。
基于表4分析結果發現,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總體水平在上升。2006年,全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均值為1.937 5,處于差等發展水平,而在2010年,全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均值提升至2.387 3,增長了23.22%,年均增長4.26%。更可喜的是,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差距有縮小的趨勢。2010年,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GINI系數、GE0和GE1分別為0.086 8、0.013 2和0.013 1,在2006年的基礎上分別減少了9.30%、10.20%和9.66%。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減少。但也應看到,這種縮小的趨勢不是直線式的,2007年和2008年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在擴大。2008年,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GINI系數、GE0和GE1分別為0.122 7、0.027 1和0026 2,在2006年的基礎上分別增長了28.21%、84.35%和80.69%。而在2009年,地區差距又迅速縮小。究其原因可能是2008年以后農村新型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大大拓展了各地農村金融發展的空間,尤其使原先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得到了較大的提升。2008年成立的107家農村新型金融機構,除了19家在東部地區外,其他的88家全在中西部地區;2010年農村新型金融機構已達到383家,農戶貸款余額達1 929 414萬元,相當于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農戶貸款余額的1.15倍,相當于五家商業銀行農戶貸款余額的7%。可見,自2006年開始的新一輪農村金融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四、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發展與改革的建議 本文剖析了現有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度量方法存在的缺陷,建立了“三位一體”“5指標+1因子”的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復合度量體系,并對我國各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研究結果表明:2006年以來,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總體水平明顯上升,區域差異有縮小的趨勢;但農村貸款的集中度在提高,獲得貸款的農戶比例處于下降態勢,農村金融“嫌貧愛富”的狀況依然在加劇。特別是還有不少地區,農村金融要么遠離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不能對農業進行有效的金融支持,農村貸款出現了異化,犯了“方向性”錯誤;要么遠離農村經濟中數量最大的經濟主體,不能對農戶進行有效的金融支持,導致農村金融不能“生根”;要么偏離了農村金融發展的本義,呈現農村金融功能的異化,不能有效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村經濟發展。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在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產業發展結合不緊密,農村金融被動服務的狀態沒有根本改變,農村金融主動服務現代農業發展的機制體制不健全。本文就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發展與改革,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兼顧農村金融的可持續性和滲透度,建立政府、農民和銀行共贏的農村金融發展機制 新一輪農村金融改革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農村金融機構的商業化運作更加明顯,農村金融風險控制更加嚴格,不良貸款比例大幅下降,農村金融的可持續性特征得到彰顯。但農村金融的滲透度卻大幅下降,普惠制的農村金融體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下一階段,必須要重視農村金融的可持續性與滲透度的兼顧問題,部分地區可以適當增加貸款的風險容忍度,通過市場與政府兩種手段,協調政府、農民和銀行的利益沖突,建立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機制。研究發現,可持續性和滲透度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獲得貸款農戶的比例每提高1%,不良貸款率會增加0.2%。目前不少地區,將不良貸款率控制在1%的水平,獲得貸款農戶的比例只有14%左右,這對很多農戶產生了嚴重的金融排斥效應。建議各地區將農村金融不良貸款率控制在3%左右的水平,并建立由政府、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戶共同分擔農村金融風險的機制。
2.推進農村金融與農村產業發展的有機融合,建立城鄉一體的價值鏈金融制度 當前農村金融存在的諸多問題都根源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產業發展的脫離。實現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突圍的關鍵是要深度推進農村金融與農村產業發展的有機融合,構建城鄉一體的價值鏈金融制度。城鄉一體的價值鏈金融制度,是從農村產業鏈的角度而不是從單一農戶或農業企業的角度進行信貸制度設計,農村金融主體深度介入農村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并進行有效的金融服務,以推進城鄉一體化農村產業鏈的形成和有效運轉,促進農村產業鏈價值最大化,實現城鄉共贏的農村金融制度安排。城鄉聯結的農村價值鏈金融制度,可以“三位一體”地促進農村金融發展:一是有利于農村產業鏈的形成和有效運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解決傳統農業項目風險高、收益低的問題,增加農業對資本的吸引力,為農村金融發展提供良好的產業基礎,對農村金融發展具有“方向性”糾偏效應;二是有利于系統性化解產業鏈上農戶以及生產、流通等各環節企業組織的資金約束,增強對農戶的金融服務能力,解決農村金融的“生根”問題;三是從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角度進行資金配置,有利于降低農村金融的運行風險,提高資金配置的總體效益,提升貸款質量,解決農村金融商業化運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3.推進農村金融與現代農業的有機結合,建立農村金融引導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效機制 農業現代化是新時期推進“四化”建設的基礎。農村金融重要的職能之一就是要維護好農業產業鏈上各主體的共同利益,實現農業產業鏈價值的最大化和農業剩余的最大化,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當前需要深度推進農村金融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結合,建立農村金融對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效引導機制。具體而言,重點需要做好四個方面的結合:一是通過農村金融誘導農業產業鏈與農業區域專業化和規模化相結合,促進農村經濟“線”和“面”的協同發展,優化農村金融的運行環境;二是農村金融要為農業技術、農業機械化、農業信息化服務提供融資便利,促進農業產業鏈與先進生產要素相結合;三是農村金融要為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提供融資便利,促進農業產業鏈與現代化農業生產組織相結合;四是農村金融要為專業大戶、職業農民、技術能手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促進農業產業鏈與現代農村人力資本相結合。
推薦期刊:《中國金融》創刊于1950年,是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中國金融出版社主辦的全國性金融政策指導類刊物。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