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錯案追責制度運行中的困境及原因探析
時間:2019年09月09日 分類:政法論文 次數:
內容提要:為了避免錯案的出現,清廷建立了以“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為主要方式的錯案追責制度,但該制度在運行中卻遭遇困境,地方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予以抵制和規避。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實際上是基于制度設計與既定目標相悖,面對無法完成的目標和強大的處罰壓力,官員不得不作出規避性應對,使制度運作未能實現目標。
關鍵詞:錯案追責,連帶責任,結果追責,規避錯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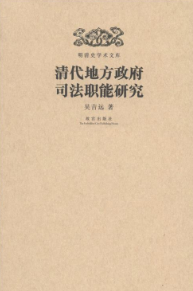
為了實現“案無疑竇”、“無枉無縱”,保證案件得到正確的審理,中國傳統社會較早形成了以錯案追責制度為代表的官員司法責任規范。已有學者對該主題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既包括對某一朝代錯案責任規范的梳理,①也包括對整個歷史發展脈絡進行的宏觀分析,②還有通過比較研究試圖從古代錯案追責制度中獲得一些借鑒與反思的文章。③
既有研究似乎缺乏對中國古代錯案追責制度運行效果的微觀考察,進而也就無法對該制度展開深入的探究。本文通過對清代錯案追責制度施行方式及運行狀況的分析,指出以“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為主要方式的錯案追責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效果不佳,產生了官員對其的規避現象。而其之所以在實際運行中產生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設計與既定目標相悖,面對無法完成的目標和強大的處罰壓力,官員在實踐中不得不結成利益共同體來對抗相應制度。
一、清代錯案追責的主要方式
清代對于官員錯案責任的規范不僅包括《大清律例》中的相關條文,還體現在《吏部處分則例》的詳細規定中。正如瞿同祖先生所指出的:“《官司出入人罪》條規定官吏故出入人罪者,即以所出入之罪反坐之,處以杖、徒、流或死刑,失出失入者,減等擬罪。但實際上,尋常失出失入皆按《吏部處分則例》議處(罰俸、降級、革職),向不引用刑律。只有情罪嚴重的案件,經皇帝降旨交刑部議處時,才引用刑律。”④
的確,除了《大清律例》中“官司出入人罪”、“斷罪引律令”、“斷罪不當”等條文的規定外,⑤《吏部處分則例》對官員錯擬案件的情形作出了規定,其既包括了改造口供、草率定擬導致故意出入人罪的條文,還有失出失入、失錯遺漏、秋審錯誤等處分辦法。⑥不論《大清律例》還是《吏部處分則例》,均體現出清代兩種主要的追責方式,即“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
(一)清代官員的錯案“連帶責任”
顧名思義,官員的錯案“連帶責任”就是指因案件裁判有誤,從承審官員到各級審轉官員均需承擔責任。通過這種方式,清廷希望既保證上級官員積極發揮監督職能,又使得承審官員在上級監督的壓力下妥善履行職責,減少錯案的出現。《大清律例》“官司出入人罪”條十分明確地規定了這種連帶責任:“并以吏典為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佐貳官減首領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科罪。”⑦
這表明承辦案件的官員均需承擔責任,而其處罰力度則是逐級降低的。同樣地,《吏部處分則例》中的相關規定也體現了連帶責任的特點。例如,早在康熙九年(1670),清廷就規定了官員因過失導致案件判決有所出入的處罰標準,其依照府州縣、司道、督撫三個層級分別予以處罰。⑧上述則例規范雖然在其后經歷了一系列的修改與完善,但各級官員連帶責任的特征并未發生改變。
(二)清代錯案追責中的“結果歸責”
從清代法律規范的構建來看,盡管存在一些免除或減輕處罰的條文,但其總體上仍呈現出有錯案必追責的態勢,即只要官員承審或核轉的案件最終被認定存在錯誤,就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即筆者所稱的“結果追責”。
《大清律例》的相關律文鮮明地體現出了結果歸責的特點。“官司出入人罪”條規定,對于故意出入人罪者,其所承擔的責任是根據其將罪犯出罪或入罪的程度來決定的,即如果將無罪者判為有罪或有罪者判為無罪,則相關人員須被判處與錯判刑罰相同的刑罰;若僅是增加或減輕刑罰,則其根據其增減的程度來折抵刑罰。對于過失造成擬罪出入的官吏,同樣是根據上述原則予以處理,只不過是在故意造成錯案的處罰結果上予以減等。⑨
“斷罪引律令”條規定,對于皇帝臨時斷罪的特旨,不能作為定律來比照使用,若官員混行比照,從而造成罪有出入的,需按照“官司出入人罪”的處罰標準來定罪量刑。⑩其同樣是基于造成錯案這一結果來作為追責的標準的。
《吏部處分則例》中的錯案責任規定也反映出以結果為導向的追責傾向,其同樣區分了故意與過失,但不論何種情形,只要造成了擬罪出入的,則例就會將其納入錯案責任的考量范圍之中,而其處罰的力度恰恰就是根據其錯誤的嚴重程度來決定的。盡管也有一些條文涉及到了官員司法活動中的具體行為,如改造口供、草率定擬等,但清廷并非以其行為本身作為追責的標準,而是將其作為判斷官員主觀方面的依據,即通過這些行為反推官員主觀上存在故意,從而加重處罰,因此這些條文的側重點仍是在改造口供、草率定擬之后所導致的“故行出入”、“枉坐人罪”等具體后果。
輯訛輥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一般情況下,只要擬罪結果與最終判決結果出現偏差,即從司法結果上看,未能實現情罪相符的最優結果,就形成錯案,追責制度便立即啟動。而有關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因素,僅是錯案追責開始之后處分程度的考量因素;即便是涉及官員行為的條文,也不過是為了考察其主觀過錯程度,以便增減相應處分。由此看來,清代錯案追責制度具有“結果歸責”的特點。
二、清代官員對錯案追責制度的規避
盡管清廷構建了詳細且全面的錯案追責制度,但相關規范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出現了地方官員規避、對抗錯案追責制度的現象。筆者主要以“部駁改正例”的形成與發展為線索,分析“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為特征的清代錯案追責制度在適用中遭遇的困境。
(一)“連帶責任”的崩潰——“部駁改正例”的出現與修正
連帶責任之設置初衷是通過增加承審官員所面臨的壓力來督促其切實履行審判職能,從而防止錯案的出現,亦即當承審官員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將連累上級官員時,會促使其更加謹慎地作出判決。但該制度在實際運行中卻并未體現出上述效果,反而促成各級官員基于抵御連帶責任之風險而結成利益共同體,來規避錯案責任。這一現象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都察院左都御史蔡升元的奏折中得以體現。
其指出:“督撫審擬案件,有宜駁正者,如所引律例不符,或前后請詞互異,經部院衙門駁回,令其詳審,該督撫恐承審各官有失入失出之罪,而伊等亦自涉朦混之愆,遂始終徇庇,不即改正。”輰訛輥根據他的描述,當錯案發生需要追究官員責任時,督撫官員會為了避免連帶責任之風險而庇護下屬官員,不立即對部院駁回案件予以改正。
清廷隨即認可了蔡升元的奏請,批準了他的立法建議,于是,在《吏部處分則例》之中有了如下規定,即所謂“部駁改正例”:凡督撫具題事件內,有情罪不協,律例不符之處,部駁再審,該督撫虛心按律例改正具題,將從前承審舛錯之處,免其議處。若駁至第三次,督撫不酌量情罪改正,仍執原議具題,部院復核其應改正者,即行改正,將承審各官、該督撫,皆照失出失入例分別議處。
輱訛輥這也就是說,一旦督撫對刑部指出的錯誤之處予以糾正,各級官員可以免受處罰。這一規定基本免除了官員由于過失導致錯案時的責任。只有當駁至第三次,督撫對于應該改正之處仍然不予改正的,督撫及其下屬官員才予以追責。從清廷的這一反應可知,這種督撫庇護下屬從而對抗錯案追責的現象有可能呈現普遍化的趨勢,從而引起了清廷的注意。
同時,基于原有連帶責任的方式遭到規避,反而容易導致錯案難以發現和糾正,因此清廷立即通過立法的方式予以彌補,終止了督撫與下屬官員之間的連帶責任,以便保證督撫可以沒有顧忌地及時上報并糾正錯案。盡管其后清廷對該例文不斷地進行調整,逐漸恢復了對部分官員錯案責任的追究,但這種限制連帶責任的做法始終得以保留。這顯然表明,由于實踐中該規范遭到地方官員的抵制與規避,通過“連帶責任”來追究官員錯案責任的方式宣告崩潰。
(二)“結果歸責”追責方式的恢復及其效果
根據上文對“部駁改正例”的描述,在免除督撫責任的同時,清廷也免除了其下屬各級官員的失出失入責任。這顯然是為了保證中央政府能夠得到充分的信息,避免錯案被掩蓋而難以糾正,于是打破原有規則,在減輕了連帶責任的同時,也部分犧牲了原本以“結果歸責”為特征的錯案追責制度。該規范的出臺導致錯案追責的目標發生了偏移,從原本為了在地方上減少、消滅錯案的初衷轉變為便于中央糾正錯案。既然目標發生了偏移,原有規范被限制,錯案核查的壓力基本上移歸刑部,則自然也就無法發揮地方上努力減少錯案的效果。
清廷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據給事中富爾敏的上奏,皇帝認為涉及凌遲斬絞立決的案件關系重大,若按之前的規定,對于過失錯擬的州縣官與知府不予追究責任,則“揆之情理,原未允協”,不僅難以減少錯案的發生,還會導致官員在審理案件時掉以輕心,增加錯案出現的風險。輲訛輥于是,清廷逐漸將錯案追責的重心恢復到推動地方官員努力減少錯案的目標上來,主要通過限制“部駁改正例”中基層官員錯案免責的適用范圍,復歸以“結果歸責”為特征的錯案追究模式。
具體而言,根據乾隆三十八年的旨意,對于刑部將錯案駁回后予以改正的情形,知縣與知府喪失了原有的免責優待,若其將“凌遲斬絞立決重案,擬罪失之過輕”,則須“照例實降”;若“監候以下罪名錯誤”,則需由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聽候處分。
輳訛輥其后乾隆朝的《吏部處分則例》便出臺了細則,對于部駁案件,承審之府州縣官員要區分三種情形追究錯案責任,即罪名輕重懸殊,罪名出入不甚懸殊,以及情罪基本相同、僅是在斬絞立決與監候之間或徒杖與軍流之間有所出入,并分別施以實降一級調用、降一級調用、罰俸一年的處罰。輴訛輥雖然其并不適用失出失入例予以處分,但這表明清廷已經極大地限制了官員錯案免責的“特權”,轉而開始注重對造成錯案的官員的追責,特別是針對知府、知縣。
與此同時,乾隆四十五年(1780)核準的條例對上司改擬的情形也相應進行了調整,按照新的規定,州縣官員即便依照上級意見對案件及時予以改正,也需承擔錯案責任,而處罰的標準則是按照經過修訂后的部駁改正例。輵訛輥這同樣表明,清廷已經把追責的標準著重于錯案發生,恢復了有錯案即有責任的特點。嘉慶年間,部駁改正例經歷了重大修改,并于嘉慶九年(1804)修入則例:凡督撫具題事件,內有案情不確、律例不符之處,部駁再審,該督撫轉飭復審各官,遵駁改正具題。
除審轉之督撫司道免其議處外,承審及審轉各官,原審律例不符者,照失出失入例減等議處;原審官未經審出實情,如罪有出入者,仍照失出失入例減等議處;罪無出入者,照不能審出例減等議處。
例應革職者,減為革職留任;例應降級調用者,減為照所降之級留任;例應降級留任者,減為罰俸一年;例應罰俸一年者,減為罰俸六月;例應罰俸六月者,減為罰俸三月。如系刑部徑行按律改正具題者,照失出失入本例議處,毋庸減等。輶訛輥這表明免責適用的情形又進一步縮小,對于部駁案件,只要由于擬罪出入而被刑部駁回,府州縣官員都必須在失出失入例規定的處分上減等議處;若刑部直接改擬,則承審官員直接照失出失入例議處。輷訛輥錯案免責范圍的不斷縮小體現出了錯案追責的結果歸責特征,即免責情形的減少使得錯案與官員責任之間的關聯性逐漸加強,對于一般情形下的錯案,均需有相關官員承擔責任而無法免責,從而形成了以初擬錯案為標準的歸責模式。
那么,在恢復了以“結果追責”為核心的錯案追責制度后,其施行情況又如何呢?事實上,其遭遇了同樣的困境,存在督撫庇護下屬官員,規避錯案追責的現象。例如,嘉慶二年(1797)的一起案件中,督撫將“例得免議”作為借口,試圖為其下屬官員開脫責任。此案為強盜案件,初審官員未審出真正盜首,而將尚未捕獲之從犯誤作主犯審擬定案,按照則例規定應當依照不能審出實情例降一級調用。
但巡撫在題本中聲稱,由于該官員未來得及復審就已離任,該案是經繼任官員審出實情,且“尚未招解,例得免議”,故此應免除承審官員的錯案責任。吏部查核之后指出,則例中并沒有該免責條款,該官員仍應依照規定受到處分。輮訛輦由此可見,為了使承審官員免于錯案追責,督撫不惜謊稱“例得免議”,從而試圖阻撓錯案責任的執行。又如乾隆六十年(1795)的一件題本中,兩江總督蘇凌阿由于包庇下屬錯案責任,試圖使藩司道府各級官員免受處分,而被依照意存回護降二級調用例予以處分。
此事起因是有兩起案件承審錯誤,擬罪有所出入,因而需要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理論上,由于該案由總督與藩司道府各級官員會同審理,故而參與審理的官員均需承擔相應的錯案責任,但蘇凌阿卻在奏折中聲稱該錯案是因其改擬錯誤所導致,并未由下屬各級官員成招。根據《吏部處分則例》的規定,若原擬本無錯誤,而是由該上司更改失當,則只需將該上司亦照部駁改正例議處,原審官免于議處。
因此,該總督隱瞞審理實情的做法無疑是為了庇護下屬,希圖為各級官員寬免處分。皇帝發現后認為其“見好屬員,沽名邀譽,實大不是”,于是下旨要求交部嚴加議處。輯訛輦然而,上述這種官員對錯案責任的規避真的僅僅是為了博取名聲嗎?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以“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為特征的錯案追責制度在實踐中施行效果不佳,無法實現減少錯案的目的,反而遭到官員的規避與抵制呢?
三、制度設計與既定目標的錯位
實際上,這種地方政府通過作假、變通、包庇等行為來規避責任、應付共同上級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中國傳統社會所獨有。有學者從組織社會學的角度對該現象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將其稱為“共謀行為”,即“基層政府與它的直接上級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種策略應對來自更上級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檢查監督。”輰訛輦學者在分析這種“共謀行為”時指出:“由于某些激勵機制的設計與實際組織運行邏輯不符,導致了相互間不兼容甚至沖突;而這些矛盾沖突造就了與中央政策相悖的利益共同體,為基層政府間共謀行為提供了利益基礎。”
輱訛輦與此同時,正是基于激勵機制與實際運行中的偏差,官員往往面臨無法完成的目標和巨大的懲罰壓力,這促使其只能通過共謀行為來予以應對。而當激勵(懲罰)強度加大,則意味著問題暴露后官員將面臨更加嚴厲的處罰,這無疑會進一步增強了其通過共謀行為來規避風險的沖動。換言之,“在激勵與組織目標不一致的情況下,正式激勵機制力度越大,目標替代的現象越嚴重,共謀行為的驅動力便越強”輲訛輦。
換言之,如果制度設計的激勵作用與既定目標偏離或相悖,則官員不管如何努力都無法實現既定目標,那么仍然堅持適用這一制度或增加激勵強度只能促使官員尋求作假、變通、包庇等行為來規避這一制度,即產生“共謀行為”。反觀清代錯案追責制度,“共謀行為”則特指在面對錯案追責時的地方各級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通過各種方式來規避風險、逃避責任的現象。
那么,該制度在實施中體現出的這種“共謀行為”是否也是基于制度設計與既定目標的錯位所造成的呢?如前文所述,清代錯案追責的兩種主要方式為“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而其均體現出對錯案“零容忍”的態度。
誠然,這種錯案追責制度會對司法官員產生威懾的效果,但當官員在既有制度的激勵下妥善履行職責、認真審理案件后,是否就能保證錯案不再出現了呢?顯然,清廷在錯案的發生與官員的瀆職之間構建起了單一的因果關系,認為冤假錯案之所以不斷出現,是由于承審官員未認真履行職責造成的,因此,只要加強對相關官員的追責力度,施行嚴厲的錯案追責制度,就能夠起到懲罰和預防的作用,從而避免錯案的出現。
而實際上,錯案的形成是由多種原因所導致的,承審官員的行為僅僅是錯案發生的充分但非必要條件。若僅僅依靠上述錯案追責制度而尋求錯案的消失,則不論官員如何努力,不管制度多么嚴厲與完善,都無法實現這一目標。具體而言,錯案的產生可能與案件本身的復雜性、外界環境的影響、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等一系列因素有關。
結語
為了實現杜絕錯案的目標,清廷不斷地完善錯案追責制度,試圖通過“連帶責任”與“結果歸責”兩種方式來避免錯案的出現。但實際運行中,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出現了官員共同規避、抵制的現象。究其根源,清廷在制度設計時,未能充分區別導致錯案的各種情況,對既定目標的可實現性過于樂觀,從而制度所能實現的效果無法保證目標的實現,兩者出現了偏移與背離,因此才促使官員在面對無法實現的目標與日趨嚴苛的處罰壓力下,轉而選擇規避與抵制。
當下,在司法改革的關鍵時期,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錯案并規范司法官員的行為無疑成為重中之重。以法官錯案責任制度為例,我國自1990年于河北秦皇島市海港區法院率先確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以來,便逐漸對其予以進一步的推行,并著力加強配套制度的完善。
1992年,河北省開始將該制度在全省推行,隨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將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在全國予以推廣,并制定了相關的試行辦法。與此同時,學界對錯案追責制度也展開了討論:一些學者堅持建立和維護錯案責任追究制度;輱訛輧另一些學者則更為重視錯案責任制度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完善措施;輲訛輧更有許多學者則旗幟鮮明地對錯案責任追究制提出了批評。
輳訛輧而隨著2013年《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以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等規范的發布,我國對于錯案責任制度的構建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筆者認為,在完善法官責任制度的過程中,如何充分考量機制運作內在的因果關系,設立明確且妥當的目標,怎樣保證制度構建與既定目標保持一致,避免兩者相悖產生的不利影響,都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而中國傳統社會中已有的經驗教訓恰恰能夠為如今的改革路徑提供有益的參考。
相關論文范文閱讀:剖析清代司法體制產生弊端的緣由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幾千年來士人晉升的途徑,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成為包括清代在內的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如《紅樓夢》中的賈雨村,早年寄居于葫蘆廟內,以賣文寫字為生,幸得甄士隱相助,進京參加考試,一年便中進士,成了知府。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