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評符力的《槐花香》
時間:2021年11月13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符力是一個典型的純正的抒情詩人,他的特別在于他將海南島的清新濕潤氣息帶進了詩歌,當然也有一些憂傷。 一個經常被遺忘的島嶼上的詩歌,呈現出的特殊優雅面貌,無疑會讓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 ”在這里,李少君首先肯定符力詩歌的抒情特質; 其次,指出其詩歌寫作帶有地域性特點,從而凸顯出了他個人化的詩歌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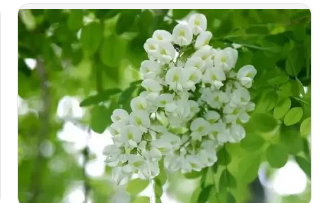
早在新詩發軔之初,于賡虞就指出:“詩歌的靈魂是情緒——是人生和宇宙中間所融化成的一種渾然之情緒表現。 ……詩歌最緊要的質素是這樣情緒的表現,而非思想的敘述。 ”從某種意義上看,符力的詩歌也常常表現為一種情緒。 除了少量略顯激越的詩篇之外,他往往從生命的簡潔躍動中發掘出那些在內心中隱隱流動的水瀾,將它們悄然注入詩中,從而讓詩歌有了流動的活力。 如作品《后溝之夜》《槐花香》《每棵樹都有自己的難言之痛》等都是如此。 當然,詩人的這種情緒不是顯豁的,它被詩人隱藏在了描述的語言中。 宋人魏泰說“情貴隱”,有時這不僅僅是一種技巧,更是詩人內心的隱秘情緒決定了詩歌寫作必須如此。
明清之際的學者黃宗羲曾說:“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 ”其所謂“情至”是說內心因被激發而情感來臨了,“情不至”則指內心的情感沒有被激發出來從而也就無從流露。 此所謂“情不至”有點類似于理論家常說的“無病呻吟”。 而一個人之所以會如此,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因素是詩人沒有這方面的情感體驗,而是硬著頭皮進行創作。
前文李少君的評論指出符力的特別在于“他將海南島的清新濕潤氣息帶進了詩歌”,實際上是已經指出了其詩歌抒情性的一個重要特色,那就是他的許多詩歌摹寫的都是海南這一特定地域的風土人情、行為事理。 這一點當然與符力本人是海南本土人有關。 故而其抒寫帶有故鄉性的內心體驗,從情感上而言,大致不會有多少偏差。 因此,在符力的詩歌中我們所見到的透露海南氣息的作品,往往都是因感至而情深。 如其《過譚昌村》《地坡嶺聽雨》等都是此類成功的詩篇。
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說,“情以物興”(《文心雕龍·詮賦》),又說,“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 可見,在抒情的文學中,外物有著迎意引心的重要作用。 細讀符力詩歌的人還會發現,符力對于“物學”有著一種獨特的偏好。 他的詩歌中總是充斥著大量對物的書寫。 符力一方面通過物在詩中的“生長”與“伸展”,抵達情的所在,另一方面也通過對“事物”的傾心表達建立起了個人寫作的一種指向。 從某種意義上說,“物學”乃是其詩歌成功的一個內在秘密。
植物書寫是符力詩歌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符力對于植物的迷醉在于他并非通過植物的“穿行”來“體物”,而主要是通過它們來營造一種抒情的氛圍或以之作為抒情的載體。 所以在符力的詩歌中,我們很少看到他有對植物進行的純客觀描寫,即使有,也往往是將對物的賦詠融入抒情之中。 如其《槐花香》一詩中寫到的“槐花”,《平原上的黃昏》一詩的第三節中羅列的十四種植物。 符力的主要目的是以之來渲染人的情緒,但這些植物又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它們與平原和黃昏形成了一種相互依附的關系,其實也就是與詩人的情感形成了一種內在關聯。
符力的確偏愛將植物付諸詩歌,這說明他是熱愛生活的,熱愛大自然及其所容納的各種生命的,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總是將這一點在詩歌中體現出來。 當然,作為一個在海南本土生長的詩人,符力對于海南植物的找尋與入詩也許還有更深刻的意義。 他一直在海島上虔誠拜寫的那些植物,它們本身或許也是作為靈魂的一種所在。
其實,從某個角度看,我更青睞他對于那些普遍性“事物”的著迷敘述。 他總是將這些體味深深地嵌入詩歌中,對這些“事物”進行著或狂歡或哀歌式或低沉或高昂的糾察與細讀,讓它們在素樸的出場中有了召回某些“通向未知”的可能性。 在《書坊小記》中,他惘然而又喜悅地敘述:“已是大寒之日,沿著那些紛繁又細小的路子/一些事物早已逃離,一些事物/正秘密歸來”。
而值得指出的是,詩人這些在詩歌中“特立獨秀”的句子大都處于詩歌的開頭、結尾部分,即使少數不在這兩個位置的句子,也都處于詩歌中間非常顯要的位置。 這說明詩人是有意安置這些詩句的寫作的。 從寫作學的角度講,這并非一種偶然,他昭示著詩人通過對某種技巧(或方式)的運用建立起了個人寫作的一種向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趙目珍,青年詩人,批評家。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