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以象外的暢想與神思——當代文化語境中的藝術思考與實踐
時間:2020年04月20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一、精神的遠游“超象”,作為藝術命題提出伊始,經過從古至今的奠基、揚棄、生成與綿延,已然成為跨越國界的藝術理論概念和藝術實踐的探索課題。“超象”是當今世界藝術發展新思維、新觀念的必然歷程。從創作實踐到理論探索,都是基于國際文化視野、華夏文化復興的意識,來高度把握并應對世界藝術的新格局、新變化,力圖以“超象”這一精神性藝術標志的確立,推進現代水墨藝術的發展,賦予水墨藝術以新的生態倫理價值和美學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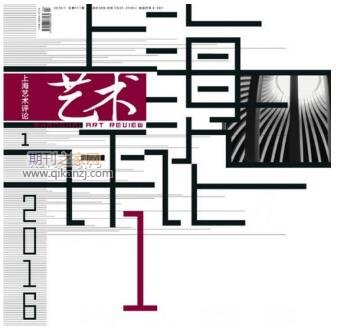
“超象”概念源于我國古代藝術思想。早在唐代,司空圖就在《詩品》中提出“超象”概念,即“超以象外,得其寰中”“離形得似”等等,用以指涉取之象外,略于形色的思維特點和藝術表現方式。作為中國藝術最高境界和最高精神目標,“超象”令藝術家及其作品不斷向心靈靠近,并遠離自然與世界的形而下特性,不斷地打破物與我的二元對立,使之契合,最終實現和諧統一。“超象”的提出及其在藝術實踐中的運用過程始終以人為主體,體現為人之自由意志的覺醒和藝術精神的覺醒。
“超象”的“象外之象”“略于形色”“取之象外”,是由此及彼,由顯而隱的提升與深入的過程,強調一種由內心意緒向生命情懷與精神境界的轉換,進而在趨于抽象卻又具體可感的藝術形態中,領略一種陌生化的玄妙意味,這是一種超驗的審美感覺。與此同時,繪畫材料與手法亦在“以技入境”中被賦予高度的意義與內涵。誠如我在自己作品《超象》系列中所表現的結構、節奏與虛靈,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呈現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象外之象”的抽象效果。
當然,對于“超象”的理解、把握與運用,是因人而異的,在藝術家那里,它往往是在完成內在自我本質的轉換之后而見諸于作品的。天地有大美而無言,事實上,對“超象”的取舍及態度的親疏,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觀、藝術觀和人生觀,乃至生命體驗、審美經驗與精神境界,在這種特定的無言之美中,體現的則是人的精神自由與情性率真的玄思與遙想,在繪畫中,則呈現為一種不可言說的幽玄秘境和精神遠游的神秘。這是難以用常規符號、技法去固定表現的,它們或濃郁,或淡然,或清麗,或雄渾,其色彩、形態的流變,激發與幻化,展示的正是“超象”那難以測度的高風遠韻。
質言之,“超象”的關鍵與根本之處,首先是一種對物性與形象的超越,這是一種向三維空間之外的更大境界的超升——對宏觀世界、對生命幽微本質的抽象性把握。因為,任何本質性藝術的運動與把握都是一種純粹的形式追尋與發現,是從形質世界向性靈世界的過渡,也必然是一種脫略形跡的提升與超越;而且,唯有在此中,才能表現出其深奧之處,顯示其最微妙的所在,并超越現象而走向純粹與永恒。在這里,藝術法則、規矩、范式、理念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超象”的突破中表現智慧、靈性、才情、氣質、格調、能力。
此外,由于它的純粹性和元初本真的特點,一切外在的、附加的、雕琢的、世俗的、偽裝的成分都被統統剔除和拋棄了。因此,它表現出來的乃是一種內在的、本質的,也是更自然的風格品質,展示出的則是內在的智慧、自在的精神、宏觀的視野、脫俗的風度,這便是“超象”的風采和韻致,也是一種審美重心的轉移。
繪畫創作中的“超象”經歷了一個從生命之沖動到天地運動、靈性之氣韻,再到造化之氣韻的轉化過程,最終合并一體并將它集中在色彩、筆墨的揮灑、運作之中,使之“得其神而遺其形,留其韻而忘其跡”。在看似隨機無意的潑、灑、揮、滴與疊加、覆蓋、錯置當中,體現出的都是畫家胸有成竹的匠心獨運。細細看去,在漫漶氤氳的畫面中,在如同風云際會、驚濤拍岸的墨色形態中,體現出的都是出自畫家生命力的充沛和昂揚,其中蘊含著支撐動感畫面的穩定結構。
與寫實、摹仿風格的繪畫相比,這是一種風格的巨變,也是對傳統審美旨趣的轉化,實際上,它只不過是今人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對“超象”的重新認識和解讀,這也是一次全新的發現。從根本上說,這是靈性十足的精神運動外化為飄逸、靈動、灑脫的形態,它表現的不是現象世界本身,而是關于世界可能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的精神圖景,這是一種境界,讓人身不由己地感受到自然生命氣韻的變異和澎湃。“超象”之后,結果必然如此。簡而言之,“超象”作為藝術概念,有這樣的特點:它以體驗和感悟為內涵,并形成特點,趨向于宇宙論、價值論乃至生態美學的追尋和叩響。它以宇宙運動形式為內在結構,強調創造性活力、活躍的生命精神、和諧的形式內涵和浩蕩無垠的詩境。它強調個人的主觀靈性和內在價值,并在價值范疇與本體范疇上肯定“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終極境界——“超象”的圖景。
二、心靈的印跡“似者,得其形而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荊浩在《筆法記》中,對繪畫的“似”與“真”做了本體意義的區分。“似”,指表象的相似,它缺乏內在生命結構與本質之處,僅止于“有形無神”而已;而“真”,則包含了事物的內在生命氣質、結構與氣韻,所以,它充沛、豐滿而又神采飛揚。后者正是“超象”特有的本質之“真”,它具有形而上的意義,賦予事物以無始無終的超越性邏輯關系的形態,并在三維空間之外呈現其神奇魅力;所謂“超象”,是一種超越表象的本質意義的“象”,是事物的終極存在,它展示的是終極的創造與心靈的印跡,是具有原創意義的藝術形式、結構與語言。
當代文化語境中的“超象”不只是審美問題,作為心靈印跡的表現形式,它體現的是一種自由精神與無拘無束的想象力;在今天,“超象”已不再是古典藝術的自律,而是藝術自身價值的體現,是對傳統審美定式的解構,因此,當代“超象”是藝術創造與當代精神共同孕育出的結果。因此,我們重釋“超象”,是以反思社會現代性的危機和西方現代主義的危機為背景的。現代科技帶來的弊端,使得具有生態美學涵義的“超象”審美意識日漸凸顯出重要性。
現代技術造成的資源枯竭、土地沙化、環境污染等弊端只是結果,根源在于現代技術與生態的敵對性質。海德格爾在分析“技術”的詞源時指出,“技術”在古希臘的本義是“引發”,技術與藝術一樣是解蔽的方式、真理發生的方式,而現代技術卻違背了其本義,成為一種“促逼”。并非現代技術發展到今天才成為人們無法控制的東西,而是現代技術從本性上就無法控制,它已經將人從地球上連根拔起。
現代技術不僅造成生態系統失調,威脅著其他物種生存,而且剝離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把萬物貶低為資源。現代技術作用下的人類,不僅把自然界作為能量儲存器,而且使人脫離了自己的本源。在這種情況下,“超象”式的審美意識成為對抗生態危機和人性異化的途徑。“二戰”之后的西方當代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以及精神性藝術的發展,是在重新認知猶太教—基督教的創世論之同時,大量借鑒了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諸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有關“生生為易”“元亨貞吉”與“坤厚載物”的論述,道家的“道法自然”“萬物齊一”、佛家的“眾生平等”等。
這些豐富的古代生態智慧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的生存方式與思維,可以成為我們建構“超象”藝術的豐富資源與素材。因此,“超象”藝術以“天人合一”與生態存在論審美觀相會通;以“中和之美”與“詩意地棲居”相會通;以“域中有四大,人為其一”與“四方游戲”相會通;以懷鄉之詩、安吉之象與“家園意識”相會通;以比興、比德、造化、氣韻等古代詩學智慧與生態詩學相會通……我們應該借此來建設一種包含中國古代生態智慧、資源與話語,并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某種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的“超象”藝術體系及其流派。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超象”的生命活力不僅來自其自身,還來自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反思、判斷,同時也來自主體間性的經驗和選擇,特別是在文化的多元格局中,觀念的多樣和媒材的多變都使“超象”確立了更具文化現代性的整體藝術特征。我創作《超象》系列作品,力求在傳統的“度物象而取其真”的理念中提取并建構現代意義的共享價值與共享空間。實際上,“超象”是一個大藝術主題,在這里,我找到了個性化和自我實現的方式,并以自我的方式抵達超我。
在《超象》系列作品中,我大體以傳統繪畫材質為主,宣紙、礦物顏色、墨色、筆和毛刷,同時也混合了外來的水粉、水彩,以及金粉、銀粉等顏色,還加入了拼貼等綜合手法,使墨、色、水、紙等互相沖撞、融合、演繹、幻化,在無序的流淌中進行局部或整體的控制,并在這個過程中完成感覺性與情緒化的介入,在水、墨色的氤氳、沖撞中凝定出心靈的印跡,在隨機性的潑灑、滴濺中表現出對無意識或潛意識的發現與開掘,讓紙上的“超象”再不確定于非具象的形態固化中,體現出自我的作用,揭示出無法復制的精神圖像和心靈印跡,揭示出夢幻、虛無的隨機性背后的心靈豐富性,以及自我感覺的獨特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無意識的潑灑與滴濺中,包含了潛意識下的選擇與控制,不同的色彩間的混融,水分的多少,氤氳與幻化,著色處與空白的布局分配,自然形態與人為的描繪,漫漶的流淌與拼貼的形狀,乃至色彩的濃淡變化……這些均在沒有具體形象的流淌中變成一種狀態、一種綜合,它的含糊性使我們的視線隨著無規則的色墨流淌向畫外延伸;潑灑的色墨、滴濺的點、線、面雖沒有蠕動,但它的節奏充滿了運動感。這樣的抽象形式意味及畫面結構、節奏、韻律、力度,表現的正是期望中的“超象”圖景,也是自我心靈的自然流淌。這種不受約束、不受規范,充滿自由與隨意性的表現方式的核心是自我情緒的沖動與狂熱,它沖破了傳統繪畫逸筆草草、一波三折的限制,把畫面的向心性、平衡特點及構圖的完整性向著更廣闊的空間擴散開去。畫面更注意力度、強度、節奏、韻律與剛柔的對比表現,這種表現必然傳達出畫家自我的主觀意識。
《超象》系列作品最明顯的特點是擺脫了“形”的約束,它們在無形、無序中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力量。把大張的宣紙鋪在地上,通過潑灑、滴濺,造成風起云涌、驚濤拍岸般的抽象狀態,傳達著某種潛意識。在密布的色彩流動、縱橫交錯、氤氳重疊中,那種沒有制約的活力與隨意揮灑的運動感、無限的空間波動愈發變得狂熱而又抒情,這里蘊含著作品生命的關鍵所在。這是一種原創的心靈圖像,它呈現為一種特殊的質感,可謂色墨和諧、動靜統一、從容自然、情緒流動、力量內蓄。這是自然流露出、鮮明而又強烈的自我表現,也是獨白式的自我表達。
我在作品中要表達的是自己對客觀世界的主觀感受,但在創作過程中,由于無意識與潛意識的強大作用,我不知不覺地超越了現實世界的客觀性,關注和強調的仍是自我的主觀感受,以及語言、材料的獨特表現力。當然,《超象》作品既不是傳統藝術所能全然表現的,也不是現代藝術所能全然表現的,它是古典的“取意象外”理念與西方現代藝術的心靈碎片相合互融的結果,進而形成特定的審美空間。在《超象》系列作品中,表現前提不是現實的片段與自然場景,而是從整體去把握并表現自然運動的生命節律的,其中的關鍵在于把對自然的感受積累起來,并歸納出它的內在構成關系和相關精神要素,用直覺的方式打開屬于它們的潛意識領域。
無疑,這是對其精神要素的肯定,為此,必然要對畫面中的時間因素進行消解,變三維空間為二維空間,一切都被平面化,而時間則被空間化,空間籠罩了心理的色彩,使我們得以在同一畫面的有限空間中看到多空間的交疊,這是自由的,也是神奇的,畫家需要將之轉化為邏輯關系和客觀規律之外的自由存在,以及更為鮮明的觀念性要素。
在潑灑與滴濺的過程中,自我與材質之間的復雜、微妙關系,作品的不確定性、無中心感和無界限感構成了《超象》主題的最顯著特點,此時,畫面上呈現的是完全自我的方式和一些不由自主的心靈印痕,可以說,在無意識中留下的是生命本身,展示了一個身不由己,但又從容自然的過程和運動軌跡。潑灑與滴濺使畫面效果往往出人意王林旭金輪紙本綜合材料68×68厘米2005料——大面積的風云翻滾、波濤巨瀾、無邊無際、鬼斧神工般的形態令人浮想聯翩……與此同時,根據畫面自身的需要,再拼貼插入局部幾何形“硬邊語言”,這既增加了平面空間的層次,又豐富了語匯,體現了一種現代意味。
誠如英國學者鮑曼所說“數學是現代精神的原型”那樣,這樣的創作手法突破了“超象”原來的定義,與現代藝術不期而遇,拓展了其外延與內涵。應該說,這里探討的重點不是主題本身,而是幾何性的形、線、型、塊、面、色的成分和內在關系,以及用以造成神秘玄妙的發人深思的效果和張力。《超象》系列作品的基礎似乎不再是現實世界和客觀自然,而是觀念——某種概念的、幾何的、建筑的、夢幻的和虛無的。它不僅表現了自我,還在于表現了一種新的視覺樣式、一種新的藝術秩序及一種新的藝術理想。《超象》系列的起點發端于東方哲學智慧,同時又是觀念與平面空間構成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我們對尺度的把握,對數學關系構成的把握,因此,它不是對社會生活的直接反映,也不像浪漫主義那樣把藝術當做對超驗世界的追求,它是審美自律性的必然表現,也是人堆存在世界主觀感覺的表現。
三、流動而綿延的圓融“超象”是可以綿延的宏遠存在。西方哲學家柏格森的綿延論與“超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認為,一種精神的運動在拒絕一種存在的同時又構建了另外一種存在。而“超象”之深矣、遠矣、不可及矣,則是對所有具象存在的超拔之后獲得的,它沒有實體,然而卻存在;就某種狀態而言,否定即是肯定,泯滅即是創造,虛無即是存在,反之亦然。
因此,“超象”具有鮮明的心靈特點,它以虛無為象征,氤氳為暗示,且緊密聯系著虛靜至極的境界,《超象》系列作品的色彩、筆墨、團塊、點線、幾何形體等的構成與整體關系便是這樣。它不是要表達什么,而是一種暗示,一種隱喻,一種對心靈世界的憧憬,它非具象的潑灑、重疊及整體取向都折射出自我身心的深化、澄化和凈化。在創作《超象》系列作品的過程中,我獲得了“超象”的啟示。同時,我還把我所走過的東西方山水、圣地、名勝、遺跡等融入了寫意與抽象的點線、墨色之中,以及畫面上色彩的漫漶、幾何形狀的交疊,構成關系的相互切割……這里面都有我發自身心的感受與體悟,這不是具象逼真的描繪,而是感覺與情緒的凝定,是一種跨文化價值與意義的建構與努力。
雪山、圣湖、山巒、流水……這些物象都是“得其神而脫其形”的抽象演繹,而作品的總體氣象都是“超象”的啟示或“超象”本身的呈現。因此,它的形式、語言與氣息是深化與凈化的,其抽象的意象便在內心成形,這也是我心靈世界的袒露——素心若雪、獨立蒼茫、泊淡遼闊、廣大精微、熔于一爐。“超象”的理念與我的“超象”主題讓我的作品通向了渾茫圓融的理想境界。從這個角度看去,現代主義藝術體現著新的世紀精神,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著傳統經典理念的某些基本要素。
正如西方理論家西里爾·康諾利指出的那樣,現代主義是從啟蒙主義那里承襲了某些智慧質素的東西,如情緒化、內心化,乃至懷疑主義,以及從浪漫派那里得來的強烈激情與高度敏感。對技術文明推進的反感,有一種對自我生活在一個悲劇時代的明確意識等。為此,現代藝術變得更為極端,這是因為它們面對著巨大的精神危機,空前地感受到焦慮、抑郁、苦悶與彷徨,而沉重的憂慮感和迷惘心態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情緒,所以,現代主義的作品往往寄寓了藝術家自身對時代的悲劇性體驗,他們的藝術表征著一種失去了現實歸屬及認同對象之后的某種放逐意味的美學意識。
以有限的材質去表現宏大的《超象》主題,我們的選擇只能是精神性的,只能用直覺的方式展示出超越的幻想,只能在有限的時空中把握內在的超越,其中的感情跌宕起伏,往往由個人出發,而聯想到時空的廣大而無窮。這是因為,面對著整體性的精神危機和巨大失望,我們期待著在“超象”的自由界面中重建精神家園,即一方面與物化世界進行抗爭與努力,一方面又將自己的藝術探索深入到生命存在之中,而“超象”體現的是與之相對應的內心力量和精神價值,并將藝術思維的邏輯起點置于這個基礎之上。
結語
藝術的偉大在于渾然蒼茫元素的介入,因為它們包含著崇高之美的意識和成分,它們往往意蘊深長,總讓人去追向和領悟超越生命空間的道理,并喚醒人對生命本質和事物本質的叩問,探尋其價值與意義的皈依,這也是我們重視并重提“超象”的意旨。這表明,藝術因此而卸去傳統的某種重負,并回歸到藝術自身,構成藝術作品的材質、形式語言的純粹性與本色也因此被空前煥發出來。因此,“超象”的世界必然是整體的、神秘的,藝術中的“超象”在虛擬的視野中現身為神秘和無限。
在這里,整體是部分的整體,思考是無限的思考,于是,思考參與到無限之中,讓形而上的波濤覆蓋了一切。在作品《超象》中,元素的選擇并未離開經驗,表面看去,是可見的,仔細審視,不可見卻無處不在,因而,它常常展示為渾然蒼茫的詩意。畫家不是哲學家、思想家,但他的特點是思考著“思考”本身,即他的思考就是答案,就是結果;我們從探討“超象”出發,經歷了創作的過程,最終又回到“超象”本身;在“超象”中,“感覺”是心靈的感覺,“發現”是發現本身,“尋找”是尋找本身,概括的說,它們都體現在瞬間的潑灑與滴濺中。“超象”是當代藝術一個歷久彌新的永恒命題,“超象”的本質意義意味著,它不只是趨近天道的一種審美方式。
藝術方向論文投稿刊物:《上海藝術評論》創刊于1987年,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管,上海藝術研究所主辦的以視覺藝術為中心、用圖文并茂形式全面展示文化藝術風采的雜志。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