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的越界與重塑:自媒體“戲精牡丹”中性別形象的述行與重構
時間:2020年04月17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反串表演從古延續至今,作為以性別扮演為基礎的傳統藝術表演形式,其一直具有相當獨特的地位。在發展迅速的新媒體環境下,以“戲精牡丹”為代表的反串表演自媒體可謂異軍突起。本文基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述行理論,對“戲精牡丹”中的性別形象進行身體意象、話語行為、場景情節三方面的塑造機制分析。其在性別形象的塑造上和延續傳統反串表演行為性別述行的基礎上,更有著依托于互聯網和數字科技的新特點。
關鍵詞:自媒體;戲精牡丹;性別形象;性別述行;越界與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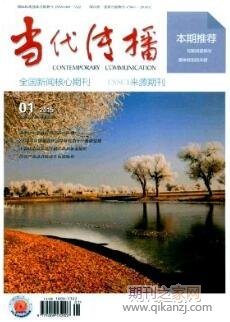
一、引言
反串表演行為源于中國傳統戲曲,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戲劇藝術表現形式,通常指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的表演行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港臺影視中的性別反串現象逐步流行,出現了東方不敗、許仙、虞姬等一系列經典的性別反串角色,性別反串表演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此后,反串表演雖然屢見不鮮,但鮮有代表性的形象產生。
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和媒介內容的娛樂化趨勢,各娛樂化平臺均涌現了反串表演代表性人物,如“大連老濕”“青島大姨”“朱碧石”和“戲精牡丹”等一系列反串紅人,實現了性別反串表演的再流行。2018年,“戲精牡丹”以反串“張嬢嬢”“趙凱麗”“趙囤囤”等形象進行表演為主的自制短視頻形式一炮而紅,其作品全網點擊量累計數億,微博超話閱讀量超8億,微博粉絲超400萬,作品相關微博評論持續破萬,并受邀參加《快樂大本營》《奇葩大會》等多檔熱門節目。
“戲精牡丹”成為繼“Papi醬”之后最受人矚目的以短視頻為主要作品的內容型自媒體之一,其反串形象深入人心,通過極具張力的表演掀起了一股“瑤池熱”。本文試圖以“戲精牡丹”的反串表演為例,以自媒體的興起為背景,試圖從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述行理論的三個維度對性別反串表演自媒體的形象進行分析,剖析近年來自媒體媒介中日趨常見的性別反串表演的形象塑造機制,探究其在性別表達及形象塑造上與傳統的反串表演形式有何異同,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探討性別反串形象的傳播所帶來的影響,深入探討其有無顛覆和挑戰傳統性別秩序之勢。根據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述行理論,性別本身即人們所不斷表演的結果,那么性別反串表演在本質上即是模仿和重復人類本身性別述行的結果。這一過程中,性別述行本身同樣具有三個維度的塑造,分別是戲劇維度的身體意象塑造、語言維度的話語行為塑造和儀式維度的場景情節塑造。
二、“戲精牡丹”的形象塑造分析
(一)戲劇維度的身體意象塑造
長期的社會發展形成性別刻板化形象,使性別角色有了其專屬特征。性別反串表演通過對傳統性別形象進行模仿以達到形象的契合。基于社會對性別形象的建構,表演者通過預設女性形象作為行動主體去達到表演效果。從身體意象上對“戲精牡丹”中角色形象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包括“張牡丹”“趙凱麗”“Fiona”“趙囤囤”在內的幾乎所有角色的形象塑造均有著較強的社會性別色彩。
在視覺形象方面,“Fiona”以黑色長發、女性漢服等符號作為角色形象特征,“趙凱麗”則以金色短卷發作為角色形象特征。除此之外,不同情節通過露肩裝、耳環等各種帶有女性社會性別色彩的符號加強了角色的塑造。在行為特征方面,表演者均以不同的異性行為特征進行表演,在此基礎上“戲精牡丹”中反串女性角色的表演者在表演過程當中仍保留了許多男性特征,最為明顯的是其濃密的絡腮胡。
此外,由于主要表演者趙泓扮演多個女性角色,各角色間主要以發型特征作為區分。在視頻作品當中多次出現其他角色表演時假發脫落,而表演者的表演特征即恢復到“張牡丹”這個角色。更為有趣的是,主要角色“張牡丹”的表演者趙泓不管是頭發的長度或是衣著的中性程度,均與“張牡丹”這個角色無任何差別。生活分享類視頻中的行為特征也與劇中角色有相當大的重合部分,說話語氣與肢體動作時常會呈現傳統意義上的女性特質。
(二)語言維度的話語行為塑造
福柯認為,話語是權力關系匯聚的中心,有其自身的社會和歷史的語境,是具體生存條件的產物,而權力結構又分散于話語實踐當中。在此基礎上,朱迪斯·巴特勒對性別身份的構造與話語緊密相連,指出性別身份其實也是話語的產物。從語言的維度對“戲精牡丹”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張牡丹”的話語風格極具中年婦女特征。其出現的作品話題通常涉及家庭生活,“張牡丹”時常言辭犀利,同時思想開放,時常以中年人的角度學習青年人慣用的話語符號或網絡語言,通過豐富的話語符號構建出了一個眼界有限但力圖緊跟時代的中年婦女形象,十分貼近生活,能引起受眾的廣泛共鳴。在視頻作品當中,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獨立的語言特征,對角色形象形成了極大的區分。
但在此基礎上,各角色卻均時常共用同一套以“惹”“哈”“吼”等語氣助詞為特征的語言體系,極具網絡氣息和女性特質。與身體意象的塑造相似,在對支線劇情和生活分享類的視頻進行分析之后發現,表演者在非表演狀態下也時常運用劇情當中角色所使用的語言特征。加上身體意象的劇里劇外的塑造,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類似于“趙泓即是張牡丹本人”這樣的身體意象和話語體系總體上的統一。
(三)儀式維度的場景情節塑造
性別是一種行為、一種過程,是“一個自由漂浮的詭計”,其實際效果是通過述行而產生出來的。朱迪斯·巴特勒認為,反串這樣的戲仿式表演行為十分需要表演情境來進行支撐,換裝反串本身并不足以構成性別的顛覆①。反串表演者通過其各種故事情節的安排和場景的塑造進行日積月累的表演和傳播,使其性別角色的塑造全面豐富并深入人心。
相比于很多反串表演者,“戲精牡丹”并未在場景的塑造上花大功夫,視頻內容的主要拍攝地就是其辦公樓的天臺,這個簡單的場景被故事情節虛構成“張牡丹”的家、“趙凱麗”的公司、菜市場、酒店和學校等。在每個不到8分鐘的短視頻中,創作者前后構建了20余個角色人物,并創造了三個主線故事相互穿插②。所有情節中的幾乎所有角色均為主要表演者,以反串表演方式呈現,通過結構分明、互相連接的故事情節和內容以及主創者精湛的表演把各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飽滿。“戲精牡丹”的視頻作品中,場景和情節在表演者精湛表演的基礎上,對形象的塑造做到了成功助力。
三、“戲精牡丹”性別形象的述行與重構
通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述行理論帶來的啟發對“戲精牡丹”進行以上三維度的分析后我們發現,其性別反串表演比起傳統性別反串表演而言有所突破。
(一)性別刻板化形象的服從與反叛
中西方的傳統戲劇都經歷過男性扮演女性的反串表演階段,男性演員通過放棄性別身份展現女性性征的方式進行表演,其最關鍵之處在于性別刻板化形象的運用。“戲精牡丹”的主要作品中,無論是身體意象、話語行為或是場景情節,均廣泛通過對性別刻板化形象的服從來展現性別角色。強化性別刻板化形象并通過這些維度展現,表演者能夠更好地將其所表演的性別角色形象立體地展現,更全面立體地塑造角色以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在此基礎上,“戲精牡丹”的作品當中時常浮現對性別刻板化形象的反叛,以主要表演者趙泓的身體意象為例,盡管他使用道具和大量的身體語言來表演多個女性角色,但始終保留其男性性征。通過對其視頻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保留男性性征并非僅僅以此為噱頭和形象特征,其扮演的主要角色“張牡丹”“趙凱麗”均為性格強勢的女性,觀者在熟悉其形象之后,會不自覺地將胡須等男性刻板化形象與其所扮演的女性角色相聯系,不僅突破了審丑的界限,也對性格形象的塑造有所助力。在近兩年的作品制作傳播期間,通過角色的塑造經營和故事情節的展開,不斷引發受眾產生共鳴,“戲精牡丹”已漸具品牌效應,從而構建出了其獨特的性別身份。
(二)性別的越界與重塑
反串表演這個表演行為本身主要挪用了性別刻板化形象,這一行為無疑是建構在異性戀二元性別框架之中的。生理上的男性模仿女性或是生理上的女性模仿男性,均是在模仿其社會性別,那么反串表演這一行為本身就暴露了社會性別本身所具有的模仿性。梅蘭芳是作為生理男性的旦角演員,而他曾在《轅門射戟》一劇中演生角的呂布,反而被視作反串。戲謔地說,對性別身份的認同本就不應從社會規范的角度去審視,但我們又不得不服從于此。
當男性反串女性時,以我們所具有的先驗的審美態度去觀看其表演,在形式上來說這樣的表演可能是缺乏美感的,所以許多傳統的反串表演都難以擺脫怪異、審丑這樣的審視框架,反串表演形式也大多被視為戲謔或怪誕的符號。但是通過場景、故事、話語、身體意象等因素支撐起的豐富的人物形象可能會讓受眾產生新的審美判斷。“戲精牡丹”在二元性別框架之下運用性別刻板化形象進行反串表演,這無疑與眾多反串表演相類似,對二元性別的邊界有逾越之勢。
在此基礎上,“張牡丹”“趙凱麗”“趙囤囤”等角色的產生無一不來源于創作者的生活,胡須等強烈的性別符號已漸漸讓觀眾產生與“張阿姨就是應該有胡子”類似的觀感,這無疑體現著對傳統性別秩序的挑戰。有趣的是,主要表演者在生活分享視頻當中的體現與角色整體形象及性格特征也并無本質上的差異,這足以說明戲里戲外角色性別形象與其本身存在互相聯系的關系。男女性別之間的界限不僅僅是在表演中被打破,還有了融合再生之勢。
四、結語
自媒體依托于“內容為王”的準則,迎合流行文化的同時引領社會風潮,其中的反串表演自媒體可謂異軍突起。面臨內容生產方式和傳播模式的改變,以“戲精牡丹”為代表的反串表演自媒體的內容形象塑造機制也因此產生了微妙改變:性別形象的塑造上與傳統反串表演同樣有在二元性別框架之中對邊界的跨越;在此基礎上,自媒體塑造性別形象有融合重構性別形象之勢,試圖對傳統性別框架持續發起挑戰。
參考文獻:
1.都嵐嵐.朱迪斯·巴特勒的后結構女性主義與倫理思想[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2.孫婷婷.朱迪斯·巴特勒的述行:理論與文化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0.
3.王蕾,朱雯文,常博.媒介中性別反串形象的塑造及社會張力研究[J].當代傳播,2018(01):37-40.
4.代黎明,王蕾.性別反串的再流行:從“朱碧石”走紅說起[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7(03):65-69.
新聞傳媒論文投稿刊物:當代傳播主要展示我國新聞傳播理論領域的最新學術成果和前沿理論,分析中國新聞傳播實踐的演進規律,揭示各種傳播現象的本質內涵,推進新聞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理論創新。
SCI論文
- 2025-01-254本工程類高性價比SCI期刊推薦:
- 2025-01-23自動化與控制系統4區期刊IMA J M
- 2025-01-23被SCI拒稿的文章從哪些方面修改
SSCI論文
- 2025-01-25通過率高!推薦6本超好發的藝術SS
- 2025-01-22語言專業研究生適合投的外文期刊
- 2024-12-24教育類ssci期刊大全,來自最新ss
EI論文
- 2025-01-24如何提升ei論文水平
- 2024-12-282024.11版EI期刊目錄,新增18本
- 2024-12-262025年即將舉辦的醫學國際會議
SCOPUS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1-24期刊單核、雙核是什么意思
- 2025-01-23城市交通發展相關文章適合投的期
- 2025-01-21天文天體學外文期刊合集
發表指導
- 2025-01-25論文投稿前要檢查哪些內容?
- 2025-01-24醫學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講解
- 2025-01-23民俗文化方向的論文文獻39篇